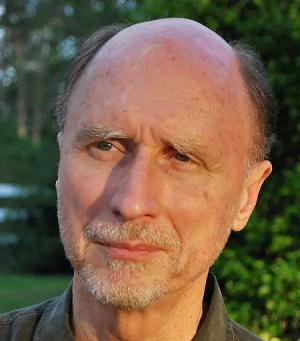2023-09-02《奇山飘香》:他们俩在玩打仗游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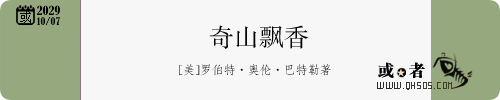
塔哥在我内心深处仍被视为同胞。这件事和他是不是越南人毫不相干。
——《投诚》
一个是生活在美国的南越移民,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一个是当过工兵、有头脑的越共政委,但是妻子和两个孩子被越共杀死,一个和另一个,当然是同胞,但是在“和他是不是越南人毫不相干”的同一性中,“同胞”的意义在于一种心灵的契合,一种文化的认同,甚至是信仰和爱——当“投诚”发生,是不是“移民”成为了共同的身份?当自杀发生,是不是战争成为了唯一的罪恶?
“我心中没有恨。”小说的第一句就将我和“祖国”一刀两断,曾经的南越已经不存在了,曾经的妻子跟人跑了,我来到了美国,成为居住在新奥尔良的美国人。但是没有恨的决绝却是另一种无尽的恨,“但我的确为过去的敌人感到难过,也为我们国家的敌人感到难过。”生活在美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并不是对恨的消除,也不是对彼岸那片土地的遗忘,当那一个关于“投诚”的故事被听到,关于背叛和坚守变成了每一个移民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投诚的主角是一个名叫宕文塔的越共政委,他当过工兵,是个杀手,在越战中当然是精英分子,“他善于向柴夫、渔夫和农夫这样普通老百姓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而且在这方面是个专家。”但是因为崑藁省的一个村干部喜欢上了美国消费品并最终因此而出卖情报,那里的村民被杀一儆百,宕文塔以为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会因为自己而平安无事,但是悲剧的是,他们也遭到了杀害,于是这个曾经冥顽不化的越共分子,成为了南越政府“投诚”计划的一部分。
塔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基于一种悲伤心理,更是一种对政治信仰的背叛,而在我的理解中,这是塔哥对妻儿的爱,“我明白,塔哥不是鬼,而是个普通人,他爱自己的妻子,对她有爱欲,就像我爱我妻子,想和她在一起一样,只不过他的爱欲限制在保持个人品行纯洁范围之内。”这是基于政治之外的个人情感的表达。但是在那个漆黑的夜晚,投诚最后变成了暗杀和自杀:塔哥溜进帐篷,杀掉了两位军官中的一位,然后他自杀了,“子弹还留在他脑袋里。”为什么投诚的塔哥会选择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个夜晚,军营的帐篷里放映了美国影片,影片充满了肉欲,几乎激活了每一个男人的渴望,连我也有了想和电影里的长发女郎在一起的冲动,“这些女人如此乐此不疲地和过路的农夫、进城的水手、送货员、中年小大夫们一起云来雨去。”塔哥也观看了影片,但是对于他来说,在激发了“渴望和妻子在一起”的欲望之后,他动手杀死了执意带他去俱乐部的军官,然后自杀。
在观看美国影片和杀人、自杀之间建立了怎样一种逻辑?按照我的看法,塔哥之所以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改变了投诚的身份,就在于,“西方龌龊的东西直接影响了他,让他产生对亡妻的冲动,这只会把事情变得更糟糕。”别无选择的他杀死了代表龌龊文化的美国军官,这是一种对背叛的背叛,他甚至认为妻子和孩子被杀是一次误杀,但是他又无法回去,所以选择了自杀。无论是杀人还是自杀,对于塔哥来说都是一场悲剧,“我最后想说的是,无度的欲望将导致不幸,顽固不化也将导致不幸。”而对于已经成为美国人的我来说,只有在把自己当成佛教徒的信仰中选择遗忘,“我终于可以长时间地从黄昏打坐到深夜,已没有想看、想听或想做些什么的迫切愿望了。”或者那也是仇恨烟消云散的证明。
从投诚到杀人,从背叛到背叛的背叛,塔哥的悲剧里隐含着一种信仰,政治信仰之外的情感信仰,在他看来,这才是不容亵渎的:在越共杀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之后,他选择了背叛;当他发现自己的选择里充满了西方龌龊的东西,他又选择了回归,一切都是对妻子的爱,但是在这个战争年代,这种爱无疑是脆弱的。罗伯特·奥伦·巴特勒讲述这个“投诚”的故事是要发掘战争之下人性的东西,但是战争无疑破坏了内心脆弱的爱,死亡便成为最后的选择,但是很明显,将塔哥的悲剧归于对于西方龌龊世界的揭露,似乎显得勉强,而且背叛和背叛的背叛无疑建立了一种二元论:要么成为没有祖国屈辱生活的越南人,要么成为接受一切美国文化的移民——而且,罗伯特·奥伦·巴特勒用越南人的视角呈现战争之后来美国的移民生活,似乎也变成了太多的想象。
小说《格林先生》中的“我”当然也是一个越南移民,但是无法遗忘的是那些关于越南的记忆:七岁时听到外公和父母的吵架声,之后离开河内南面红河边的城市,这次争吵的原因是生为天主教的父母要离开故乡,而信佛的外公认为是对祖宗的背叛,“你父亲正在做件可怕的事。如果他必须做个天主教徒,那还算说得过去,但他远离自己祖宗,让自己永远孤独地四处漂泊就说不过去了。”在外公看来,我们生于斯也必将死于斯,最后他在西贡去世,而那时我已经二十四岁,新婚燕尔的我选择了离开来到了美国。外公和父母以及我,其实代表着三代,三代有不同的选择,这种不同的选择反映在那只名叫“格林先生”的鹦鹉身上:小时候外公总是冲着鹦鹉鞠一躬,然后说:“你好啊,好好先生。”格林先生也回答:“你好,好好先生。”而当外公和父母发生矛盾的时候,他说了一句:“那时该怎么办呀?”格林先生也同样说了一句。“你好,好好先生”和““那时该怎么办呀”构成了两个时代的态度,而当我去了美国,格林先生也被带去了那里,它最喜欢说的话还是那两句。
但是,当我已经四十一岁,比我还大五十岁的格林先生却开始拔自己的毛,我的阻止根本无效,格林先生不仅拔毛而且还会咳嗽。这也许是因为鹦鹉老去的缘故,拔毛本身就是苍老的标志,但是这只从外公开始和我们在一起的鹦鹉,也见证了战争,见证了分离,见证了美国化的生活,但是它内心里有一种东西始终没有改变,拔毛在另一个意义上则是对美国化生活的抗拒,甚至变成了一种自戕,于是我伸手,“一把拧断了它的脖子”,我用极端的死亡终结了它的生命,终结了它没有遗忘的记忆,当然也终结了它的痛苦——和塔哥一样,死亡就是对无法选择的选择的放弃——无法回去,也无法适应,唯有死亡才是最后的态度。
| 编号:C55·2230721·1982 |
这便是罗伯特·奥伦·巴特勒想要表达美国化之后“回不去”的困境,地理的隔阂,政治的隔绝,是无法回家的现实,而战争在内心里更是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入殓》也是关于死亡的,水姐死了,并不是死在战场上,也不是死于战争,而是和丈夫来到美国之后死去的,曾经在西贡体育馆里一起玩耍,之后和礼哥开始恋爱,和我的丈夫在战争中牺牲不同,我来到美国带着儿子成为移民,至少对于战争还有阴影。但是水姐和礼哥来到美国,完全和那里发生的战争无关。但是战争并非只是表现在战场上,当水姐入殓,我为她梳理头发,心生嫉妒的我甚至还萌生出奇怪的念头,“她让我把她头发梳得漂漂亮亮,好上天去勾引我爱的男人。”但是我发现她的左边乳房没有了,“一个月牙般的伤疤从那个部位一直弯到胳膊下面。”这是身体留下的伤疤,它永远掩盖在衣服底下,只有在死亡的时候才最后呈现出来,而这一伤痕也代表着痛苦,也和战争有关,“这时我才想起她在加利福尼亚那三年的苦日子。她怎么对此只字不提呢?她是怎么用微笑把自己所遭的罪掩盖起来的?”
“三年的苦日子”,等于死去了水姐最美丽的乳房,而战争呢?是不是也让很多人失去了家园,失去了生命,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美国化的生活其实也是战争的一部分,它造成的伤害永远刻在人的身体和内心里。《投诚》《格林先生》和《水姐》其实呈现了三种死亡,军人的死亡、动物的死亡和乳房的死亡,死亡仿佛成为了一种宿命。小说《鬼故事》里,罗伯特·奥伦·巴特勒还写到了另一种死亡:变成鬼魂的死亡。“鬼故事”在罗伯特·奥伦·巴特勒的小说中最具东方特色,讲述者之所以讲述这个鬼故事,也在于表明自己是东方人的身份,“你坐在车上看见一个东方人,正沿着通道走过来。你用不着费劲,一眼就知道我是越南人了——一眼就能认出这是个东方人。”但是从“我们的故事这么开头吧”到“我登上了一辆叫大灰狗的公共汽车”,再到“你”认出我是东方人,人称的变化是罗伯特·奥伦·巴特勒的一种写作技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让作为美国人的自己化身为越南人,从“我”的写作和故事中传递一种普遍的情感。
鬼故事发生在越南,发生在战争还没有停止的一九一七年,一个名叫阿冲的南越少校去市里看望情人,在晚上回来的路上,为了避开越共,他关掉了车灯,借着月光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盘旋。忽然,他看见前方的一个女人,挥着手让他停车,当时他的车正向她冲去,但是一转眼女人不见了。在行驶了一段路之后,他又发现了一个女人,他以为是另外一个女子。后来阿冲感到疲惫,于是睡在了路上,梦里一个穿白旗袍的女子出来了,她说她叫阮芝琳,“哇,一定是一种荷花让他动了心,随之激起他的荷花梦。”但是在阿冲醒来之后发现路边有一个死去的人,“这是少校一次夜间巡逻中曾看到过的惨状。显然,这些人遭到埋伏,在这个地方被消灭了,正如那个年轻女子在梦中警告他的那样。”死亡发生了,连接了梦和现实,过去和现在,但是这并不是死亡的全部,当阿冲来到村子,那个叫阮芝琳的女子其实四年前就已经死了,当她出现便成了鬼。
|
| 罗伯特·奥伦·巴特勒:这里的世界没有国家界限 |
战争中死去的人, 死去的人变成了鬼,为什么阮芝琳还要变成鬼回来?这也许是这个“鬼故事”的寓意所在,叙述者讲述这个故事,对于和自己女儿的丈夫一样的美国人来说,这个故事没劲,但是对东方人感兴趣的听者却想要知道故事的结局,“你就会对这个故事结局感到惊奇。”因为最后的结局是:阿冲最后悲惨地死在了这个魅力十足的女人口中。这又是另一种死亡,一个在战场上作战的少校之死,似乎是某种对战争的谴责,但是死亡终究越过了战争的界限,因为这个故事的真正结局是:讲故事的人是琳的哥哥,他给我看过琳的照片,照片里琳的那张嘴巴十分显眼。那个关于鬼的故事在琳的哥哥那里已经完结了,但是在我的叙述中又开始了:当我离开越南被带到美国的时候,琳就冲我微笑,而我之所以要讲这个故事中的故事,“因为我想看看自己在异国他乡能得到什么样的待遇。”当然有人还在听这个故事,于是故事的真正结尾是这样的:“当我坐上黑乎乎的大轿车离开时,眼睛望着窗外,看见琳姐的舌头又从嘴里吐出来了。她舔着自己的嘴唇,好像刚把我吞下去似的。她真是那么做的。”
琳不是鬼,琳只是一个有着大嘴巴的女孩,当有人离开去美国的时候,她张开嘴巴然后把我吞了下去,吞下去就是阻止了离开,就是破坏了分离,和阿冲之死、我在异国他乡寻找听众一样,是为了保留“鬼故事”的真正内核,那才是属于东方文化的一种。如此,在某种意义上,罗伯特·奥伦·巴特勒所塑造的死亡都只有一个目的:不离开,或者回来,而这种情绪的表达,其背后却是战争带来的离开,是隔阂造成的“回不来”。但是,罗伯特·奥伦·巴特勒在另外几篇小说中却叙述了“不回来”的选择。《童话》以一个曾经是“傻乎乎的西贡酒吧女”的视角讲述自己的经历:一九七四年,她认识了在美国使馆工作的男人,然后说要娶她,然后有了孩子,男人把她带到了美国,孩子和母亲则在越南。但是后来他变了,这个名叫诺小姐的女人又离开了他,遇到了另一个男人冯特诺,冯特诺让诺小姐成为了真正的美国公民,他们也结婚了,他以修理汽车发动机为生。
诺小姐的故事里虽然有欺骗,但是美国的生活对于她来说并不是一种悲剧,因为她曾经尝到了苹果的味道,“要不是因为大兵送我苹果,我这辈子也吃不上苹果。”一个苹果,其实是生活被改变的,它代表着甜蜜,而美国生活意味着更多苹果,“现在她吃到嘴里的苹果,味道显得格外香甜。”这的确像是一个童话。和童话带来的甜蜜一样,《一对美国夫妇》则讲述了一个游戏:我和丈夫生活在美国,一次免费度假的机会遇到了美国人弗兰克和妻子艾琳,四个人游览风景,但是最后丈夫文哥和弗兰克却开始了一场游戏:“我终于明白了,他们俩在玩打仗游戏。”因为弗兰克曾经是越南战场上的一名大兵,而文哥也上过战场,两个人的游戏很简单,就是跟踪和反跟踪,就是掩护和抢占海滩。游戏对于他们来说,是为了再次体验共同的经历,“他们共同经历了愤怒、恐惧、施暴的刺激,也共同经历了正义的感召和战斗中的生与死。他们在同一场战争中感受到这些。他们都不愿意忘却那段经历。”
在游戏中回到战争,当然不是为了还原战争的残酷,而是“一对美国夫妇”用游戏让自己回去,回到曾经的故乡,感受曾经的文化,“夜幕即将落下,我丈夫终于又回到人间。我也是。”游戏其实也消融了战争的对立性,或者,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游戏。《奇山飘香》的视角更为独特,一个已经快一百岁的老人,生活在美国,但是一天晚上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他竟然是胡志明,胡志明还亲切地称他为“刀老弟”,还一起感受了和好教的教义“宝山奇香”,当胡志明的手上还沾着做糕点的糖渣,它构成了在文化认同和记忆复原下的体验感,即使儿女和孙子孙女都在战争中死去,奇山飘香也永远无法磨灭。而在奇山飘香的夜晚,胡志明对他的选择没有责怪:“你觉得自己已经尽力就行了。我再也不会质疑另—个灵魂的选择。”并且告诉他,“这里的世界没有国家界限。”甚至对刀老弟“不过问政治”表达了赞许。
奇山飘香的奇特夜访,仿佛一下子拉回到了没有纷争的岁月,这也许是所有人的期望,也寄托着罗伯特·奥伦·巴特勒的美好愿望。但是美国人创作关于越南人生活和情感的故事,通过越南人的视角构筑“奇山飘香”的命运共同体,或者真的是一种想象,就像所谓没有国家界限的世界,不过问政治的态度,尊重灵魂的选择,都变成了一种理想,它封闭在每个人的心中,就像那一股香味,“他离我非常近,糖味又浓又甜,直冲我的肺腑,似乎它是从我的身体里散发出来的,似乎胡志明正穿过我的身体,我听见身后的门打开了,接着又轻轻地关上了。”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5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