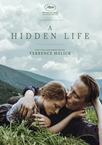2024-11-29《隐秘的生活》:信仰之路上的双重拷问

依然是黑屏中开始的独白,依然是广角镜头下的画面叙事,依然是充满追思的情绪性表达——依然是泰伦斯·马力克标签式的影像语言,但是这一次马力克重回叙事,甚至重回《细细的红线》中的战争叙事,在没有改变影像语言的叙事中,马力克却极大地拓宽了电影主题:他曾经在《穷山恶水》《天堂之日》《新世界》中探讨“土地之母”,曾经在《通往仙境》《圣杯骑士》中探讨“天国之父”,而这次他将两者结合起来,不仅是一次从地上到天国的探讨,更是以真实事件改编的故事中,对大地之母和天国之父提出了双重拷问,而拷问的最终目的是寻找关于信仰的最终答案。
土地构成了马力克关于信仰叙事的第一层含义,在奥地利的圣拉代贡德地区,弗兰茨和法妮是一对夫妻,他们在“心有灵犀”中相遇相识相爱,那辆摩托车是他们爱情的见证,而成为夫妻生下三个女儿的他们,更是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对于他们来说,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是平和的、幸福的,他们面对着雪山,他们躺在柔和的草中,他们欣喜于土地发出的第一粒芽,他们每天和土地对话,也就是说,对于他们来说,“土地之母”代表信仰是一种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他们播下种子,他们辛苦劳作,他们完成收获,如此年复一年,“我们生活在云端。”即使弗兰茨之后进入恩斯军事基地训练,两个人通过信件传递着这种对“大地之母”的无限热爱,“生活如此简单,似乎没有任何烦恼可以打扰到我们的山谷。”
但是,当战争到来,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我原以为我们能在高高的树上筑巢,如同鸟儿一样飞向高空……”当他们抬头望去,天空中没有了自由的飞鸟,只有发出轰鸣的飞机,这种侵入式的声音完全打破了这一片不被打扰的土地。但是在完成恩斯军事基地训练的弗兰茨回到家乡,却表达了自己拒绝被征兆的想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每一位应召入伍的奥地利士兵,在服役期间都要向希特勒宣誓效忠。弗兰茨对征召的拒绝就是对效忠的拒绝,而对效忠的拒绝就变成了对权威的拒绝,而信仰对于每个人来说,上帝也是绝对的权威,由此构成了弗兰茨对于天国之父的拷问:“一个人有权利将自己置于死地吗?这样做可以取悦上帝吗?他希望我们拥有和平和幸福,而不是给自己带来苦难。”
| 导演: 泰伦斯·马力克 |
弗兰茨看来,天国之父带来的是和平和幸福,而信仰上帝的人自然会获得他给人类的和平和幸福,自己一家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在云端上生活,不正是和平和幸福的实现?为什么会被征召?为什么会加入战争?为什么要效忠而去杀人?弗兰茨面对信仰,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但是当神父、主教回答他的问题,并没有让他得到了关于信仰的解答,反而陷入了更深的疑问。在弗兰茨明确表示自己不会被征兆的时候,神父找到他警告说:“你或者会被枪毙,而你的牺牲对别人毫无意义。”而主教对他的劝解是:“你对祖国负有义务,每个人都服从架之于他们手上的权力。”当弗兰茨表达了自己的想法,神父的回答是:“那我们只能站在你的对立面了。”
弗兰茨终于被征兆了,当他告别妻女、告别那片土地来到恩斯,在众人以纳粹军礼行礼时,弗兰茨再一次选择了拒绝,他被征召意味着将穿上军装成为一名士兵,但是他的这一拒绝的举动让他穿上了囚服,关进了泰格尔监狱,狱警问他:“你这样做是上帝告诉你的?弗兰茨的回答变成了一次反问:“难道战争不是正义也不重要了?”狱警对他的警告似乎直接泯灭了他的信仰:“没有人是无辜的,创造了世界的主也创造了恶。”上帝创造了恶,甚至他们告诉他的是:“只有成为一个敌基督者才是聪明的人。”但是弗兰茨心中永远有上帝,永远有关于正义的信仰,所以他拒绝妥协,拒绝效忠,甚至拒绝律师提出在同意书上签字,“这只是几句话而已。”律师对他说,在他们看来,效忠只是一个暂时的态度,只是说几句话而已,但是弗兰茨再一次拒绝,“我做不到!”弗兰茨对信仰越是提出拷问,就越是坚信对上帝的忠诚,而他越是坚守,也就越来越承受身体之痛,在监狱里他被毒打,被侮辱,也正是如此,从另一方面来说,他越是不肯妥协和背叛,“我内心有一种感觉,无法去做我认为错的事。”柏林的军事法庭对他作出了死刑的判决,面对法官给他的机会,面对律师给他的条件,甚至面对法妮前来看望而无法最后拥抱,弗兰茨还是坚守内心的想法,由此进入到拷问之后的信仰的最终回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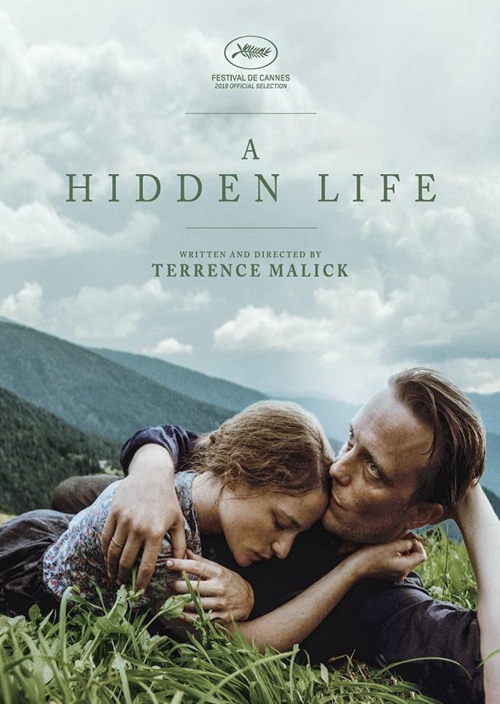
《隐秘的生活》电影海报
弗兰茨在监狱里受到非人的待遇,他对于天国之父的拷问,就在于在战争这架机器中,信仰早已经被异化了,在神父那里是逃避,是明哲保身,在主教那里是权力,在其他人眼里则变成了沉默。同样,那片土地也被异化而遭遇了灵魂的拷问,在弗朗茨还没有被征兆的时候,无论是镇长还是村里人,都对他们投以鄙视的目光,甚至还侮辱他们,因为其他男人都被征兆了,为什么弗兰茨可以拒绝?“他们是敌人,而你是叛徒。”镇长这样对他说;当弗兰茨离开土地,法妮更是遭受了村里人的冷落和辱骂,他们和法妮保持着距离,他们再也没有帮助弱小的法妮,甚至还偷走了法妮辛苦种下的蔬菜。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本来和弗兰茨、法妮一样是勤劳、淳朴的,但是战争改变了他们的态度,他们变得自私,他们学会了偷盗,这是农民的一次迷失,这是“土地之母”代表的信仰的沦落,法妮甚至只有在寡妇、流浪者面前感受脆弱的爱。同样,在弗兰茨的世界里,土地已经远离,土地的信仰也早已经被异化,在狱中一个囚犯看到了地上长出的一株小草,他试图接近遮住小草,但是狱警粗暴地将他拉走,并毁坏了这绿色的希望;而在弗兰茨被判死刑给法妮写最后一封信的时候,纸上爬过了一只毛毛虫,这让他回忆起在那片土地上的劳作,回忆起和法妮第一次见面时的摩托车,而这也成为弗兰茨再次回到土地之母的一种象征。
土地之母还在,天国之父也还在,他们在弗兰茨的世界里构成了真正的信仰,所以在被判死刑之后,在目睹了别人残酷的行刑之后,信仰在弗兰茨的世界里反而变成了更具力量的存在,那就是爱、信和期盼,他在给法妮的信中说:“我至爱的你们,我会在另一边祈祷,上帝的恩泽会让我们重逢。”当弗兰茨被执行死刑,村子里响起了教堂的钟声,“我们活着,我们会相伴而来,我们会耕耘,会重建土地,我们会在群山之中相见。”那株小草还会长出来,毛毛虫爬过最后的信,在死亡的瞬间看见的是家乡的高山、麦地、驴子和羊群。信仰不灭,它在爱、信和期盼中重新让人获得力量,而这种力量在马力克的叙事中是关于土地和生命的,它最后变成一种善。
“因为世上善的增长,一部分也有赖于那些微不足道的行为,而你我的遭遇之所以不致如此悲惨,一半也得力于那些不求闻达、忠诚地度过一生、然后安息在无人凭吊的坟墓中的人们。”引用乔治·艾略特的话,马力克将信仰变成个体的善,它们微不足道,却是对世界的一种改变,就像弗里茨,他拒绝效忠只不过是一个人的态度,“你这样能改变什么?你比其他人更好?”这是对他的拷问,在这些人看来,弗里茨一个人的行为并不能改变他人的态度,并不能改变战争的走向,个体行为不仅毫无意义,甚至自己还失去了生命,但正是这一种忠实于自己的态度,正是拒绝不义的善,才是信仰的真正力量,它是生命本身,它是自由精神,它是对平庸之恶的刺痛和唤醒,它是对沉默者、逃避者、迷失者的解救,就像法妮在信中所说:“你永远的留下了,亲爱的弗朗茨,你是那昼夜的温差,你是那四季的变换,你是那山谷里最温柔的回响。”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