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7-20《鲸鱼马戏团》:整个山谷都在止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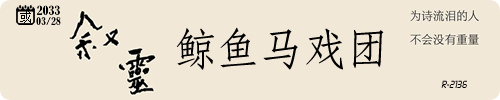
在梦境里
我梦见自己死了
一团透明的物质
白色的肉身
望着睡梦中的我
望着我做梦的那个地方
不知身居何处
——《神奇梦》
竖的《饭泡粥》之后,阅读的第二本“年代诗丛”诗集,也和竖一样,孤陋于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诗人叙灵的名字,更没有只言片语阅读过他的诗,而“年代诗丛”似乎也乐于将每一个诗人都脱离于他具体的生存实践:主编韩东的标准是:“入选的诗人无关年龄、知名度”;对于叙灵的介绍极为精简的放在某个角落里:“叙灵,原名禹运涛,1973年生于湖南麻阳,苗族。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数学系。著有诗集《舅舅的湖泊》等。”没有关于叙灵技校毕业、乡村供销社供职、湖南大学求学、北影学习以及问道的个人经历介绍,甚至连叙灵的那篇《<鲸鱼马戏团>后记》也没有收入诗集中。当一切具体的个体背景被抽离,它只是一本诗集,一本作者为叙灵的诗集,一本收录1992年至2024年诗歌的诗集——“叙灵”在一本诗集中也只是一个作者的名字,它以夸张而畸形的签名设计呈现在诗集的封面上。
背景被抽离,经历被抽离,对于诗集的阅读只能在诗歌本身之上,这是不是叙灵所一直追求让事物呈现自身的问道之中?但是诗集却恰恰以时间坐标标注了叙灵的不同人生阶段,它所构成的也正是一种“个人史”。在并没有提供进入叙灵个体生活的进口时,阅读所形成的只能是一种诗歌意义的个人史,文字是起点文字也是终点,而这无疑是片面的、抽象的。在这个由诗歌组成的简史中,大致可以看出叙灵自我角色的转变,这种转变可以用孤者、幻者和隐者三个阶段来定位,而《神奇梦》作为收录于2013年至2014年诗辑《远处群山》中的一首诗,也正体现了这种自我角色的更新:在梦境中“我梦见自己死了”,死了的是一团透明的物质,而这物质就是“白色的肉身”,而且肉身之死不仅消解了物质性的存在,而且连自己做梦的地方“不知身居何处”,死去的不仅仅是肉身,还有梦,还有做梦的我,还有我的位置,死亡仿佛是一次彻底的告别。
死亡可以看作是《神奇梦》的上半部分,当肉身和梦、梦中的我和位置都死去,却留下了静寂,这是“杂草和虫子形成的静寂”,这是画眉“倒伏在芦苇丛中”的啁啾,是静寂却也有声音,静寂是肉身死亡后的静寂,声音是静寂之后的言说,这个梦的后半部分就变成了一种新生,而这个所谓从死亡到新生的“神奇梦”更有所寄托,“赠曾祥源”就是对于这种新生的回应。这个曾祥源是谁?在同一辑的《葫芦河小叙事》的“小记”中叙灵提供了答案:“2010年9月,我从城里搬到小汤山镇居住。2013年夏,认识了曾祥源舅舅,他来自江汉平原,是一个隐者,也是一名渔夫。2014年8月,舅舅离开了小汤山葫芦河,不知所终。”曾祥源是叙灵在2013年认识的,他在诗中称其为“舅舅”,曾祥源的身份是隐者,是渔夫,当叙灵将这个隐者和渔夫的舅舅写进诗里,并以“不知所终”留下了可能,实际上很明显建立起了和隐者的某种隐秘关系,而这首在这本诗集中唯一的长诗也可以看做是叙灵在肉身死去之后以一个“神奇梦”转变为像曾祥源一样“不知所终”的“隐者”。
但是肉身为什么会走向死亡?回溯叙灵这本诗集在2014年之前的诗歌,可以看出这种死亡是逃离也是追逐,他甚至在一篇访谈中谈到自己其实很想把2005年之前的早期诗歌“统统扔掉”,这无疑是一种更为主观的死亡态度。的确,早期诗歌显出了更多的稚气,比如第一辑《孤独的声音》收录的就是1992年至2004横跨12年的诗歌,第一首诗歌是《春天谣曲》:“田野上的燕雀说/有一种花最苦/叫做忧伤/而村子里的人说/有一种人流浪/只是因他怀着希望”,读起来就像是中学生的习作;“我就要离去了/将开始另一种流浪/只带走九只蜜蜂的歌唱/和一枝橘花的清香”,还在追求着押韵;1993年的《孤独的声音》中写道:“逝去的日子是多么珍贵/那时我关心田野和土地/那时我和朋友谈诗为眠/那时我贫穷而自由/终日在故乡游荡”,也像极了流行歌曲。不过在这一辑诗歌中,还是能看出叙灵后期诗歌的意象雏形,比如2002年的《西禅寺》中,他已经有了一种问道的感悟,“一些混合的光影/来自庙堂、报恩塔和树木/老吴在光影里说/这里真好/人很少哦”;在《爱情》中把“一声不想/便爬了进来”的虫子比喻爱情,恐惧则是一辆“倒悬的火车”,皎洁的月光“像从奶头里流出的奶水”,也是对于事物显示自身的一种写作努力。
虽然在2005年的《舅舅的湖泊》中就有了“舅舅”,“人群/不存在/它是一个幻觉/舅舅乡下蓝宝石的湖泊/沉默着”,《舅舅乡下的湖泊及幻觉》中也有了某种“神奇梦”的感觉,但这一时期的诗歌叙灵所写的还是人生的虚幻,一方面他通过对小人物的书写表达了生活的幻灭感,他们是《小贩邢吉清的清单》里的贩子邢吉清:“职业为街头小贩 全年收入二千有余(吃喝拉撒在内)/据说已离异 妻儿下落不明/平生喜好唱歌弹琴 穷开心/家中财产约干本32开《中外歌曲》小杂志/稍值钱的还有一台国产电子琴 一张脱漆方桌 四把咯吱叫的老椅子/去过的地方有吉首、怀化、铜仁、洪江、泸溪、花垣等十余地/去这些地方的动机和原因大概是贩山羊、倒水果、卖冰棍、擦皮鞋、干苦力”;是《夏天》里孤独的老人、在镜子前发呆的裸体女人,是“他窥视内心的方式/显得胆怯”的潜行者,是看见清澈见底河水中秋夜一动不动的“隐者”,是在立交桥下“形迹可疑的人”……他们活着,却好像活在生活的“监狱”里,“有人在逃跑/他后面并没有追捕人/他仍显得惊慌、软弱及恐惧”。无疑在叙灵的笔下,这些人都有着被生活所累的“沉重肉身”,肉身甚至连进入死亡之梦的可能都没有,“肉身那沉重的负担/让它久久进入不了/那个有湖有草/有微风有树枝沙沙奏晌的梦乡”(《厌恶》)
| 编号:S29·2250604·2314 |
另一方面,这些沉重负担的肉身何尝不是叙灵的一种自喻?“如果我没有从这条山村公路走出去的话/我的身体就会在山谷中/静静地腐烂掉”(《身体静静腐烂在山谷》),在这里他已经有了“走出去”的渴望,这种渴望也是新生的欲望,在《西江的罗伯·格里耶先生》中,他写道:“在西江/他会觉得写作是件毫无意义的事情/群山翠绿/空气中流动着醉人的酒香味”,西江之于罗伯·格里耶来说,不是写作,而是呼吸山水之间的新鲜空气,这也是叙灵对于“走出去”的寄托,他期待的是像罗伯·格里耶一样书写一部人生的“新小说”。但那只不过是叙灵灵光一闪,真正的命运在《蝶恋花》这一辑中,依然是走不出的某种宿命感:他看见了《1985年随舅舅在水库偷鱼》的自己,“这时 我的心在狂跳/周围是杉木林形成的静谧/而舅舅仍坐在一块石头上/抽他的卷烟/似乎没有听见一个孩子的心跳”,还是“舅舅”,却是活在1985年那个真实的舅舅;他也感受到了《1978年下午三叔有些哀伤》:“七八米以外的菜地/在奶奶俯下的头顶/有一只黑蜂/忽高忽低/一直飞动着”;还有《1990年山村张保保家》里的那种暗黑生活,“那一夜/我就睡在他半山腰的家中/那种如盐的月光/散发着汗香/从幽暗的屋后偷偷爬入/好像是他那浪荡的儿子/半夜打牌赌博归来”;那是妈妈的一双手“像鱼鳞一样粗糙”,那时的爸爸手提一件锈皮铁桶、身着一件蓝色的确良工作服,“却是那样地显眼”,那时的童年生活布满了“静得要命的阴影”……
1978年下午的三叔,1985年偷鱼的舅舅,1990年赌博归来的张保保,都构成了叙灵的回忆序列,它以明确的时间、人物和事件构成了“童年”叙事,那些东西也许是美好的,也许是哀伤的,但是在叙灵那里,一切逝去之后就变成了一个人的孤独,“这些灰色/一直生长在石缝间的植物,/像人体内部一件件柔和的器官。”(《蝶恋花》)而即使那时候叙灵开始远离故乡完成了一次出走,他所面对的依然是孤独,它们是从13号道口走出去看见的“极其荒凉”的北苑,是公园里“六节城铁”,是冒着白色烟尘的烟囱旁边的紫绶园12号楼……它们反复出现在叙灵的诗歌中,构成了一种时常萦绕的梦,“有时候/一些人需要做不同的梦才会醒来/例如/2005年3月一天我从双榆树58号院11号楼醒来/2006年9月一天从蔚秀园27号楼月租900元的房间醒来/2008年4月一天又从北苑家园紫绶园12号幽暗的直通过道间醒来”,但它们都是同一个梦,同一个梦,同样醒来,同样无法逃离,这就是叙灵的孤者生活,“空虚/忙碌/甚至无常/我已经虚度了自己的一生”(《绿头苍蝇》)
也许这些梦也唤起了叙灵对于人生的另一种感悟,虚无而追求“走出去”的生活,当“走出去”依然是虚度,那么梦回到梦本身是不是另一种选择?梦醒来,看见了“像丝绒一样的雪”,六节车厢像黑亮的马在“乌兰巴托草原跑过”,还有伯格曼在法罗岛,“只是坐在那里观望/那些玻璃窗外的暴风雪/或者更远处的海洋”(《嘿!伯格曼先生和法罗岛》),正是这些梦让叙灵从虚度中找到了另一个向度,他也开始了从孤者向幻者的转变,“中间隐蔽的那些树木和一座人工湖泊/极像/一个处于迷幻时期的幻者/随手/画下的一幅漫画—”(《康斯丹郡》)电影也是一场梦,“我将变成一头鲸鱼/一头将在马戏团里/表演孤独、饥饿、抑郁、焦虑、失业等节目的/陆地鲸鱼”(《鲸鱼马戏团》)《鲸鱼马戏团》就是这本诗集的名字,虽然其中有编辑对于市场的某种偏向,但叙灵的这首诗也成为对他最喜欢的贝拉·塔尔的某种致敬,更是呈现了一个幻者之梦。
这个幻者之梦里有孤独,但已经是消失在静谧中的孤独,也有静寂,但已经是发出声音的静寂,这样的境况在《远处群山》中就成为了“遥望”,“有好几年/我都这样站在窗台边/遥望那些沉默的群山/就像遥望那从未开始过的一种生活”,这种遥望构成了叙灵之后几年的一种姿态:心向往而身慢慢靠近。“舅舅”曾祥源无疑就是他所遥望的群山,他在2014年几乎用一年时间写下的《葫芦河小叙事》,从“第一年:秋”到“第四年:冬”,完整回忆和曾祥源共处的日子:这里有秋天的荷叶,有冬天的冰层,有春天的豌豆,有夏天的西瓜,有盲人敲击冰面发出的声音,有热天卡在渔网里的鱼,还有一起住在那里来自湖南的石师傅夫妇,“葫芦河”成为叙灵离开城市的一个起点,他从曾祥源的身上看到了“走出去”的真正意义,“舅舅一回头,刚好一阵光/照亮了他头顶位置的一片芦苇/他回头看了一眼,说/哦,你来了/然后,照亮他头顶芦苇的那一片光亮/就消失不见了”
“舅舅”曾祥源制造了这个被光照亮的神奇之梦,最后“不知所终”所开启的其实就是隐者的生活,2015年至2016年的诗歌就被命名为《一个隐士》,从此写诗的叙灵开始了问道,或者说他在问道中写诗,写诗和问道又合二为一:遥望的群山变成了“眼前一座山”,而且“突然被一束光所照亮”;他帮林燕丹居士“收了二次晾在竹竿间的衣服”,看见佟总把湿衣服放在石头上“取些暖”,目睹一个隐士在圆形木桩上“双眼微闭/纹丝不动”;或者自己坐在岩石上,“仿佛听见/远处深山村落/村民的交谈”……成为隐士,叙灵的诗歌就是让事物自己呈现自己,“黄花正黄/白花正白/紫花正紫”,而从2015年至2024年的诗歌中,叙灵追求的自然、空灵以及静寂,明显有着斯奈德的影子,在诗歌中他也写到了斯奈德《砌石与寒山诗》集子,写到了用斧头劈柴,
斧头挥下去
整个动作
就是一首诗的构成
斧头落下位置
刚好在木柴的中心
位置找准了
不用费多少力
柴会自动裂开
写一首诗也如此
他在恒山看橙子色的夕阳,在鹅峰寺感受“心动”的禅意,在长白山养病,用两天半的时间穿越五台山……他的确正在成为隐者的路上,“有时打坐,有时去割草/人生无根,如蓬也如寄/八月在广东,九月下福建”(《长歌吟》)但是这样的隐者人生真的可以“不知所终”?真的是一次抵达自我的新生?真的在观照自然和自我中绽开?“那些沉默的群山/裸露的山顶/披着光/像一个隐士”,《隐士》中的隐士也许的确在叙灵那里只是“像一个隐士”,那种想要放空一切的姿态却总是变成了“所执”,问道是所执的问道,写诗是所执的写诗,活着是所执的活着,“去年初冬/从嘉午台下来/沿途整个山谷都在止语/只有一条不知名的溪流/穿过荒石与丛榛/所发出的声响”,在这种与自然的对比中,“止语”何尝不是一种人为的自我约束?所谓的静默又何尝不是刻意的沉默?
于是,关于一本“年代诗丛”的诗集,最后又回到了和竖一样的问题——豆瓣中的评分高达8.6分,很多读者都打出了五星,平心而论,这本诗集根本无法达到这样的水准,而留下评论的大都是和叙灵认识的朋友,更为关键的是,有一个“自行车苗苗”的ID转载了对诗集的不同评论,而打分几乎一致是五星,“2005年夏天,我以苗苗的笔名进入了广西自行车论坛,写作观念才发生了颠覆地改变,由以往抒情转向叙述性的先锋写作。”很明显,这个“自行车苗苗”就是叙灵,如果只是为了分享他人对诗作的评论,只是为了收集不同读者的诗评,何必要用五星来标注?也许问道也罢,写诗也罢,生活也罢,都只是呈现为一种书写意义上的无所执,都是诗意中被看见的“止语”,人是世俗功利的人,肉身也总在成功者的梦里欲望无限的肉身。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3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