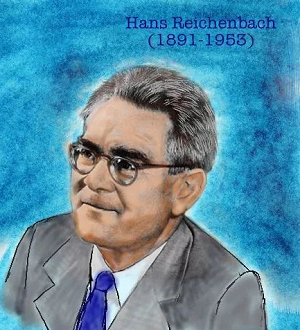2025-07-27《科学哲学的兴起》:科学家是路标的设置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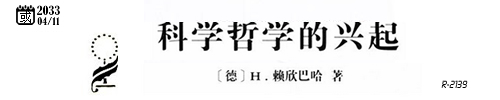
如果逻辑家所能告诉我的只是作假定,我何必去找他呢?他的建议只会增加我的疑惑,而并不能给我以行动所需的勇气。
——《插曲:哈姆莱特的独白》
“TO BE OR NOT TO BE”,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哈姆雷特在独白中以诘问的方式探讨生与死的人性困境,但是当这个“哈姆雷特的独白”从莎士比亚的悲剧中走出,进入到赖欣巴哈的“插曲”中,已经从内心的诘问变成了对外部世界的追问,从人性困境的挣扎变成了寻找答案的努力,这一切都指向了真,且指向了迷雾重重背后的真相,甚至是一个在知识领域里的真问题,于是,生存还是死亡变成了“重言式”的问题,于是所有的陈述都为了获得确切的答案,“我要知道一个综合陈述的真理性;我要知道我是不是活下去。”也于是,这个悲剧人物也变成了赖欣巴哈笔下不按照“逻辑”行事儿缺少勇气的人。
即使哈姆雷特选择以“上演那出戏”的方式进行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实验:“如果他们谋杀了他,他们就无法掩饰他们的心情。这是很好的心理学。如果实验是肯定的,我就将确定无疑地知道事实真相。”但是哈姆雷特最后还是放弃了,因为在他看来实验基于一种逻辑分析,而逻辑分析所能告诉的只是“假定”,而假定只会增加疑惑,所以哈姆雷特放弃了,他放弃了实验,放弃了假定,就是放弃了逻辑分析,“逻辑不是为我预备的。”实验不再具有意义,问题不再有真相,于是,悲剧就永远成了悲剧,而当哈姆雷特为父亲报仇的愿望无法实现,赖欣巴哈创作这一“插曲”,很明显就是批评哈姆雷特缺少勇气,“要能一贯地在逻辑的指导下行动,一个人必须比哈姆莱特多有一些勇气。”而“插曲”之所以意味深长,就在于赖欣巴哈希望在构建知识的哲学道路上,更多一种“在逻辑的指导下行动”的勇气。
而赖欣巴哈提出“科学哲学的兴起”,就是一种勇气的体现。一直以来不喜欢和形而上学的思辨形成不同路径的分析哲学、逻辑经验论,他们不仅让哲学误入歧途,而且背叛了哲学“爱智慧”的真正追求,而赖欣巴哈之所以提出在哲学探索的道路上一种“勇气意识”,就在于让哲学从思辨走向科学:他的勇气一方面表现在对传统思辨哲学的批判,甚至全盘否定,另一方面则是对科学哲学的构建的大无畏精神,在序言中,他就针对哲学和思辨不能分开、哲学不是一种科学的传统思想,反其道而行之,“写作本书的目的是要指出,哲学已从思辨进展而为科学了。”在他看来,思辨哲学只是探究知识的一种过渡阶段产物,是培根所说的四种幻象中的“剧场幻象”,它像“一片暧昧的雾气”遮住了那些没有受过逻辑分析方法训练的人的眼睛,使他们看不清真正的哲学知识,所以阐述科学哲学就在于消散掉这片雾气,从而让哲学去除错误的根源,并由此而升向真理。
很明显,在赖欣巴哈看来,思辨哲学和科学哲学是完全对立的,那么这种对立体现在什么方面?他提出“问题”引用的是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绪论中的一段话,“理性是实体,也是无限的力,作为一切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基础的它自己的无限物质;它同样也是使物质运动的无限形式。理性是一切事物从中获得存在的实体。”在引用这段话时,隐去了“黑格尔”的名字代之以“一位著名的哲学家”,隐去了《历史哲学讲演录》代之以“著作”,这种隐去本身就是一种不屑;而对于这段话,他认为很多人并不能看懂,即使一遍又一遍阅读,读者也在最后会认为自己“已经懂了”,但实际上在赖欣巴哈看来,懂了无非是自我安慰,之所以让人不懂,是因为其中的表述并不能证明是真的,或者说,表述故意制造了障碍使得阅读的人“不懂”,“如果这是那位哲学家想说的一切,他为什么一定要用神秘的方式来说呢?”
提出这个令人不懂的“问题”,赖欣巴哈就是要指出思辨哲学在对知识的探究上走上了一条完全错误的道路,他认为,“知识的本质是概括。”发现的艺术就是正确概括的艺术——在英语中,“概括”和“普遍性”都是从同一个词根而来,所以“概括”也就意味着寻找普遍性,赖欣巴哈由此得出结论,概括就是“把有关系的因素从无关系的因素中分离出来”,从而达到一种普遍性,这就是知识的开始,所以概括就变成了科学的起源;概括也是解释的本质,解释意味着将观察到的事实归入到一个普遍规律中去,是一种“用推论出来的事物和事件补足直接经验世界的工具”,也就是说,观察到的事实是有限的,是局部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它无法满足求知的欲望,求知只有超越观察才能建立普遍性,解释就是这种作用的体现。赖欣巴哈的这一思路是清晰的,从观察到解释,再到概括,再到建立普遍性的知识,这就是知识的必由之路,但是哲学是不是就是追求这种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知识?“爱智慧”的哲学并不仅仅是一种知识学,而且赖欣巴哈在这里仅仅指事实意义上的知识,外部的知识,如果这是终极目标,那无疑这就是一种科学观,但是和哲学有何关系——甚至还有一种叫“科学哲学”的东西?无疑,哲学就这样变成了科学的婢女,成了科学建构的一种模型,哲学也就失去了它超越知识、超越外部知识、超越科学知识的“爱智慧”的意义。
| 编号:B82·2250616·2320 |
科学哲学和思辨哲学从这里开始了完全的分野,在这个起点上赖欣巴哈就是对哲学的一种误读,所以当科学哲学需要概括时,思辨哲学却用想象来代替它,赖欣巴哈认为想象是一种解释,但不是概括意义上的解释,而是一种类比法的解释,这就是一种假解释:古希腊哲学对本体论的探寻总是建立在创世故事之上,这就是一种假解释;哲学按照心理愿望的满足进行解释,这是将逻辑与诗、理性与比喻、普遍性和类似性相混淆的结果,都是假解释;如果是无害错误形式,还可以在经验的不断发现中得到纠正和改善,而如果用类比来满足解释,那一定是有害错误形式,它所导致的就是空洞的空话和危险的独断论,柏拉图的理念论就是一种诗人的想象,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和内容学说就是假解释的例证,当然黑格尔将理性这样的抽象名词当作一种“实体”,更是一种谬误。想象的、类比的解释是思辨哲学所表现的图像思维,在赖欣巴哈看来,这是一种“逻辑外的动机”,是从逻辑范围以外的精神需要中产生的,并不是逻辑分析的;另外一种非逻辑分析的知识就是从感官获得的知识,它也是不可靠的,而且容易走向神秘主义;唯理论追求确定性,但是它是理性的派生词,当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是用逻辑推理证明了“我在”,但是这也是一种“魔术式的公式”,它只是在思维内部揭示了自我的存在。
近代哲学出现了两种认识论,一种是唯理论,一种则是经验论。唯理论是一种分析演绎,是前提为真情况下的演绎,所以它必定是真的,但是唯理论建立在所谓天赋观念基础之上,它无法产生新的知识,一切都是自明的和空虚的;经验论则是一种基于经验和感性的归纳,它是综合陈述,它不断产生新的知识,但是这种新的知识并不是真的,不能给我们绝对确定的知识——康德认识到了这两种认识论的先天不足,他提出了“先天综合判断”,在赖欣巴哈看来,康德哲学代表了想证明有综合的先天真理的伟大企图,“从历史上说,它代表了唯理论哲学的最后伟大体系。”但是,康德哲学是以绝对空间、绝对时间、绝对的自然决定论为根据建立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在他伟大的同时也导致了失败。同时赖欣巴哈认为,思辨哲学的伦理学也是一种演绎,从柏拉图提出“美德即知识”开始,思辨哲学走向了伦理-认识的平行论,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是在逻辑推导下完成的,康德提出的道德律令也是建立在先天综合判断基础上的,伦理学成为一种认识论无疑也是对知识的一种错误看法。赖欣巴哈对于黑格尔哲学的评价是,他的哲学出发点从来不是科学,而是历史,甚至黑格尔伟大的辩证法在赖欣巴哈那里就是“逻辑戏法”,虽然在这里赖欣巴哈不再用“一位著名的哲学家”来指称黑格尔,但是他将黑格尔放在极低的位置,“黑格尔的体系则是一个狂信者的简陋的虚构,他看到了一条经验论的真理就企图在一切逻辑中最不科学的逻辑之内把它做成为一条逻辑规律。”
|
| 赖欣巴哈:哲学不是一种科学 |
黑格尔代表了十九世纪思辨哲学的没落,而对于经验论,赖欣巴哈认为他们没有使用图像语言,没有追求绝对确定性,也没有试图把认识的知识变成道德指导的基础,虽然没有重复唯理论的错误,但是他们把理性的力量限制在分析之中就陷入了新的困难:“他无法说明经验知识从过去推向未来所使用的方法,即是说,他不能解释知识的预言性质。”实际上,赖欣巴哈为代表的逻辑经验论和传统经验论的区别就在于知识是否具有预言性质,当知识不再只是简单的观察和归纳,当知识的模型变成一种逻辑意义上的预言,那么思辨哲学的经验论就走向了科学哲学的逻辑经验论,而这就是从经典物理学在近代的突破获得的一种哲学方向:经典物理学是通过实验的方法带来了革命,而在实验之外,必须使用数学方法建立科学解释,这就是假设演绎方法的发明,即“被观察到的事实的、以数学假说为形式的解释”。从经验论到逻辑经验论,从数学演算到数学假说的解释,最为关键的就是因果性,因果律表述物理规律,那么物理必然性就可以变换为数学必然性,所以建立在因果性基础上的数学规律不仅是整理的工具,更是预言的工具,它赋予了科学预见未来的力量。
如果说指出传统思辨哲学的错误是一种“破”,那么如何建立科学哲学就变成了赖欣巴哈的“立”——其实赖欣巴哈已经抛弃了哲学,他所谓的科学哲学只是利用了哲学的认识论,让哲学成为科学方法论的模型,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科学,这种科学是建立在和技术相匹敌的逻辑分析基础之上的方法,是以工具思维解决普遍性和确定性知识的实践,是以哲学的方式提出问题而获得条理的体系,“在通向哲学领悟的道路上,科学家是路标的设置者。”逻辑经验论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逻辑分析,一个是经验归纳,两者是如何在结合中构建科学哲学的体系的?赖欣巴哈从康德建立在先天综合判断上的时间观念之“破产”开始阐述,在他看来,时间是人类经验中最突出的特性,感官提供了对时间次序的感知,但是时间如何获得一种客观性?对于时间的表述,一种是计量意义的,时间的年月日时分秒的表述是一种计量,它只是均匀时间中的一个“同格定义”;而时间的次序就是因果关系,即使这里的因果性并不意味着真正关系的发生,但是先后次序是通过“同时性”定义而完成的,时间计量的同格,时间次序的同时性,使得时间不再是柏拉图所说通过洞见来感知的东西,也不是康德所相信的是人类夹在世界上的一种主观秩序形式,而是一种因果流的结构,这种让时间从感受、主观性中抽离出来而具有客观性的方法,就是科学哲学的方法,“为了进行逻辑分析,科学须与感性内容分离开。”
时间的次序就是建立在因果性之上的一种关系,赖欣巴哈提出因果性的哲学就是科学哲学,它是“如果-那么”的关系,要让“如果-那么”在任何时候都有效,都具有普遍性,那就是要正确处理好概率规律,这就是概率蕴涵,甚至因果结构中最重要的恰恰是这个概率结构,“物理世界的因果结构为概率结构所代替,对于物理世界的理解就以一种概率理论的建立为前提了。”赖欣巴哈通过对量子理论和进化论的回顾,就指出了因果性中的概率的特殊意义,尤其是通过逻辑分析处理概率问题,其实就是科学哲学真正的概括,“逻辑是哲学的技术部分;正由于此,它是哲学家所不可或缺的。”这种逻辑不是在唯理论那里是空洞的、自明的逻辑分析,而是使用归纳演算的归纳逻辑,但是和经验论的纯粹观察不同,归纳逻辑使用的归纳法针对的是超出以前观察总结之外的东西,只有这样,归纳法才能发现新的东西,归纳推论才能成为预言性知识的工具。
从观察中进行归纳寻找观察之外的东西,并对知识进行预言,要达到这一步,就必须通过概率理论发现将会发生的事,也就是把或然的事变成确定的事,这就是“假定”,它的重要性就在于,“假定是未能获致真理时的行动工具”,但是它唯一的方向和目标就是获得真理,所以在这条科学哲学之路上,赖欣巴哈总结说:“一切知识都是概率性知识,只能以假定的意义被确认;归纳法就是找到最佳假定的工具。”通过概率来假定,通过假定获得真理,真理在赖欣巴哈那里也并非是和事实完全相符的真,而是赋予了真一种意义,也就是说,真理就是具有真理性的意义,在这个基础上说,通过假定通达真理的说法就是“意义的可证实性”,它是科学哲学不可或缺的部分:在语言的使用中,真句子就变成了有意义的句子,作为符号的记号就发挥了预言工具的性质,它就成为了知识;对于世界的认识,意义的可证实性也破除了现象和自在之物的二元对立,使得经验具有了一种逻辑实证性;当然最重要的时,伦理学不再是先天综合真理,它让真理变成了指令,而指令在意义的可证实性中就具有了“工具意义”,所以伦理学就变成了和哲学无关的意义存在,“用你的耳朵倾听你自己的意志说什么,并努力设法把你的意志和别人的意志结合起来。”
通过对思辨哲学之破和科学哲学之立,赖欣巴哈认为哲学由此进入到了新时期,甚至是通过一种哥白尼式革命进入到了属于它的时代:哲学不再企图用图像语言进行伪解释,不再“说不可说的东西”,不再追求绝对真理,它追求的是经验知识,它运用的是归纳逻辑,它寻求的是最好的假定,它通达的是意义,就方法论而言,它就是科学的,“它坚持真理问题必须在哲学中提出,其意义与在科学中提出一样。”于是科学哲学其实就已经在赖欣巴哈的阐述中变成了科学方法论,这是一种对思辨哲学的否定,更是对哲学观念的挑战,建立在否定和挑战之上的构建需要的就是哈姆雷特所没有的巨大勇气,就是从错误到真理的“意义的可证实性”:“如果错误一被认出为错误就得到纠正,那么错误的道路也就是真理的道路了。”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