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7-27《路标》:只在途中向思想显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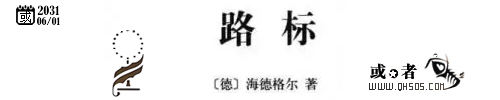
形而上学本身唤起并且加固了一个假象,仿佛它追问并且解答了存在问题似的。而事实上,形而上学绝没有回答存在之真理的问题,因为它从未追问过这个问题。
——《<形而上学是什么?>导言》
为什么形而上学说出了存在却是“加固了一个假象”?为什么形而上学通过对存在者的思考追问存在,追问本身却充当了界限?为什么形而上学把存在者放在优先位置却带来存在本身的遗忘?对于形而上学的诸多“为什么”才是海德格尔提出“形而上学是什么?”的问题,才是海德格尔在提出问题后开展了讨论和讲座,而疑问变质疑,质疑需要回答,就回到了海德格尔的真正目的:回到形而上学的基础。
形而上学的基础其实也是哲学的基础,而哲学的问题也是形而上学的问题。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绝不逃脱它的基础,但是它总是离开它的基础,而且就是通过形而上学之力而离开它的基础的,这种离开是思想的必然,因为通过踏上一条“经验形而上学之基础”的道路,思想开始尝试思及存在本身之真理,而不仅仅把存在者表象为存在者,那么思想就离开了形而上学。所以这里的一个问题是,形而上学遇到了一种困境,那就是它根本没有回答存在之真理的问题,甚至从未真正追问过这个问题,它只是“通过把存在者表象为存在者而去思考存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存在者只是以一种“指引”的方式对存在者进行思考,它实际上只是充当了界限,阻挡了存在与人之本质的原初关联,使得思想进入到一个渊源之中,而形而上学在本质上思考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是应该像光一样自身显现的。
那道显现的光就是真理本身,所以开设《形而上学是什么?》的讲座,海德格尔就表示其目的是进行一番透彻的思考:从形而上学最终的目的出发,“而不是从某个幻想出来的目的出发”,也就是说不是以习惯的方式思考形而上学,而是“从形而上学的本质和真理而来思及存在之真理”。这个目的在《<形而上学是什么?>后记》中,海德格尔用另一种方式表达,对“什么是形而上学?”的追问必须越出形而上学之外,也就是要深入到对形而上学的克服中去,这种超越和克服就在于在另一个时机里被探讨,那就是:“它必须以诸科学为出发点。”这个诸科学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那就是现象学,或者说海德格尔那时所说的现象学就是科学,他在《现象学与神学》一文中,就谈到了科学的时机,“科学是为被揭示状态本身之故对某个向来自足的存在者领域或者存在领域的有所论证的揭示。”他就是将这种揭示用在对神学与哲学关系的探讨中。
在一般的观点中,神学和哲学的关系就是信仰与知识、启示与理性的关系,由于哲学远离信仰和启示,神学合乎信仰和启示,所以两者既是分离的也是对立的,但是这种关系是在世界观的信念中裁定的,而并非是由科学来决定的,所以海德格尔通过科学的揭示来裁定它们的可能关系。既然科学的目的是揭示自足的存在者领域,那么科学就是理解此在的一种可能性,科学的可能性包含两方面:存在者的各门科学和关于存在的这一门科学,在存在者状态上的科学就是把现成的存在者当做客体,而这个现成存在者的科学就是关于某个实在的科学,这就是实证科学;而作为存在的科学,即存在学,是从存在者转向存在,并且将存在者保持在目光中。海德格尔认为,神学就是一门实证科学,也正由于此,神学与哲学绝对地区分开来——为什么神学是一门实证科学?海德格尔从三方面来揭示这一结论:第一神学具有实证性,神学本身属于基督教历史,也为这种历史所拥有,又规定着历史本身,神学现成的东西即实在就是基督性,所以信仰就是一种人类此在的实存方式,是始终在信仰上理解自己的信仰,“这一存在者为信仰所揭示,而且信仰本身归属于这一以信仰方式被揭示的存在者的这一发生联系中。”这就是神学具有的实证性。
第二,神学具有科学性,神学是关于在信仰中被揭示的东西的科学,神学是关于信仰行为本身的科学,所以神学就是信仰的科学,它使信仰及其所信的东西成为对象,并且从中获得理由,而且神学具有实证性,神学就是一门历史科学,在这个意义上,神学是系统的、历史学的、实践的科学,它当然具有科学性。神学具有实证性和科学性,虽然信仰不需要哲学,但是作为实证科学的信仰科学却需要哲学,海德格尔认为,“哲学乃是对神学基本概念的存在者状态上的、而且前基督教的内涵所作的可能的、形式显示着的存在学调校。”也就是说,神学和哲学的关系就体现为这种调校,它是对此在的信仰状态和自由的实存状态之间矛盾的调校,但是仅仅是形式上的调校,哲学作为只能是它所是的东西并不能真正充当调校的角色,海德格尔将所谓“基督教哲学”形容为一个“方的圆”。
“方的圆”无疑在形式意义还是在本质意义上都是不存在的,但是海德格尔在科学的时机中却揭示了神学和哲学共在的可能性,这是海德格尔在现象学的理论中揭示的东西,而在更早的时候,他在评评述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世界观的心理学》一书中,也阐述了现象学的方法。《世界观的心理学》初版于1919年,是雅斯贝尔斯在海德堡大学的讲课稿,1921年海德格尔对此书进行了评论,雅斯贝尔斯本人认为海德格尔是“唯一知道我尚不完善之处的专业同仁”,海德格尔是如何发现雅斯贝尔斯在其中“不完善之处”的?海德格尔在评价这本书时,首先认为雅斯贝尔斯对谋求一种心理学整体作出了努力,它让人认识到“人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这是一种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心灵-精神生活的基本力量和倾向的审视性理解和明察。”这种整体观心理学,在海德格尔看来具有“哲学的”倾向,因为它提供了“作为世界观的自我沉思之手段的那些澄清和可能性”,这就具有对悬而未决的、无视差异的、调解一切的混合主义的拒绝,而这就是真正的批判,在海德格尔看来,批判就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现象学批判。
但是海德格尔也看到了这种现象学的批判在雅斯贝尔斯的作品中的“不完善之处”,原因就在于雅斯贝尔斯的方法是建立在先行把握之中的,是建立在对作为领域的生命的设定之中,建立在作为考察的对于生命的态度之中,而生命是一个无限流动的整体,当雅思贝尔斯以概念表达的方式考察生命,就是使生命停滞了,就不可能真正把握生命,“他就落入一种欺瞒中了。”雅斯贝尔斯的“不完善之处”就在于他对真正的方法难题错认和低估了,而真正的方法就是用“具体科学的态度”着手处理世界观和心理学问题,认清普遍的心理学与世界观的心理学不能互相替换,也不能与原则性的哲学难题分开。从科学对神学和哲学问题的揭示,从科学对自我沉思的可能性的提供,从现象学批判是真正意义上的批判,海德格尔所强调的“诸科学为出发点”的时机其实就是一种超越和克服,而它同样用在“形而上学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追问中。
| 编号:B82·2240422·2109 |
海德格尔进入追问,首先描绘了折中追问的双重特征,一方面问题总是呈现为整体本身,那么追问就必须与追问者的问题共在,也就是说追问者必须被置入在问题中,这种追问就是科学的方法,“在一切科学中,当我们追踪它们的最本己的意图时,我们是与存在者本身相对待。”此在就以一种“动人的质朴性和鲜明性带入科学的实存之中”,世界关联、态度和突破就实现了统一性,也就是存在者本身,那么存在者本身之外再无什么。在这里,海德格尔就开始了真正的追问:当再无什么,那么无是什么?在他看来,科学不愿知道无,但是科学在寻求本质的时候却只能求助于无,科学不愿知道却又必须为科学所用,无到底是什么?海德格尔开始了追问的“问题之制订”:什么是无这个问题本身就走向了它的反面,因为它剥夺了问题的对象:追问必须事先被给予。对无的给予就是畏,“畏启示无。”畏使我们漂浮,畏使存在者整体脱落,畏使我们无言——面对无,任何关于存在的言说都沉默了,也就是在这沉默中,无得以敞开,在这敞开中才能被追问——也就是说,无在畏中簇拥此在才是无的本质,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无化”,“无化既不是对存在者的消灭,它也不是从一种否定中产生的。无化也不能归结为消灭和否定。”
无化是无之源始的可敞开状态,人之此在才能走向存在者并深入到存在者那里,所以关于无的问题,海德格尔给出了答案,“无既不是一个对象,也根本不是一个存在者。无既不自为地出现,也不出现在它仿佛与之亦步亦趋的那个存在者之旁。”无是一种可能性,是使存在者作为存在者得以为人的此在敞开出来。而无的追问就体现了对形而上学本身的追问,形而上学问题包括的是形而上学整体,对形而上学进行追问的存在也要置入到问题中,所以形而上学的命题就是一个无的命题:“从无生无。”这个命题的意思是:“从无中生出一切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所以形而上学就是把追问者置入问题的整体,把人之此在嵌入无中,在无中生无中超出存在者并成为此在之本质,而这种超出就是形而上学本身,一句话,“形而上学是此在中的一种基本发生。形而上学就是此在本身。”形而上学运转起来,哲学才能真正获得自身,这就是一种“跳跃”——追问在形而上学之外,是对形而上学的克服,是以诸科学为出发点。
对于形而上学以诸科学为出发点的跳跃,海德格尔在1928年作了《什么是形而上学?》的讲座同时,也写作了《论根据的本质》一文,如果《什么是形而上学?》是对无的思索,那么《论根据的本质》则是一种存在学差异,而它们都指向了“超越”。无是对存在者的不,而存在学差异则是存在者和存在之间的不,这个不所表现的就是“根据的本质”。亚里士多德把全部本原的共同点看成是“存在或生成或认识由之开始之点”,这就是“根据”的各个变式:是什么存在的根据、如此存在的根据和真实存在的根据,而根据的共性就是亚里士多德的“第一起源”,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就是“根据”,海德格尔认为,根据问题所凸显的就是超越,或者说根据之本质就是超越问题,“超越乃是这样一种超逾,这种超逾使得诸如一般实存之类的东西成为可能,因此也使一种在空间中的‘自行’运动成为可能。”
超越使实存成为可能,而主体之存在就是超越,“这个存在者在超越中并且作为超越而存在。”从存在的本体论问题变成了主体的问题,海德格尔认为,主体的存在作为一种超越,是人之此在所具有的,“世界恰恰归属于人之此在,虽然世界涵括一切存在者,也一并整个地涵括着此在。”人之此在是人作为处身于存在者中间、对存在者有所作为的存在者在此实存着,这使得存在者始终在整体上是可敞开的,使得存在者在超越中才能获得光照。进一步,海德格尔认为,对世界的超越就是自由本身,“自由乃是向着根据的自由。”此在的有限性也在作为向着根据的自由的超越中而揭示出自身。当此在在自由的超越中揭示自身,当自身在敞开状态中成为本质,存在学差异的“不”和形而上学的“无”就构成了海德格尔关于真理本质的阐述,“着眼于真理的本质,自由的本质显示自身为进入存在者之被解蔽状态的展开。”从遮蔽到敞开,就是解蔽,而对存在者的解蔽就是真理,海德格尔在《论真理的本质》一文中就说:“一切人类行为和姿态都在它的敞开域中展开。因此,人乃以绽出之实存的方式存在。”
形而上学的追问其实就变成了关于真理之解蔽,关于实存之绽出——海德格尔认为,这种解蔽和绽出在柏拉图的理论中也得到了体现。他在《柏拉图的真理学说》中重新审视了洞穴学说,他认为洞穴的种种比喻说明的就是一个“造形”的本质:理念存在于洞穴之外,是关于事物、生物、人类、数字、诸神的外观,如果没有这些外观,各种东西都无法被感知为一座房子、一棵树、一位神,理念的造形就是一种本真的解放,它让一切在外观中显现出来,“最无蔽者就是最真实者,亦即本真的真理。”而最高的理念就是善,柏拉图认为善的理念是“给予无蔽状态而又给予觉知的主宰”,当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对于柏拉图来说,就在于让形而上学变成了“对于人之存在以及人在存在者中间的地位的努力关注”,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的真理学说体现的就是形而上学的一次转向:形而上学就是人道主义——人从“理性的动物”的规定变成了对其可能性的释放,对其使命的确知性,对其“生命”的保障,也就是说,形而上学的规定围绕着人的旋转,而形而上学的完成就标志着人道主义达到了最极端的“地位”上。
《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海德格尔深入阐述了形而上学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人道主义就是人道的人,就是人道的人所体现的人性和人道,“人之人性就在人之本质中。”而形而上学从来不无视这样的本质,也就是从人之本质如何被规定方面,一切形而上学都是“人道主义的”,相应的,任何一种人道主义也都是形而上学的:人在其本质中才成其为本质,这是人的居有,本质的绽出,或者海德格尔从解蔽和敞开的角度来说,人是被存在本身“抛入”存在之真理中的,“人在如此这般绽出地实存之际守护着存在之真理,以便存在者作为它所是的存在者在存在之光中显现出来。”所以人之人性规定成为绽出质实存,它的本质性东西并不是人,而是存在,是作为绽出质实存的绽出状态维度的存在,所以人作为一个存在者,“人是存在之邻居。”
从对形而上学的追问到人道主义的阐述,从对存在者的超越到对真理本质的探寻,“诸科学”作为出发点也成为海德格尔的一种本体论思想,“现在是时候了,人们必须戒除这样一种习惯:高估哲学并因而对哲学要求过高。”在从现象学的科学出发的这个思想之路上,海德格尔无疑将这些都变成了“路标”,路标的意义就在于:“这条道路只在途中向思想显露出来——既显示又隐匿。”一路上的思想路标既显示又隐匿,是不是也是一种解蔽的可能?是不是也是对于存在的敞开?海德格尔在1967年的《前言》中把自己看成是“老者最老者”,这是一种对自身的规定,它必然走向思想之实事,“这种规定并不带来什么新鲜东西。”但是在敞开中,在超越中,在解蔽中,路标的真正意义是“要求那种在持续地被寻求的同一者之同一性中的逗留”。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6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