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8-03《论运动图画》:透过它们看见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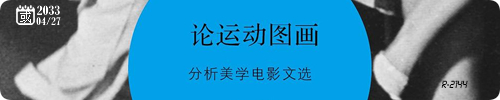
摄影机的运动不是我们的运动,而其效果恰恰是将我们推到场幕之外,让我们回到形而上学的笛卡尔之洞中。
——阿瑟·丹托《论运动图画》
摄影机“拍摄”而成为一部电影,运动一定是摄影机的运动,也一定是电影所表现的运动,但是摄影机制造的“运动图画”却不简单只是一种运动:摄影机的运动打开了一个新的维度,它让对象运动,恰好与摄影机的静止形成了运动;当摄影机运动,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自己的运动”的经验;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运动的摄影机带来了一种革命,它使得摄影机的记录模式成为记录的一部分,而在记录中把摄影机的艺术“推到了影像之中”,当记录把艺术“推到影像之中”,而我们的运动又在经验层面被推到了“场幕之外”,内和外构成了分析哲学最重要的一种阐释,阿瑟·丹托将之看成是电影“自我意识”的形成,也就是说,电影以某种方式成为其自身的对象,“它给予我们的不仅是一个对象,也是关于那个对象的一个知觉;一个世界,连同看那个世界的一种方式。”
这就是电影看和被看的双重意义,“在这个艺术作品中,艺术家的观看模式,与被观看的东西同样重要。”当自我意识成为了自身的一个对象,我们就在它之外而看,并用其他诸意识关联于整个世界。这是丹托在1979年的文论《论运动图画》中提出的一个观点,这篇文章的标题也正是这部“分析美学电影文选”的书名,在这个意义上,丹托也是作为分析美学的代表人物对电影这一“运动图画”进行分析阐述。在这片文章中,丹托所论述的并非是一个问题,而是在泛论的意义上分析了电影的本质。他首先把电影院看成是教堂的某种变体,坐在影院里的观众就是不属于教会的集会人员的变体,从分析哲学来看,每一个观众都是作为一个观众成员的“函项”——早期分析哲学家弗雷格就把“概念”视为一种特殊的函项,它对每一个变项都有一个真值,函项是不完全的,但是当确定的专名对之进行填充,就得到了真值,所以每一个观众对电影的反应就是作为观众成员的一个变项。
但是当我们作为函项中的变项,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们能看进去电影但又无法进入真正的电影物理空间,也就是说,电影是一种盒子,一面透视镜,电影空间就是那个镜中世界,它在逻辑上将观众排斥在它所占据的空间和时间之外,所以这样的看类似于普鲁斯特的视角,他所实践的是一种窥探,以一种外在于人生的视点,讲人生视为一个整体,“从外面向里面观看”,从而把人生变容位艺术,这是看的一层含义;但是电影艺术和普鲁斯特幻想的戏剧又有不同,丹托指出,在戏剧中,同一部戏剧可以有不同场次的演出,这个多就是一种诸殊相,而戏剧本身是理念,也就是说这接近于柏拉图所说多是对理念的分有,但是电影的诸多放映和同一部电影的关系,则是原本和副本之间的关系,更接近于亚里士多德“类”的设想,“类”是基于事物之中的相似性;但是电影这种诸多副本又和绘画不同,绘画的诸多副本完全是一种复制,但是电影的两次放映并非是彼此的复制,这反而和照片与其底片之间的关系,按照本雅明的观点,就是“可机械复制的类型”,这是看的另一层含义;和绘画、照片相比,电影又和戏剧更具亲近性,这里的亲近性在本质上就是时间性,也就是说,电影是具有时间性的,照片和绘画是不具有时间性的。
丹托把时间性看成是电影的一种本质属性,也由此进入到一个关于“运动图画”一个最关键的进口,他举例说,有两种放映,一种是将一张幻灯片放映8个小时,虽然这里有时间,但幻灯片包括它所呈现的影像不具有时间性,它只是静态的一种照片;另一种则是从头到尾放映一张以图片作为封面的电影8个小时,同样是8小时,也同样是不变的照片,但是它是一部电影,尽管它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是她已经超出了幻灯仅仅在逻辑上被决定而成为艺术家的某种意图,这种意图中就有了时间性的“运动”。幻灯和电影的这种差异,丹托举例了艺术作品和现实对象之间的差异,虽然艺术作品和现实事物在外观上看起来完全一样,但是艺术作品已经不再是现实事物,电影和戏剧也不是现实事物,是“假的”,但是它们却服从描述,同样,幻灯作为“是运动的”这一描述是假的,因为画面中没有运动,而电影中,事物是运动的。
关于幻灯和电影的区别,丹托继续深入,他举例说有一个“关于一出戏剧的电影”,比如是关于《哈姆雷特》戏剧的电影版本,还有一个是摄制的银幕剧,是一部关于《哈姆雷特》舞台剧版本的电影摄制,他们看起来具有相似性,或者说都和电影有关,但是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前者中它是电影,是关于戏剧的电影,戏剧是在电影之中的,戏剧在电影化中得到再现,“它是关于一部特殊戏剧的特殊展演,无论什么都隶属于那出戏本身。”而后者是被拍摄下来的舞台剧,戏剧是电影之外的实存——不管有没有通过摄影机记录下来,它在原则上都会发生,按照实在论的认识论,它就在那儿,不管我们能否感知它,它都是确定不变的。正是有这样的本质区别,它带来了关于看的本质差异:看一出戏就是看一部电影,它是一种“使用”,而看一出被摄制成电影的戏剧,就是一种“提及”,“使用”所指的是某个东西,而“提及”是谈这个词本身。
| 编号:Y22·2250616·2318 |
电影是“运动图画”,它不仅仅是关于运动之物的图画,即使关于实际上静止不动的对象,也是一种运动图像,比如喜马拉雅山,所以运动之物的再现,本身不必是一个运动的再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电影作为运动的图画,它的再现就意味着:“我们不仅是看见它们在运动;我们还看见它们运动着。”我们不仅看见它们运动着,而且是关于我们自己的运动的经验,这就是看与被看在运动意义上实现了一种革命:不是“关于制作电影的电影”,而是“其自身的制作是其所关于的对象的电影”,在丹托看来,只有后者才是从艺术向哲学的转变,“它不仅展示它所展示的东西,还展示它在被展示这一事实。”也就是说,电影不仅给予我们一个对象,也是关于对象的知觉,看同时是被看,意识同样把意识的自我意识当做对象,“我们无论以何种方式意识到自我意识,自我意识都不是自身的一个对象,当它成为一个对象时,我们就已在它之外,并用当下透明得无可救药的其他诸意识模式关联于世界。”
丹托不仅对“看”进行了语义学的分析,还在知觉经验意义上建立了看的模式,当看既成为自我意识的过程,也把自我意识看成是意识的对象,在知觉经验上就变成了“看那个世界”的一种方式,并与世界相关联。所以他在2001年发表的《看与展示》中,就对“眼睛本身和人的知识本身都同样是历史性的”这个论点进行了驳斥,在他看来,眼睛看是一种视觉系统的看,它有看的可塑性,但是可塑性并不强,或者说眼睛作为视觉器官的看,是对符号标识系统的看,“看”是不变的,它无法完成解释学中关于“制作与符合”的功能:艺术家通过“看”来检测“展示”,从而进行调整,直到“展示”符合所看的东西。这种“制作与符合”的观念就是基于眼睛是历史性的存在,就是建立在看具有可塑性的建构之上。“眼睛具有的是一个进化历程而不是历史。它是通过突变而变化,而不是通过历史性转换。”丹托提出这样的反驳,就是把眼睛仅仅当做一个视觉器官,而真正的看应该是一种知觉意义上的,所以对于那种观点的纠正就是:“眼睛不是历史性的,但我们是历史性的。艺术哲学由此开始。”
我们是历史性的,也就意味着我们在知觉意义、在将自我意识作为意识的对象的“看”,才是一种再现,而要从“最小视觉经验”的眼睛之看,到“识别最大描述语之下的事物”的看,就需要语言,那么这种“看”的语言在电影中具有怎样的特点?肯达尔·沃尔顿1984年发表了《透明的图像:论摄影写实主义的本质》一文,指出了图像具有的本质特点就是“透明”——在这里“图像”并非是对丹托静止性“图画”说辞的一种修正,无论是图画还是图像,其实都是对于电影的一种本质解读,而沃尔顿的标题本身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图像是透明的,这种透明揭示的正是“摄影写实主义”的本质。关于摄影写实主义,沃尔顿引用了安德烈·巴赞在《摄影影像的本体论》上的一句话:“摄影影像就是对象自身。”这句话扩充的引用就是:“影像可能模糊不清,畸变褪色,失去记录价值,但是它毕竟产生了被拍摄物的本体,影像就是这件被拍摄物。”
照片拍摄对象,对象成为图像,这就是一种写实主义,但是摄影写实主义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风格上的“写实”,按照巴赞的说法,照片拍下的对象就是对象本身,也就是说图像和对象具有同一性。与照片不同,绘画也是对对象的一种摹写和创造,但是绘画中的对象如何真实,看起来如何想象,它也无法具有同一性,它所具有的只是相似性。照片和对象具有的同一性是更具本质的“写实”,而这种写实带来的是关于看的全新方式,那就是:“摄影是透明的,我们透过摄影看世界。”透过写实的照片,我们看见了已故的亲人,这是一种真正的感知,“我们所看的是照片,但我们确实看见了那个被摄对象;因此,照片和对象之间一定在某种意义上是同一的。”即使照片是模糊的,是扭曲的,在和对象同一性中,摄影就成为了一种再现。电影也一样,电影也是一种透明的图像,我们透过电影看见影像就是世界——即使和照片一样无法避免错觉,“但这有什么要紧呢?当我们直接看事物时,我们也可能被欺骗。如果照相机会说谎,我们的眼睛也会。”
摄影写实主义的这一本质,在沃尔顿看来,是因为“某物以某种纯机械方式所因致的视觉经验”,它构成了看见的含义,通过视觉经验,我们透过照片看见了对象,我们诠释照片获得了事实,更重要的是,我们和世界形成了感知接触,“这就是摄影的透明性——它是最为独特的摄影性,它构成了‘摄影写实主义’的说法之正当性的最重要证明。”对于沃尔顿的这一观点,诺埃尔·卡罗尔提出了反驳,他在1996年的论文《定义运动图像》中提出了巴赞早就提出过的问题:电影是什么?这个问题指向了电影的本体,但是卡罗尔显然反对所谓的“媒介本质主义”的提法,在他看来,“媒介本质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假命题,电影不是一种媒介,电影也没有所谓教条式的“本质主义”,他认为只有在“类”的意义上来回答“电影是什么?”才是恰当的,而这个“类”就是“运动图像”。
虽然和沃尔顿的说法一样,但是卡罗尔对于电影这一“运动图像”的阐述完全站在沃尔顿的对立面,一方面,沃尔顿把电影也看成是写实主义的摄影,但是现在的电影早就脱离了单纯的“摄影”,即使从摄影来说,也在技术的发展中数码化了,那些对象和摄影图像已经不构成同一性了;其次,沃尔顿把我照片看成是和望远镜一样是视觉辅助装置,但是卡罗尔认为照片和电影图像不是提供直接地看的透明呈现的实例,它们根本和望远镜这类装置不同,所以所谓的“透过”也是不能成立的。卡罗尔的论点其实就在于否定沃尔顿所说的摄影写实主义,从而驳斥图像和对象具有同一性,他提出的观点是:所有的照片和电影都是“分离的显示”,图像不是再现,而是一种对对象的呈现,“只有当某物是分离的显示时,它才是一个运动图像。”分离的显示提供了一个基于图像本身的视觉阵列,图像和视觉在“疏离”中被看见,这种看见所形成的才是“运动图像”。
但是,和卡罗尔对沃尔顿的批评不同,格里高利·居里在《新电影理论批评》中也认为电影是运动的图像,“运动的图像是电影的本质。”也同意沃尔顿认为电影的图像是写实的,它与对象是再现关系,并从心理学上构建了这一理论,所以,居里把观看电影所获得的体验因为和正式世界获得的体验相近,他称之为“知觉写实主义”,他否定看电影的“幻觉说”,那只不过是电影公司作的宣传,而知觉写实主义的意义就在于使得电影成为了既是时间上也是空间上的媒介,“电影通过空间的手段来表现空间;通过时间的手段来表现时间。”这就是电影的实在论。无论是沃尔顿提出的“图像是透明”的摄影写实主义,还是居里阐述的“知觉写实主义”,都试图回答“电影是什么?”这一本质的问题,都在围绕着看电影和看世界的同构进行阐述,但是电影图像真的和照片一样是再现?电影真的和对象是同一性关系?我们的看真的是一种“透过”?
沃尔顿在《吓人的虚构》中直接进入到看电影的体验之中,当观众在观看一部恐怖片时陷入生理和心理的恐慌,他透过图像看到了怎样的世界?他的恐慌又和什么具有同一性?沃尔顿认为这种感受和我们看小说、戏剧时一样,是“情感上的陷入”,他将这种陷入称为“假装游戏”:他把银幕上的影像当成道具,自己则成为了一个扮演自己的演员;观众的感受是私人意义上的,所以假装游戏也必定是在私人意义上的,这就需要一种内省;这种内省既需要对自己的感觉“优先了解”,又必须让自己成为“外在的观察者”,从而在真实世界和虚构世界中建立联系,“他通过内省而了解自己的假装恐惧的过程,正像是一个真正害怕的人了解自己真正的恐惧的过程一样。”这就是沃尔顿所说的同一性、再现和“透过”,但是这里的问题是,这一切在虚构世界里发生,它是不是本身就取消了写实主义?这是一种“假装游戏”,是和梦一样的存在,它的意义是对特定情境、介入行为和感受的感受,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所谓的看是不是反倒变成了幻觉?电影图像不是摄影照片,它已经变成了一种相似性意义上的戏剧,“我们仅仅是站在虚构世界之外向里面看,把鼻子贴在一道不可凌越的栅栏上朝里面张望。一旦意识到我们出现在虚构世界内部,似乎就能够得出合理的解释。”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4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