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0-26《莫恩先生的悲剧》:你天生是爱的比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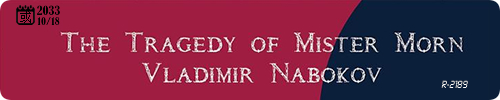
世俗的生活是神圣原型的一个译本,模模糊糊;思想大致清楚,可原来的曲调在字词中大半损失……激情是什么?翻译中的错误。爱情是什么?是我们不和谐的语言在传输中失去的韵律……我该回归原初!
——《第四幕》
激情是翻译中的错误,爱情是传输中失去的韵律,它们原本都是展现力与美的存在,但是在“翻译”和“传输”的过程中变成了缺失的东西,而这一切的“原本”和在过程中失去的东西构成了矛盾,它们就是世俗生活和神圣原型之间永远不对位的关系:世俗生活是神圣原型的一个一本,但是最后在原来曲调的损失中变成了模模糊糊的存在——当加纳斯在埃拉面前呼喊着“我该回归原初”,就是回到激情和爱情构筑的世俗生活中,就是回到对神圣原型的一种完美投射之中,就是回到不被损失的原调中,但是,加纳斯的呼喊有多少强烈,就有多少绝望,最后在“脱离战火,脱离怒火,脱离饥渴的梦想”中,选择了去修道院了却余生。
但是,当他对埃拉说起自己修道院的生活,“我知道一个修道院,有清凉的紫藤缠绕。我将在那里生活;透过彩虹玻璃窗我会注视上帝,听着风琴的鸣唱将世俗的灵魂吹到胜利的高度,思想徒劳的伟业,想到一个英雄,他在黑蒙蒙沉睡的桃金娘丛中祈祷,蒙难地的萤火虫将他拥抱……”这是一种对神圣原型的回归?还是跌入到另一个绝望的世界?第四幕第二场加纳斯的这句话也许是解读纳博科夫这一文本的一把钥匙,1923年,24岁的纳博科夫创作了这部五幕剧,这也是他文学生涯的第一部重要作品,但是他并没有将这部作品出版,直到他去世20年后即1997年,这部戏剧作品才重见天日,俄罗斯文学刊物全文刊出,2008年成书出版。生前创作却搁置于箱底,这是一种隐藏,甚至在去世之前也未曾想要了却这一心愿,如此说来,纳博科夫的确不愿让这部作品被人读到,永远沉默是它最好的归宿。
但是它却被发现、被出版、被阅读了,这是不是违背了纳博科夫的初衷?甚至在重见天日之后,文本依然保留着“死亡”的痕迹:第五幕的第二场,莫恩、艾德明、外国人和其他客人在一起,当女士对“那位绅士”说“走吧,我害怕”之后便是俄文原本中遗失的部分,这个说自己不是埃拉的女士对绅士到底说了什么?她害怕的是又是什么?之后“国王”对她说:“梦一旦中断,便无法再续,在梦中,我眼前飘浮的王国突然变成静立于大地之上。……是的,梦总是虚幻的,都是谎言,谎言。”但是剧本的原本又突然从“国王”变回了了“莫恩”,也再没有从莫恩转回国王,那么从国王转向莫恩的过程中,是不是也遗失了一些东西?英译本注解的这几处原本中遗失的部分应该不是纳博科夫在创作中故意设置的,不是如艾德明那样在莫恩自杀后选择隐瞒真相,“绝不能让人看到我的国王如何向上天报告,莫恩先生的死讯。”
原本中遗失,只能是文本诞生之后在漫长过程中技术性的遗失、历史性的仪式,甚至就是从神圣原型变成世俗生活之后,包裹着激情和爱情,在翻译和传输中失去的东西,而这也证明了纳博科夫根本不想成为一种被人阅读的读物。从1923年完成创作到1997年出版发行,这部作品走过了54年,这54年囊括了一个伟大创作者流亡、偷渡、改国籍以及逝去的全过程,这54年甚至见证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初生到壮大、从称霸到解体的曲折历史,在个体之履历和国家之历史的双重沉浮中,一部五幕剧如何能避开这可能遗失和失去的危险?但是为什么纳博科夫在24岁时创作完成后将它搁置在历史深处保持永远的沉默?1924年之前的纳博科夫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之后随着家人离开俄国前往克里米亚,在朋友家中暂住18个月后忧郁白军反扑失败,一家人离开克里米亚前往欧洲西部,开始了真正的流亡生活;1919年纳博科夫一家在英国定居,纳博科夫成为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学生,开始学习其他斯拉夫语和罗曼语;1922年纳博科夫一家住在柏林,他以私人身份教授英语、法语以及网球、拳击等,就在这一年,纳博科夫的父亲在柏林被俄罗斯君主制主义分子刺杀,原因是他掩护了他们真正的目标,一位拥护宪法的在野党领袖鲍威尔·米留科夫;1923年,纳博科夫接受剑桥大学法文与俄文学位,开始用弗拉基米尔·西林的笔名写作,也就是在这一年创作了这部《莫恩先生的悲剧》,同一年与纳博科夫已经订婚的斯维特拉娜西撕毁了婚约,因为她的父母认为他不能照料好他,几个月后纳博科夫在柏林一个化妆慈善舞会上邂逅了犹太律师之女薇拉,两人最终在1925年成婚。
之后纳博科夫的经历当然和这部五幕剧无关,纳博科夫在1923年完成创作,这部戏剧也一定和发生的这一切相关,这里有政局的动荡,有被迫的流亡,有撕毁的婚约,有革命和反革命的风暴,有父亲被误杀的恐惧——尤其是父亲被误杀之后反反复复出现在纳博科夫的文本中,《微暗的火》中,约翰·席德就是因为被错认为赞巴拉国的流亡国王而被刺杀。梳理纳博科夫1923年以及之前的种种经历,也许能找到这部戏剧“遗失”部分的入口,更能发现纳博科夫选择让其沉默的原因。从剧本的故事来看,是一个和国家政治有关的故事,它构筑了革命与反革命、国王和造反派之间的二元对立,而这也是纳博科夫对当时俄罗斯动荡政局的一个体现。以特拉门斯为首的造反派在这四年时间里发动暴动,他们进攻广场,他们刺杀国王,他们号召人们,为的就是推翻国王统治,为的就是建立新的王国,但是这个王国在国王的带领下,“创造了一个幸福的时代、和谐的时代……”按照莫恩的说法,“这是上帝给我力量”。那么,特拉门斯的造反又有什么意义?
| 编号:X44·2250922·2363 |
在这四年里,加纳斯离开了妻子米迪亚加入特拉门斯的造反派,进行着反革命活动,当他在四年后回到特拉门斯那里,质问的是:“告诉我,我不明白:你想要什么?”在他看来,这个国家在战争和革命之后,四年来歌舞升平,国家已经变得非常强大,而这一切就是国王以一己之力完成的,“你还要什么?”的质问就是对所谓造反的质疑,而在第二幕中,造反者登场,他们同样在质疑造反的意义,第一个说,“我们累了,一脸迷茫……特拉门斯想把我们推向何处?”第二个说现在的房屋被毁,血肉和战火裹住了自己,当暴徒们还在继续为炮火欢呼,“兄弟们,我不懂,我迷惑,他在计划什么……”第三个造反者虽然在说造反是为祖国谋福祉,但是,“我痛惜流放时的不眠之夜……”特拉门斯告诉他们国王“占据人民的灵魂,占据空气”,所以就是要推翻这样的统治,但是他同样陷入了造反事业的虚无之中,“致命的反叛,毁灭的严酷,狂喜;虚空;虚无。”他也在质疑一切的奋斗,一切的冒险,一切的暴力,只是为了虚幻的“人民”。
造反者的质疑,加纳斯的流亡,特拉门斯的虚幻,也许都源于那个在四年之中坐上王位并创造了幸福与和谐时代的统治者,是一个隐秘的面具人,“他们说,他混在人群中,目光犀利,穿过城区,出没街市,无人知悉。”所以暴力也好,革命也罢,为了虚幻的“人民”,为了新的王国,只不过是要接触那个面具,让国王显出真面目,当寻找真相成为革命的目的,或者仅仅为了让“国王”成为一个人民可见的存在就发动暴力革命将更多人拖入战争,是不是本身就是对真相的遮蔽?而实际上,在国王莫恩身上,面具的存在也成为他对王国统治正当性的一种怀疑,“我戴着黑色面具出现在钟声回响的大厅里,出现在那些冷酷、老朽的议员面前……轻而易举使他们精神焕发——又离开,笑着……笑着……”用面具坐上王位,即使实现了国家的和平、生活的改善,对于莫恩来说,也是戴着面具的遮蔽生活,“这是王冠。我的王冠。瀑布滴滴落在尖刺上……”
面具遮蔽了真相,这是延续了四年的革命和反革命、统治和造反的共同原因,也正是莫恩作为戴面具的人遮蔽了一切,所以所谓革命背后的激情,和幸福和谐有关的爱情,错失了,走样了,变异了,世俗生活不再是神圣原型的译本,而成为了翻译中的错误。在这里,莫恩的面具人身份除了政治之外,也指向了世俗意义的爱情,他在成为国王之前就是一个巫士,一个催眠师,“我会读心……我会转动水晶球算命;在我的手指下,橡树桌子像船甲板一样晃动,死人长叹,通过我的喉咙说话,逝去的国王在我体内倘佯……”也正是这一特异功能让他从戴面具的巫士变成了戴面具的国王,从戴面具的国王变成了爱上米迪亚的男人——而米迪亚正是加纳斯参加造反派之前的妻子,于是,这个关于面具的政治故事在“莫恩”代表的双重角色中变成了一个寓言,一个寻找在激情和爱情的翻译中“遗失”部分的故事,一个在遗失中渴望救赎回到神圣原型的故事。
从政治剧到寓言剧,纳博科夫的用意是明显的,他对人物的命名完全在隐喻中抵达了神圣原型,译者对剧作中的人物名字进行了分析:
莫恩的名字(Morn)显然来自Morning(早晨,黎明),含有多义:莫恩把和平的黎明带给国家,最后又以自杀把良知的黎明带给自己。加纳斯的名字Ganus近似Janus(古罗马门神,其两张相反的面孔代表同时面向过去和未来),只有他能反省过去,最终放下武器而面向未来。特拉门斯的名字Tremens为疾病delirium tremens(震颠性谵妄)的一部分,暗示他罔顾现实,只做白日梦。但迪里奥的名字Dandilio近似dandelion(蒲公英),莫恩等称他为“无忧无虑的蒲公英”,意为随风飘荡,与世无争,随遇而安。埃拉的名字Ella源于意大利语,在古式英语中意为“美丽的女子”,也代表勇气,还有“光亮的”“多产的”等含义,她命运之坎坷使这个名字的后两义带上了反讽的意味。
这是译者的解读,其中可能也有误读,但不管如何,纳博科夫如此设置实际上也是让这部五幕剧戴上了面具。而回到这个失去了神圣原型的世俗故事,莫恩先生的悲剧也是特拉门斯的悲剧,是加纳斯的悲剧,是米迪亚的悲剧,他们共同构成了在翻译中失去的这个悲剧主体:加纳斯在四年的革命行动后回来,发现妻子米迪亚已经成为了莫恩的情人,按照特拉门斯的说法,“她已经堕落了。”当加纳斯化妆成摩尔人来到米迪亚家中的舞会,发现妻子的背叛,米迪亚的哭诉是:“突然地,你从死人堆里回来,现在,突然地,你一下闯入对你如此陌生的生活……我不知道该对你怎么说……我该对一个恢复人形的鬼魂说什么?我真的不知所措……”在米迪亚看来,他早就已经随着革命而死去,回来也完全变成了幽灵,“该怨谁呢?你为什么要离去?为什么要打仗一把幸福抛弃,对抗情火与真理,对抗国王?……”在舞会上认出了加纳斯的除了米迪亚还有莫恩,莫恩和加纳斯在互殴之后约好进行决斗,在扑克牌的决斗之前,加纳斯说:“复仇的冰与火,我死死盯住无情的恐惧它那猫样的眼睛:驯兽师知道他只要把脸转开——猛兽便会扑将上来。”但是这里不是激情而是恐惧;而莫恩之所以决斗,是为了米迪亚的爱情,一个从面具开始的爱情,也必将是一个以面具结束的爱情,“我要做一个幽灵。等我的继承人长大,我让他揭示我死亡的真相:他将以一个童话开始另一个童话。”
巫士是存在的,国王是存在的,但是戴着面具的巫士和国王同样是不存在的,和所谓的革命,所谓的王权,所谓的人民,以及所谓的爱情一样,都是一种虚无的存在,都是一个童话,甚至都是一个谎言,“这是王冠。我的王冠。瀑布滴滴落在尖刺上……”它们构成了戏剧中反复出现的梦,它是在第一幕中特拉门斯的梦,“燃烧的炉火朝我嘶嘶作响,不是热火,/而是蛇一般的寒气……哦心啊,哦心啊,/燃烧起来!滚蛋,发热,你这毒蛇!……”它是女儿埃拉的梦,“突然,我看到了:/过来了,过来了,燃着火,大吼大叫,/一个牛头怪飞奔而来,/我满心欢喜,献出自己——我醒了……”它也是莫恩的梦,“梦一旦中断,便无法再续,在梦中,我眼前飘浮的王国突然变成静立于大地之上。……是的,梦总是虚幻的,都是谎言,谎言。”所谓的爱情,所谓的理想,其实都构成了梦的一部分,而梦无疑是戴着面具的,它看起来通往美好之地,却完全是一个噩梦。在这个世俗的世界里,所有一切都是面具的存在,“你天生是爱的比喻”,莫恩在看透了这一切之后,选择以死亡的方式赎罪,而死亡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告别戴着面具的世俗生活的方式“回归原初”,回到神圣的原型,这从但迪里奥的那句话中得到阐释:
万物必须衰腐,因为万物要复活——由此看,三位一体很清楚。怎么说?空间是上帝,物质是耶稣,时间是圣灵。如此,我的结论是:由这三者构成的世界——我们的世界——是神圣的……
曾经戴着面具坐上王位,曾经在情人面前追求虚无的爱情,“莫恩先生的悲剧”就是一个谎言的悲剧,“我真是国王吗?毁了一个姑娘的国王?不,不,够了,我将落入——死亡——炽热的死亡!我只是一个火炬,被扔到井里,燃烧,旋转,飞行,向下飞,飞向它的倒影,那倒影像晨光在黑暗中生长……”当以死亡的方式完成自我的毁灭,在空间、物质和时间中重回原初状态?当莫恩的身影被夜光照亮,他的死亡或许将开启信仰意义上的“黎明”,只不过当给他递上了手枪的艾德明在死亡发生之后隐瞒了“莫恩先生的死讯”,面具又被重新戴上,谎言还将继续流传,在连死亡都无法回归原初的沉默中,纳博科夫让它54年来从不说话,让它在重见天日时依然带着缺失的伤痕,“我将消失……你懂的,我将消失,我将伴着为王的隐秘记忆静静走完我奇异的一生。”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3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