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9-26《一个人大摆宴席》:我和们说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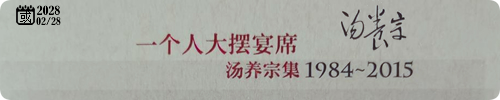
适合一个人独享的事有:试茶,听雨,候月
或发呆,高卧,摸索身体,枯坐,念,看云,抓腮
怎么做这么个孤君,握一把天地凉气
适合两个人分享的事有:交杯,对弈,分钱
或用情,变双身为一体,或从中取一勺,卿卿我我
捏住对方一指,莫走,谁知谁去谁留
适合三人的事,叫共享:高谈,阔论,制衡
分高下,俯仰,或拉一个压一个,度量,此消彼长
好个小朝廷,且暗中提鞋,边上放尿
——《散章》
翻开《一个人大摆宴席》,阅读汤养宗的诗歌,是从清朗的周日下午开始,最后在没雨的周一夜晚结束:一个周日的下午,一个周一的晚上,一个关着的房间,一个手拿图书的阅读者,以及一本诗集。所有地一切都指向了单数的存在,这是一个人的阅读,一个人的感怀,也是一个人大摆宴席。作者和读者在“一个人”的世界里达成了契合,是不是都是在做着独享的事?只是在试茶,听雨,候月,发呆,高卧,摸索身体,枯坐,念,看云,抓腮之外,还应该增加另一个动作:读诗。
汤养宗在《散章》中似乎并不只是说出了“一个人独享的事”,在一个人之外,还会有两个人,两个人的事叫分享,它是交杯,是对弈,是分钱,是用情,是亲亲我我,是“莫走”的呼唤;还有三个人的事,叫共享,它是高谈,是阔论,是制衡,是高下、俯仰、度量,以及此消彼长,是“暗中提鞋,边上放尿”。从独享到分享到共享,是从一个人到两个人到三个人的转变,但是即使一个人独享的时候,真的只是一种孤绝的存在?试茶是对面不是还有茶?听雨时不是外面还有雨?侯月时不是天上还有月?以及发呆,以及高卧,以及摸索身体,以及枯坐,以及念、抓腮,不是还有那些动作指向的目标和对象,不是还有面对的身体本身?或者在汤养宗一个人写诗的时候,不是还有白纸一叠,还有词语几束,还有句子若干?或者在一个人阅读的时候,不是还有那若隐若现出现或强调的“汤养宗”?
的确,汤养宗在诗集里看见了太多“一个人”独享的事:隔江而治的时候,一个人登基成王;喝酒的时候,一个人大摆宴席;书写的是“一个人的宗教史”;站在霞浦东冲口看日出时,是“一个人占领一座海”;如果有一把枪,最后一颗子弹“必须是留给自己的”……无疑在汤养宗所构筑的一个人的世界,就是一个孤绝的世界,独立的世界,没有他者的世界,或者说,他有意离开了他者,有意背向了他者。《关于一个孩子脸上的那道疤痕》里是和一桌人在一起,一桌人无疑就是他者,面对美妇人儿子脸上的疤痕,“我说了三句不近人情的话”:第一句是,“这孩子未来的脸/很可能反因这道疤而性感无比”;第二句是,“他今后的任何老师,已不再可能比这道疤/教授给他更好的东西”;第三句没有敢说,“天地有反证/你拥有的美,有点满,他必将弄出一个自己的符号/独立于世”。三句话对美妇人说,对美妇人的儿子说,对一桌子的人说,他们所构成的他者正是汤养宗的反面,在说的同时自己也成为了那个独立于世的符号。
他者总是处在我的对面,这便是汤养宗保持“一个人”状态的缘由,比如在《单人校》里,我是十万大山中认字最多的人,我是授业解惑的老师,但是我安于“门前有菜地三五畦,门后有竹笋七八条”,我把身体里长出的见识都变成了“自己所用的漫不经心”,我甚至读懂了人生的乐趣,“埋在泥土里的种子,没有消息,就是消息(《单人校》)”这就是在他者中找到的一个人,或者说这正是一个人所映照出的他者——他者和一个人构成的是对比关系,在这个对比关系里,“我终于/两手空空。不给身体挠痒。也不给人指路(《少》)”或者,“从来是国家忙国家的,我忙我的/我不但人长得丑,还经常爱傻笑(《今天是哪一天》)”于是,“时光有百法致人于一死。我是你们中的人民公敌(《扔了一首无序的诗歌而留下所遗落的残句》)”连城市里都在区域性限电,“只有我一个人的电灯泡是亮的(《这一年,我又一直在犯错》)”而即使“一个人大摆宴席”,对面的也是上上下下的电梯,是四面的空气,是身体里摸出的一个王,“要他在对面空椅上坐下/要他喝下我让出的这一杯(《一个人大摆宴席》)”
一个人他者对面的一个人,一个人是以他者为背景的一个人,汤养宗的这种解构就生生将“我们”拆解了:我们,就是“我”和“们”,就是单数和复数,就是一个人和他者,“我们。我与们。我或们。”拆解开来的我和们都变成了另一种状态,“我和们说话”,或者作战、分食可以“各有分工”,或者,“我是我,们是们”——似乎最后的状态才是汤养宗想要的“一个人”,“我心存感激,我到处跑,就是找不到哪个是们/那人受人尊敬,做过很多善事/但最后参加他葬礼的人数,取决于当天天气的好坏(《我与们,我或们》)”诗歌《最后一根火柴》更是将这种拆解彻底到了隔绝的地步,“这根火柴后,我不再来看你/不再有我与们。不再有我的事与们的事/墙内埋着行尸。墙外走着走肉……”
| 编号:S29·2220820·1861 |
我们变成了“我和们”,变成了“我是我,们是们”,变成了“不再有我与们”,汤养宗似乎走到了几乎决裂的地步。但是拆解也好,隔阂也罢,“我”和“们”还是存在着结合成“我们”的可能,“我们”是一个背景,它似乎永远存在于情感的逻辑中,甚而至于是从独享到分享再到共享的过程,而实际上,汤养宗在解构“我们”的同时,却在我和们之间建立了另一种关系学:我和们,我和你,我和他,以及我和我,他们都是“我们”的一种组合。《寄往天堂的十一封家书》无疑是“我和你”的一次对话,无疑是“我和你”的一次融入,无疑也是“我和你”情感的一种维系——借用聂鲁达《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的组诗结构而写成的《寄往天堂的是一封家书》,正是对逝世母亲的周年祭。我追寻着你,“坐在你坐过的藤椅上,辨认着/左手与右手,那是我的要求/在掌心,哪一边掌握了更高的真实”;我回忆着你,“小时候/我常到邻居家把你找到,这一回/已纳入永恒的寂静。”我体会到失去你的悲伤,“已没有一盏灯可以照亮它/这就是不可企及:瞬间变成了永恒,存在/归结为虚无。”我也从你身上学到了一些东西,“自从你离开人世,我才得知/这个世界的最高虚构怎样形成/同时,我拥有了更为可靠的时间”;当然我也在你的故事里发现我的人生,“因为你的死,我现在已经学会了/一门手艺,许多假的东西/在我手上已纷纷获得了真实的名分”……
我和你,是面对面可以说话的人,我和你,是连接在一起的存在,我和你,是无论生和死都分不开的情感,而我和你也便组成了“我们”。这是汤养宗基于亲情的一种回归,而在我和你之外,是不是还有“我和他”的组合?我站在他的对面,站在她的对面,或者站在它的对面,这种对面呈现的站立状态是不是最终要走向的是分享的事:交杯,对弈,分钱,以及卿卿我我,但是在这里汤养宗把这种分享变成了追寻和探索,而“他”便成为了一种远方的存在:他是飞鸟,“眺望群岛,眺望祖国以外的祖国/星粒以外的星粒/我的身体拥有了太多的飞鸟(《群岛》)”;他是树,“从树出发到一场雨水的降落/从雨到一个国家优美的耳朵/每一棵树都值得我们仰望(《琴十行》)”他是石头,“神的孩子们,要走你们就赶紧起飞吧/只是不要让我窥见/你们跃起时的那对脚蹼/不要让我怀疑,我也在你们中间(《山坡上的石头》)”
|
| 汤养宗:最多完成了他自己 |
长诗《一场对称的雪》是我和他最深层的对话,按照邻居张婆的定义,“雪是白白的人儿。”雪是他,他是什么?雪公开了大地上的一切,“像遥远的大海上那艘早已沉没的小舢板/现在又要重新让它装载下一整船的童话/证实事物有了变故(《天上那群人》)”雪拥有自足的形状,“内心早已自我对称,像我看到的民间的窗花/出自我祖母那种人的手,每一瓣花瓣/都把一句细细的软语再重复三遍以上(《关于雪的诠释》)”雪指明了天的方向,“雪排列着自己的队伍,涌向深不见底的黑”;雪组成的词叫“雪豹”,它是奔跑的高度,也有“雪耻”,它是反扑的力量,“窦娥横下心预言/林冲在一个风雪夜走上不归路/哈姆雷特被生与死的问题折磨成人鬼模样”;雪和身为银匠的父亲有关,“父亲死去的那个午夜,我家中的许多银器/都一齐发出了尖叫,更令人震惊的是/第二天屋顶上,无缘无故飘满了白雪”;当然,雪的存在抵达的是一个叫做诗歌的地方,像雪一样的白纸,不允许弄脏,像雪一样的文字,祈祷着不被化掉,当然也会有像雪一样的光环,或者那才是一种自我迷失的可能,但是雪终归是要白起来的,白的纯净,白的无暇,白的自然,“我们无比景仰它,用手轻轻抚摸,喃喃自语/像祈求谁芳心的允许。让我们爱过一次(《一张白纸与一片雪地》)”
一场对称的雪,我和他组成的我们也变成了一种对称,我是我,他是他,反而在另一个意义上去他者化了,而实际上,汤养宗对“我们”的拆解,并不是拆解组合本身,而是一次去他者化的努力,而努力的意义是形成新的组合,我和你维系的情感,我和他具有的启示,都是赋予了“我们”新的意义,而在这去他者化的道路上,最重要的却是“我和我”的组合,我是我,我是另一个我,一个自己和另一自己,是不是也存在着对话的可能,是不是也有交杯的意愿,是不是也有卿卿我我的情感诉说?一个我总是有另一个我存在,这是一种自然状态下的面对,“风生水起里鸟生蛋蛋生鸟/乱开合,无法无天,又各领各命/我叫汤养宗,我还有三四个小名/水火的事,谁攻火谁攻水,已相忘于纵横之间(《阴阳论》)”这是一种命名,汤养宗的小名三四个,是三四个被命名的自己,而这个被命名的自己和我组成的一种原始关系就是对立:比如一张纸盖章用左手,也可用右手,左手和右手是对立;比如1978年开始读正史,也读野史,正史和野史野史对立;“有时,我竟会这样无端地想:当某天/终于活在一个沦陷的国家/活在自己祖国的敌国中(《急就章》)”祖国和敌国野史对立……小名和本名,左手和右手,正史和野史,祖国和敌国,就是我和我的对立,于是拒绝,于是反对,“我们自以为是的身体,一直挑三拣四/不是被另一个身体反对,就是/至今仍拒绝着另一个身体(《偌大的单人房,为什么都置放有一张双人床》)”
但是对立或者只是一个种表象,对立制造了紧张,但是对立也创造了化解的可能,也正是从这个切口汤养宗开始了对自己的命名:以一个人的方式命名另一个人,从而“完成了自己”。自己是可以看见另一个自己,那具“雕花的身体”不正是有另一具身体?“天下少了我一人,便无花可看/这具身体一直名花有主,只有一些/遁世的花朵,还在气绝地叫喊着我的小名/浮现与不浮现,辨认与无言/今天我远远看着谁,一再地在空气里/嗅来嗅去,嘴角上仍带有那分不屑(《雕花的身体》)”;自己是可以发现另一个自己,“而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肯定还有另一个女人/她带着美妙的各种器官拼命成长/为赶来与我相见,但我们没有成为夫妻(《我出生那年,这世上一些事也发生了》)“自己当然也可以阅读另一个自己,“那里没有讨好,没有向谁低头/也没有狡赖与搪塞/仿佛只有完美的病人对另一个完美的病人/仿佛一个苍老的父亲见谅了他苦难的儿子(《试着在三十年后读到一首汤养宗的旧作》)”
在历史中发现另一具雕花的身体,在出生时想象那些同一天的自己,在三十年后再读自己的旧作,这是时间上的另一个自己,这是空间里的另一个自己,还有酒桌上的另一个自己,一个人大摆宴席就是和另一个自己痛饮,还有文字里的另一个自己,诗歌的世界是乌托邦,因为那里只允许自己进入……从另一个自己发现自己,从自己和另一个自己中完成自己,这便是汤养宗真正去他者化的意义所在。在诗论中,他说:“没有谁完成了诗歌。是的,他最多完成了他自己。”诗是载体,就像另一个自己是载体,目的就是要让真正的自己独立出来,“一个诗人要独立出来,就得养出自己的坏脾气,敢于自我裂变,敢于使坏,梁山泊一百单八将每一个都是敢于使坏的坏孩子,但他们同时又是不同于其他任何人的好人。”在《一个逻辑怀疑者在一座山上的左想右想》中他说到有一次在观音山,在耀佛岭,在国家级森林公园的树林里,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一队人马中的人员,而是森林里的一棵树,去他者化的意义就是树的独立,而在那一刻,感觉整座森林都是我一个人的,“我所要的生活,也通过它们的走动有了彼此的相认。”自称是现实中孤魂野鬼的汤养宗终于发现了“一个人”的真正意义,“这不但是由于我历来不适应人群,还由于心中一直有一道我看不见,却能处处左右我的魅影。”
去他者化而将“我和你”维系于一种情感,去他者化而将“我和他”变成行路上的一个整体,去他者化而将“我和我”实现了对自己的完成,于是我和们说话,我和们喝酒,我和们作诗,孤冷而孤绝的世界里,“我们”才是真正的一个人,一个王:
隔江而治,我是江南寂寞的领袖
隔山而治,我是百万草木的主
隔村而治,村里只住我一个人
我是自己的村长,管着一口井,一口锅
还有想象中
每天来开路条的村民
还有自认的选举,相当于
排他法,我把名字张榜在城头
与我放一起的还有一块城砖
藤蔓上长出的菩提果,一条爬壁虎
可没有谁能与我相比肩
我只好一个人登基,当王,一个人
在时光中挥金如土,一个人
把自以为是当作享用不尽的财产
石头,老树,头顶经过的
白云,都顺从这里的村规或王法
在我自己的帝国,时间已有点多出来
篱墙花乱开没有一棵结出正果
我骂骂咧咧,要精心安排
天地之间,一场浇灭心火的国殇——《隔江而治》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