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7-21 大历史与小易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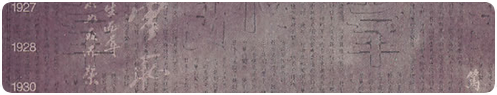
当当的退书还是没有动静,卢松松说,其实亚马逊的价格普遍比当当便宜。也曾经很细心地比较过,卓越亚马逊、当当和京东书城作为图书网购的三驾马车,大致的价格是相当的,只是某一类别的有些高低不同,但都可以让我比较优惠地拥有零运费的服务,相对来说,网购的间接性和不可预知性仍然是其不可避免的问题。
但既然当当还在等待中,那么就索性回归到最原始的购买方式:到新华书店,摸着书页付钱,这就是最传统,但也是最奢华的购书方式——从来不会打折。其实,买书也全是借了小五儿童节购书卡的光,名义上为他买些学习书籍,其实是为了填补自己网购尚无期的空闲机会。书店基本没什么变化,除了个别柜子进行了调整,大致的格局还是差不多,当然还是那些坐着站着看书的阅读者,他们组成了新华书店最大的人流量。转来转去,没有眼花缭乱,其实书真的不多,几下一转基本看清了书目,比起网络书城,这里自然是贫瘠的,挑了张爱玲的《雷峰塔》和《易经》,都是“张爱玲外集”的一部分,和两年前购买、至今尚未读完的《小团圆》组成了张爱玲“自传三部曲”。现在,有点对“外集”的意义产生了一点疑问,大约是张爱玲生命之外出版的文集,不列内,是不是不太正统?或者是张爱玲用外文写就的文字,还是需要重新回到母语状态,一来一去,都已经经失了味道。其实,从市场来看,这两本书的销售并不见好,但是张爱玲用双重语体来告诉一个真正的张爱玲,或许也是一种勇气。王德威在《雷峰塔下的张爱玲》一文中写道:“从散文到小说、从自传性的《流言》到戏剧化的告白,穿梭于中英文之间的张爱玲几乎用整个一生反复讲述《What a Life!》的故事。”
从张爱玲的外集,牵涉到文学史的问题,还是王德威,他说,
文学史本来就没有定论,尤其文学史是一个虚构的历史。什么是历史,什么是文学史?这是一个吊诡的词。张爱玲特别有趣,仿佛我们的祖师奶奶在哪一个地方操作,真的是把整个的时间顺序都弄反了。她活着的时候,我们以为她不见了;她死了以后,又源源不断地回来。所以魂兮归来,我用鬼魂的意象,真是有所为而为的。
同样是历史,黄仁宇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用大历史观来“匡正”看来不如人意的“中国现代史”,那么历史也就是一个我们所闻之外“吊诡的词”。只是出版此书的“九州出版社”实在生疏得很。
三册图书购来,都是原价,合起来是113.80元,而如果在当当网上,总价就是72.60元,相差41.20元,当了一回真正的冤大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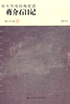 |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黄仁宇 著 九州出版社 49.80元
这是黄仁宇的一部历史著作,记叙的时间自1924年国民党黄埔建军始,至1945年抗战结束止。书中对海内外关于蒋介石的评议,多有精彩的辨析;作者拣择与排比史料的方式,别具慧眼,言人所不能言。作者沿袭其大历史观的研究方法,检视蒋介石的历史定位及其历史局限性。作者曾说,写作此书,目的在于阐明中国由“中世纪国家”步向现代的挣扎和转折。此次增订出版,增补了作者相关的四篇文章,作为附录;并对全书的文字重新做了核订并有所补充,使全书更趋完善。在第一章中,黄仁宇说:“刻下中国现代史的时候,将蒋介石的日记公布,可能有匡正的功效。”而这匡正更多是对历史的无奈:中国过去一个世纪的经历,既包含着极大规模的颠簸,也有无数的纵横曲折。不仅人与人之关系间产生了各种惊险离奇的波澜,尚且在各人心目中引起无限块垒之起伏。如果当中激昂忧怨的情节概可以用“善恶”两字形容,也可见得作者并没有将笔下题材通盘掌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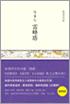 |
《雷峰塔》描写了张爱玲从4岁到18岁的少女时代,写到父亲迎娶后母,后母挑拨父女关系,将女主人公琵琶监禁阁楼,以弟弟的病死告终。张爱玲在1966年的一篇英文文章中,表达了写作《雷峰塔》的初衷:“这本小说就是写给美国读者看的,她努力接近美国人的阅读习惯。”《雷峰塔》和《易经》原属同一部小说,因为篇幅过长,分拆成上下两部。作品完成后,由于遭到书商拒绝,对美国市场充满期待的张爱玲心灰意冷,将书稿锁进抽屉,一锁就是四十多年。而现在重见天日可以看见那囚禁她的家里到底有什么样挥之不去的记忆?里面写道:“宽敞半黑暗的火车站里水门汀回荡着人声足声,混乱匆促,与她意念中的佛教地狱倒颇类似。那个地下工厂,营营地织造着命运的锦绣。前头远远的地方汽笛呜呜响,一股风吹开了向外的道路。火车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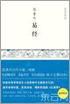 |
接续《雷峰塔》的故事,《易经》描写女主角18岁到22岁的遭遇,同样是以张爱玲自身的成长经历为背景。张爱玲曾在写给好友宋淇的信中提及:“《雷峰塔》因为是原书的前半部,里面的母亲和姑母是儿童的观点看来,太理想化,欠真实。”相形之下,《易经》则全以成人的角度来观察体会,也因此能将浩大的场面、繁杂的人物以及幽微的情绪,描写得更加挥洒自如,句句对白优雅中带着狠辣,把一个少女的沧桑与青春的生命力刻划得余韵无穷!虽然小说《易经》主要是描述香港沦陷和女主角回到上海的历险,但张爱玲写作此书时已经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回顾将近20年以前的经验,她其实是有着历史的后见之明的。1950年代末,在美国写作《易经》时期的张爱玲,已是一个两度结婚,移民他乡,依靠非母语写作的中年作家了,回望1938年初入文坛以来的种种遭遇,她有理由为自己所经历的变化唏嘘不已,从而理解“易”的意义所在。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2538]
思前: 午后,一闪而过的虚幻
顾后: 等待复活的仪式
文以类聚
随机而读
- 1条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