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4-10 《东京物语》:低处的空寥和迷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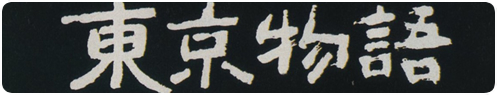
缓缓的时间流淌,依然是火车和轮船的汽笛声,依然是夏日的宁静,依然袅袅升腾起轻烟的一柱蚊香,只不过,现在坐在窗口的只有平山周吉一个人,摇着扇子,看着江水,看着落日,看着船只,“一个人生活,觉得日子都变长了。”他说,在身边没有妻子的生活里,注定会剩下一个人的寂寥,注定会是轻轻地哀叹和迷失。
这是时间在港口小镇尾道留下的印记,它拉大了和那个叫东京的距离,像妻子的病逝一样,东京仿佛就在眼前,却已经变得遥远。10天,却比人生漫长,就在10天前,平山周吉和妻子富子在这个屋子里,整理去东京的行装,仿佛是人生最后的一次远行,而在那个陌生的地方,都是他们的牵挂,大儿子幸一一家在东京、女儿文子一家在东京,在战争中死去的二儿子昌二的妻子纪子也在东京,小儿子敬三虽然住在大阪,但是到东京沿途也可以下车去看一下他,除了未嫁的小女儿京子还在跟他们住在一起,东京就是他们全部的牵挂。父母和孩子,隔着两个不同的城市,也隔着是两种不同的世界。尾道是他们的起点,而东京,是不是会成为他们回不去的终点?
一切仿佛都不在暗喻中,父母和孩子总会走在不同的路上,只是东京,是一种陌生。东京之行像是在消弭陌生,而其实,这一段时空的距离谁也无法超越。起先来到的是大儿子幸一家,女儿文子和媳妇纪子都来了,一家人欢笑、聊天,看起来其乐融融,父亲说,这次又打扰你们了,母亲问,孙子小勇几岁了,他们一起吃饭,一起说起东京的生活,也一起聊起尾道的那些邻居,不幸的阿孝改嫁了,常常去钓鱼的那个男人死了。父亲说,一直以为东京很远,没想到今天就和大家见面了。母亲说,很高兴看到大家都好。
 | 导演: 小津安二郎 |
 |
这是现实的东京和心里上的东京的差别,但是热闹或者并不是理想的东京,而在深入的过程中,他们慢慢发现东京里有着更多的隔阂,走在去拜访好友的路上,周吉说:东京真大啊。而富子也说:是啊,如果在这种地方失散了,可能一辈子都见不着面了吧。”这种隔阂并不是地理空间上的距离,而是某种淡淡的无归宿感。子女在东京,本来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亲情拉近距离的机会,但是幸一和文子的忙碌,让他们若有所失,甚至这种隔阂也蔓延到更小的孙儿身上。因为要住在幸一家里,大孙子小实的书桌被搬掉了,小实很不高兴;第二天因为幸一出诊而取消出游计划,小实不断地抱怨:“真无趣,真无趣。”而自始至终小孙子小勇一直没有和爷爷奶奶打过招呼,刚到东京那天,富子几次试图拉住小勇的手,小勇却总是跑开了。看起来是孩子认生,而在老人心里总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在终于带着小勇走到外面的时候,富子对自顾自拔草游玩的小勇说,你长大了想做什么,是不是和爸爸一样想当医生?小勇没有回答,而一旁的富子哀叹道:“恐怕奶奶等不到那一天了。”怅然里有着淡淡的哀愁,而这样的哀愁在东京的物语里,也越来越明显。
幸一和文子商量,每人出点钱将父母送到热海温泉去度假。看起来是为了让父母能够感受不一样的东京,但实际上是将他们推向一个更为陌生的地方,旁边是打麻将的吵闹声,是唱歌的嘈杂声,两个老人,躺在房间里,扇着扇子,看起来安逸、平静,实际上他们根本不能适应这样的生活,他们只能坐在大堤上看着那平静的水面,聊着天说着话,仿佛就在自己尾道的家里。场景的置换,反而让他们有一种想回家的感觉,他们说,这是年轻人来的地方,其实是在以一种借口来宽慰自己,同时宽慰在东京的子女。而因为他们提早回来,文子显得不高兴,叫他们多玩几天,因为自己晚上还有一个讲习的活动。这种不快越来越明显地写在脸上,两位老人决定不打扰文子,平山周吉去找曾经的在尾道的邻居服部,而富子则去了纪子一个人的家。
这是他们主动选择的东京生活,而这似乎也将两代人之间的隔阂又放大了许多。遇到老朋友,平山周吉和他们喝酒,而这样的生活中,平山周吉似乎才找到了曾经的自己,他们一起聊起自己的子女,也感叹人生,他们的孩子也有战死,也有不听话,平山周吉说:“没有孩子感到寂寞,有了孩子又会嫌弃你,真的难以两全其美。”共鸣的老人们喝醉了酒,而被派出所的人送回到文字家里,文字看到醉态的父亲,还带了一个陌生人,心里更加不快,责怪父亲以前也是老喝醉酒,这种不快看起来是因为平山周吉醉酒“出格”,但其实也是两代人难以弥合的隔阂,进一步放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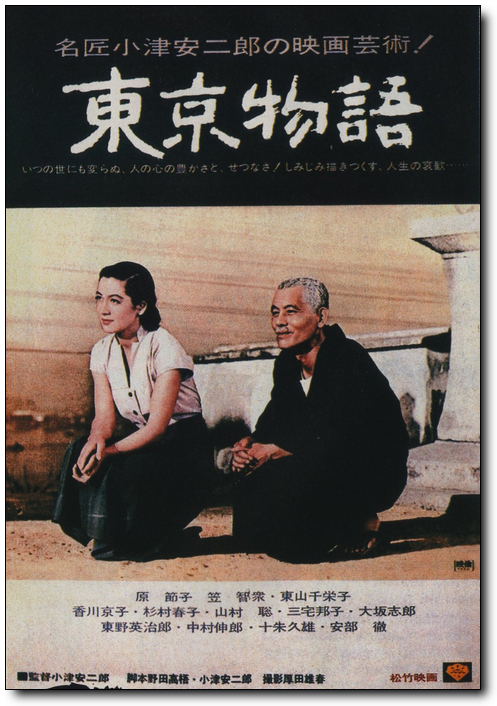 |
| 《东京物语》电影海报 |
而在纪子家的富子,却感受到了一种温暖的亲情,从来东京开始,纪子就一直像自己的女儿一样照顾他们,微笑着,安慰着,打着扇子,问寒问暖,而在纪子家里,唯一和富子联系在一起的似乎只有那张还没有取下的昌二的照片,一种死去的纪念,8年了,纪子其实并没有重新开始自己的婚姻,而死去的昌二并不仅仅是怀念,在入睡前,富子对纪子说,有好的对象就嫁了吧,你这样让我们很难过,等你老了,一个人了就会寂寞了。纪子还是微笑着,而等到灯火熄灭,纪子却也偷偷抹去了泪水。这是触及心底的伤感?对于纪子来说,丈夫死去8年,其实也都是一个人难以排遣的的寂寞,而对于到来的公公婆婆来说,纪子从心底理解那种孤独,所以她用一种温情来照顾他们,而富子显然在这里更能得到亲情的寄托,只不过这更多是一种象征,就如她睡觉的地方,也曾经是儿子的床铺,睡在死去的儿子的床上,对于富子来说,一方面是对于生老病死的无奈,另一方面或者更有现实的迷失。
这种迷失不是东京的陌生,不是儿孙的忙碌和淡漠,更多的则是人生的无助,孩子长大,自己年老,或者像昌二一样的逝去,都是不可逃避的现实,虽然在他们离开东京的时候,都说游玩了东京让他们很满足了,而富子也说,这次见到了大家,下次有什么事也不用赶来了。这像是宽慰,但更像是一种对于人生的哀叹,见面或者只是一种形式,但是对于年老的父母来说,并不仅仅是形式,而这句话也一语成谶,在尾道的火车上,富子感觉心脏不舒服,虽然经过大阪敬三那里的短暂停留,但是回到尾道,富子就一病不起,而起很快就撒手人寰。生老病死也是人生的一种过程,所以富子的死一直没有过分的渲染。而在富子死去前后,亲情的隔阂似乎又一次被拉大了,幸一和文子赶来见了母亲最后一眼,但是他们是带着孝服来的,也就是说他们对母亲的离开并没有过多的不舍;敬三因为工作出差而没有赶上,他甚至连母亲确切年龄都没有记住,而在为母亲办法师的时候,他一个人走到了外面,或者在心里有一份深深的愧疚,他说,我不习惯木鱼的声音,妈妈好像随着那声音越来越小,我没有尽孝,妈妈不应该现在死的。但是死去是一件无法挽留的事,就像8年前的昌二。送别母亲,对于他们来说,也更像是对于人生告别的一个形式,幸一、文子和敬三又匆匆坐火车离开了尾道,留下的是纪子和未出嫁的京子,而临行前,文子甚至还将母亲的一些衣服作为纪念拿走了。
幸一、文子和敬三作为有自己事业和家庭的子女,更多已经不属于尾道这个曾经的家,所以他们以过客的身份告别母亲,也必将以过客的身份回到自己的生活轨道,而对于尚未出嫁的京子来说,她感觉到的是人情的冷漠,她哭着对纪子说:“妈妈一死就要拿东西做纪念,我一想起妈妈的心情就觉得伤心。外人反倒更有感情呢,骨肉之间不应该这样。”而纪子却对她说:“可是,京子啊,我在你那么大的时候也这么想。不过,孩子长大后,就开始渐渐远离父母了。大姐已经离开父母有了自己的生活。她绝不是存心不良。大家都是以自己的生活为重的。”这段话可以看做是对于离去亲情的理解,但是同样处在孤独中的纪子来说,善意的理解并不能消弭京子心中的冷漠感,她说,这世界太让人灰心了。而灰心的世界在失去妻子的平山周吉看来,却显得淡然了许多,他只是在纪子要回东京的时候,劝她放下顾虑活得幸福,并送给她富子留下来的一块怀表,感慨地说她是一个好人。而纪子在这即将离开尾道,即将告别和平山家有关的一切时,才会泪如泉涌,才会袒露出自己的心扉,她说,我不是什么好人,我也很自私,我甚至有时候会想不起昌二。
美丽、贤惠、克制、孝顺、坚强、真诚……纪子是一种理想,而所谓的自私或者想不起曾经的丈夫或者代表着一种鲜活的人性,她的泪水、她的痛苦只不过藏在微笑的后面,而在人生的历程中,纪子更能够洞察死亡、孤独和迷失,而在平山周吉和富子的生活当中,何尝不是用微笑来掩饰孤独和迷失?他们始终那么安静,那么坦然,对于子女的生活,他们也从不抱怨,尽可能去理解宽慰他们,东京之行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要看多少热闹,要游玩多少地方,只是希望能和儿女在一起。富子的死亡像是一个劫难,但是他们也没有过多的痛苦,看起来东京之行有着一些预兆、比如在热海时的晕眩,在火车上的难过,以及两次忘记拿雨伞的健忘,但实际上这一种死亡也只是人生的常态,只不过在命运面前,总会显得如此无力如此无常。
无力无常的现实被隐藏在和谐幸福之下,幸一在东京收到了父母回家的感谢信,说在东京见到了大家还去了热海,感觉很幸福。但是刚收到感谢信,那封母亲病危的电报便也到了。感谢信和电报,对应于幸福和无常,一方面是安慰和满足,一方面却是无法逃避,成为现实的两面。作为小津安二郎自己最喜爱的一部电影,《东京物语》其实并没有从道德批判的角度来谴责生活中的冷漠和无常,而更多的是从冷静和平和的叙事中寻找生活的本真状态。低视角、180度越轴剪辑、固定机位,还有相似性的镜头组接,这些电影语言的运用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容被打破的现实,而那种宁静却总是让人感到无奈。静物,无人的室内,建筑物的立面和风景,这些镜头总显得空洞,作为“额外叙事空间”的运用,也是为了表现一种静观的眼界,一种倾听和注视的态度。“对我来说,没有人能像小津一样让电影如此接近它的本质和目的,也就是为这个世纪的人提供一个适用的,真实的,合理的形象,人们不仅能从这个形象中辨识出自己,更重要的是,他能从这个形象中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真实、合理的不仅是电影语言,更是现实状态,那里的东京和尾道,无所谓热闹也无所谓冷清,而生与死也无非是一种逼近真实合理的状态。
如果从电影中看到小津安二郎的人生态度,或许也是一种对现实的逼近,就像那封在病危之前送抵的感谢信,所谓的“幸福”更多就是与世间的某种隐秘对抗,而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从未描写过“幸福”,他的作品所表现的却是“幻灭”,作为一个从未结过婚,更没有子女的导演,他却一直在讲述“父子”“父女”之间的故事。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喜欢给剧中人起一样的名字,喜欢用同一批演员,喜欢讲述类似的故事:姓平山的一户家庭,父亲一般叫周吉,长子一般叫幸一;如果有次子,一般叫昌二;如果还有三子,一般叫敬三;有女儿或者儿媳的话,总有一个叫纪子(又译节子),而且是最孝顺最乖巧的一个;如果有孙子,最好是两个,大的叫小实,小的叫小勇;每家人都有几个常来常往的朋友,这家也不例外,总有一个叫服部,总有一个叫间宫;男人们一起去一家叫若松的料理店吃东西,去一家叫露娜的酒吧喝酒。 他不怕观众混淆,也许他的目的就是这个:希望观众把电影中不同的故事当做一家人发生的故事。千姿百态的人生说到底也是一样的,不外乎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生老病死。正好六十岁生日去世的小津安二郎,他的墓碑上,只有一个汉字:“无”。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521]
思前: 听到自己从墙的另一头走过
顾后: 〇文本的现在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