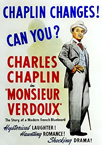2024-04-10《凡尔杜先生》:和我冲突的是人

人生第一次喝朗姆酒,也是最后一次;法罗神父的祈祷是打开天堂之门,凡尔杜先生却知道自己走向的是地狱;被判死刑不是悲痛和悔恨,而是面带微笑走出牢房……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天堂就是地狱,死亡之痛被微笑代替,被绑住了双手的凡尔杜先生以“背对”的方式走出了牢房,走向了绞刑架,最后一幕对于他来说也并非是失败者的悲歌,有些器宇轩昂地走向死亡之地更像是一个胜利者的慷慨“就义”。
这就是卓别林塑造的凡尔杜先生人生最后一幕,这是肉身之死,作为法国连环杀手,凡尔杜得到了法律的制裁,他的死是一种法律的惩罚,但是他真的就这样死在了罪恶的地狱?在监狱里“会见”法罗神父的时候,有一段对话揭示了他最后的内心世界:神父说想要拯救他,“我来是希望你能和上帝和睦相处。”但是凡尔杜先生微微一笑,“我和上帝一直是和睦相处的,和我冲突的对象是人。”神父说他应该为自己的罪恶忏悔,凡尔杜先生却说:“谁又知道什么是罪恶呢?生为从天堂里坠落的上帝的天使,谁又知道它的使命是什么呢?”他甚至对神父提出了疑问:“如果世间没有恶,你能做什么?”神父回答他:“孩子,我所做的事情就是用我微薄的方式来拯救一个在悲痛中失落的灵魂。……愿上帝宽恕你的灵魂。”凡尔杜最后说:“不管怎么样,我的灵魂本来就越是上帝的。”
在被推上绞刑架之前,凡尔杜并不怕死,也不认为自己犯了罪,因为他在看来,自己一直和上帝和睦相处,自己的灵魂也一直属于上帝,他反而质疑的是所谓的罪恶,所谓的救赎,所谓的祈祷,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也在怀疑神父眼中的上帝,他是不是就是一个魔鬼?当自己杀人而被判死刑,当然不需要在上帝面前忏悔,因为魔鬼从来都是上帝,所谓的使命也是一种坠落和堕落。与上帝在一起,与魔鬼为伍,所以这里不存在宗教的忏悔,没有信仰意义的宽恕。但是,凡尔杜却指出了真正的罪,那就是人,或者是人性,因为“和我冲突的对象是人”,人是面前的众人,人是投以落石的他人,人是丧失人性的存在,而凡尔杜所说的人指向的更是这个社会,是社会的规则,社会的制度,将自己变成了魔鬼。
与神父的对话中,凡尔杜先生指出人的问题,揭露的是人性,更是一种原罪,那么,在这个丧失了人性的社会,在这个充满了原罪的世界,他杀人的举动是不还具有了合理性——反过来说,他是不是也是带着原罪的那个魔鬼?他是不是也是在别人面前制造冲突的人?这像是一个悖论,而这个悖论的化解需要从电影最开始的自述中找到答案:一处墓地的一块墓碑,上面刻着“亨利·凡尔杜”的名字,生卒年为1880-1937,之后是旁白:“如你所见,我的名字是亨利·凡尔杜,30年来,我都是一个银行职员,直到1930年大萧条时期,我被解雇了,然后我开始专注于对异性的‘清算工作’,严格来说,这曾是供我养家糊口的工作,接下来便是我的故事……”从凡尔杜先生最后被处死为结局,以死之后的“复活”未开始,凡尔杜又以怎样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他又会以怎样的方式实施对异性的“清算”?
| 导演: 查理·卓别林 |
在这里,关键词就是“清算”,或者说,凡尔杜一生就是清算的一生。他曾是银行的职工,对账目进行清算是他工作的职责之一,这是工作方面的清算,也是在经济意义上的清算,而这一清算最后把自己也“清算”了,因为他成为了大萧条时期第一批被解雇的“牺牲品”,他有一个双腿残疾的妻子莫纳,有一个年幼的儿子彼得,对于这个家来说,“清算”而失去工作就是逼上了绝路,曾经虽然不富有但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也正是这一次的清算,让他开始实施属于自己的“清算计划”,那就是对那些有钱的异性下手:先是接近他们,给他们各种甜言蜜语,然后和他们结婚,最后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杀死他们,获得他们的巨额财产。凡尔杜的清算其实是一种拥有:第一步是成为他们的丈夫,和不同的女人交往最后成为了“所有人的丈夫”,他是莉迪亚眼中在印度支拿做桥梁项目的丈夫,是安娜贝拉对别人夸口是“船长”的布热尔,是西尔玛认识两周就私奔结婚的男人……而在杀死他们之后,凡尔杜就拥有了他们的财富,西尔玛在巴黎国立银行的6万法郎就变成了自己的财产,莉迪亚从银行刚取出的7万法郎也到了凡尔杜的手中。
清算而拥有,这便是凡尔杜先生遭遇清算而失去一切之后的所得,卓别林用死去凡尔杜的讲述打开的故事就是重新回顾这一人生的转折,从西尔玛一家发现她的失踪和银行存款消失为开始,之后是凡尔杜先生收到了银行的存款,然后他又赶到了莉迪亚那里,告知现在金融危机马上要来了,让她把银行的钱都取出来,最后在吟咏了一番夜月之景之后,凡尔杜走进了“妻子”莉迪亚的房间,毫无声息地“杀死”了莉迪亚,得到了那一大笔钱,他极快的数钱动作表明已经是一个清算的高手。从巴黎到里昂到科贝尔市不断变换的城市,从亨利到布热尔不断变化的名字,以及从西尔玛、莉迪亚不断更新的妻子,他的清算行动就在那不断出现的火车车轮中被展开——从没有出面早已经消失的西尔玛,到出现在故事中被凡尔杜现场解决的莉迪亚,再到几次出手被各种原因阻碍而无从下手的安娜贝尔,再到刚刚遇见用谎言和甜言蜜语以及无数的玫瑰花打动而开始交往的格恩内夫人,卓别林设置了在凡尔杜先生周围处在清算不同阶段的女人,由此完整组成了凡尔杜先生的清算链条。
对女人的清算只是凡尔杜的一个步骤,这个计划的下一步是另一种“清算”,那就是得到这笔钱后投入到股市之中,用交易赚来的钱给莫娜和彼得,这就是他对家的责任。但是正因为凡尔杜清算计划有着经济的考量,他最后又成了被清算的人,因为经济萧条,因为金融危机,因为银行倒闭,更因为即将到来的战争——死于1937年,这个墓碑上的数字正是这个被清算时代的一道铭记,卓别林用纪录片的手段展示了这个时代的残酷:在金融危机中,很多银行倒闭,很多投资者跳楼,然后是战争乌云开始笼罩,然后是希特勒的纳粹上台。从经济萧条到金融危机,从金融危机到战争爆发,卓别林构筑了这个被清算的时代,即使凡尔杜用各种不同的手段得到了大笔的钱,但是在这样的时代面前,他的悲剧依然走到了起点:就像工作30年被银行解雇一样,他最后还是一无所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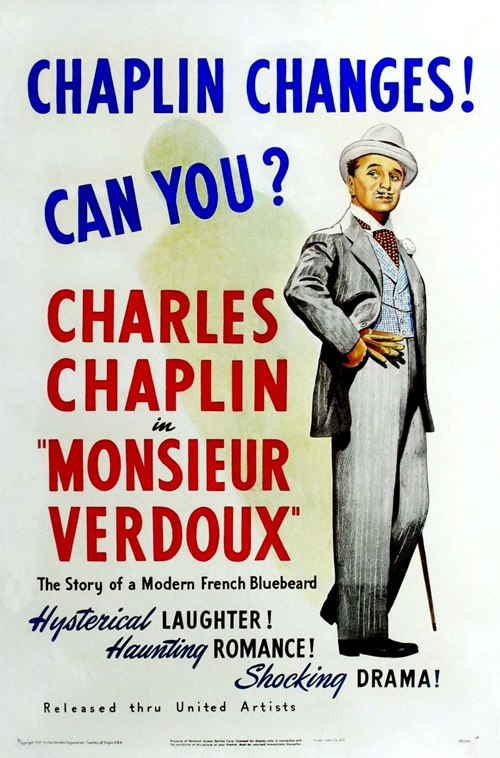
《凡尔杜先生》电影海报
工作中被清算、为了报复实施清算计划,金融危机和战争再一次开始清算,这就是卓别林构筑的“清算时代”,这样的清算并不只是和凡尔杜有关,并不是和那些女人有关,更是和整个社会有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卓别林把主题提升到了对人性的批判:他被银行解雇,是社会制造的残忍,他报复女性是因为女人是最现实的存在,是物质的奴役,所以凡尔杜先生说:“失望是我的麻醉剂。”已经经历了太多的失望,所以才会认为自己犯下的罪和整个时代比起来微不足道,“善与恶之间要保持好平衡,任何一方占支配地位,都有损于灵魂的完整。”所以才会把整个社会都看做是一门生意,“我的杀人是一门生意,是许多大生意的历史缩影,战争或者冲突什么的,归根结底,都是生意。”在没有善与恶的人生中,在没有天堂和地狱的世界里,在一切都是生意的社会中,一个人杀人,杀死那些物质的奴隶,又有什么错?
“和我冲突的对象是人”,站在人性泯灭的角度,凡尔杜先生的杀人行为被合理化,但是卓别林却又不是将他设置为毫无人性的罪犯,他对妻子和孩子的爱藏在心里,更重要的是,他遇到了刚出狱无家可归的女孩,在她那里却发现了爱的微弱之光。本来他是为了实验自己新研制的毒药而把女孩带回家中,女孩说自己来自比利时,因为在这里偷窃了打字机被判入狱三个月,他们遇见的那天是她出狱的第一天。凡尔杜邀请她回家,然后给她倒了酒,酒里就掺入了研制的毒药,但是和女孩的对话中他得知她爱着自己的丈夫,他从战场上回来变成了残疾,即使如此,女孩也泯灭希望,当凡尔杜悲观地认为这个社会本身就很残忍,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爱,“活着有什么好?”女孩却说:“太多了,春天的早晨,夏天的夜晚,音乐,艺术,爱情....……”就这句话让凡尔杜偷偷倒掉了那杯酒,重新换上了没有毒药的酒,告别时还给了她一笔钱,女孩离开时感谢凡尔杜的救命之恩,“这个世界是多么美好啊。”她如此感叹。
女孩唤醒了凡尔杜,女孩也拯救了凡尔杜,尽管是微弱的一点光,他也做出了终止犯罪的计划,他也感受到了一种爱。但是这并不是最后的拯救,心怀所谓的爱,然后实施自己另外的计划,对于凡尔杜来说,更具合理性,从此他就可以安然和成为魔鬼的上帝在一起,从此他就可以安心实施自己的清算计划,从此他可以在和人的冲突中无情地批判社会——但是,他既成为了这个时代的牺牲品,也成为了无情社会恶的代表,他对人的仇恨也让他被仇恨,这是不是反而成为了一种轮回?对于社会的深刻反思,对于人性的彻底批判,是卓别林的一次真正转型,距离《大独裁者》7年,他就把社会的顽疾变成了人性之恶,而“凡尔杜先生”也成为卓别林在麦卡锡主义时代的一次发声。海报上写着:“卓别林变了,你能吗?”如此明示着一种变,安德烈·巴赞说:“夏尔洛无法适应社会,而凡尔杜却适应过了头。”对社会解读以及实施清算计划的凡尔杜已经将被动生存的夏尔洛形象完全颠覆,这是“凡尔杜杀死夏尔洛”的一次根本改变,但是卓别林之变把犯罪变成了原罪,把个人之罪归结为社会之罪,把个体的不公平遭遇变成滥杀无辜的借口,某种意义上不也是对人性的一种漠视?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