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4-10 《维洛妮卡佛丝》:这个国家身上带着毒

“回慕尼黑,1860露天体育场。”罗伯特在离开诊所的时候,坐上了出租车,目的地在别处,时间在别处,1860年属于足球,属于体育,属于自己的生活,这是罗伯特对时代的告别,也是对现实的逃避,或者只有当他回到1860年的露天体育场,回到自己作为体育记者的职业,他才能远离那一种痛,远离那一种毒,远离那一种死。他是需要这样一种隔离,在离开之前,他听到了医生和官员举杯庆祝一场“胜利”:“现在一切都好了。”在听到胜利之前,他看到了报纸头版刊登的“超级明星服毒自杀”的消息。之前的自杀悲剧,之前的胜利庆祝,似乎都在罗伯特的生活之外,他只能用离开的方式远离这个时代,远离被黑白欲望笼罩的时代。
无法救赎,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悲剧。在时间的背面,写着1860年的字样,但是当时间翻转过来的时候,却是站在现在的超级明星佛丝,却是读到那孤独房间里纸条上的“都是最好”,是的,医院里的那间房间再不会打开,为她举办的演唱会就如一个梦幻,收音机里的音乐变成了一种怀念,而镜子里的自己,即使画上了口红,也只是一个不真实的影像。一间屋子,在佛丝看来,是“安全的避风港”,卡特兹医生,在卡佛丝看来,是最好的朋友,可是当吗啡换成了避孕药,当演唱会变成了囚室,“都是最好”如同那一句“现在一切都好了”的祝福一样,变成了一个女人最后的墓志铭。她拿出抽屉里的药,张开嘴巴,喝了下去。
|
| 导演: 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 |
 |
而讽刺往往是自己无法改变的现实。那部电影里,她就曾经说过:“它会摧毁我所有的一切。”所以留下遗书,所以吞服药物,“谢谢你,我的一切都给你了。”不是奉献,是因为看见了自己的宿命,一部电影,却是自己一生最后的预演,对于佛丝来说,就是在这亦真亦幻的世界里看不见自己,把一切给了“你”——把青春给了曾经的那个时代,把婚姻给了自己的编剧,把生命给了“最好的朋友”,把身体给了那一间“避风港”。而真正的事业,真正的爱情,真正的人生呢,却只是最后的安眠药,最后收音机里的音乐,最后镜子里的面容。
却是遇见一个男人,在大雨滂沱的夜晚,她活在了他的伞下,在孤寂恐惧的时候,她活在了他的身边,在歇斯底里的瞬间,她活在了他的面前,这是重返现实的努力,佛丝似乎在寻找一个真实的自己,他是暴雨中的安全港,那一把伞可以遮挡风雨可以带来温暖,她是满足的,尽管他送她上公交车的时候,她拒绝坐下来拒绝转身,因为“人们会认出我,还有人会和我讲话。”被认出,并且和人讲话,她就会变成曾经的自己,就会变成电影里的角色,就难以走出那个过去的时代,所以对于罗伯特,她像是一次奇遇中的感恩,在充满了逃避的现实里,他让他看见了活着的自己。“在你不知道我是维洛妮卡佛丝的情况下,我再一次感觉自己像一个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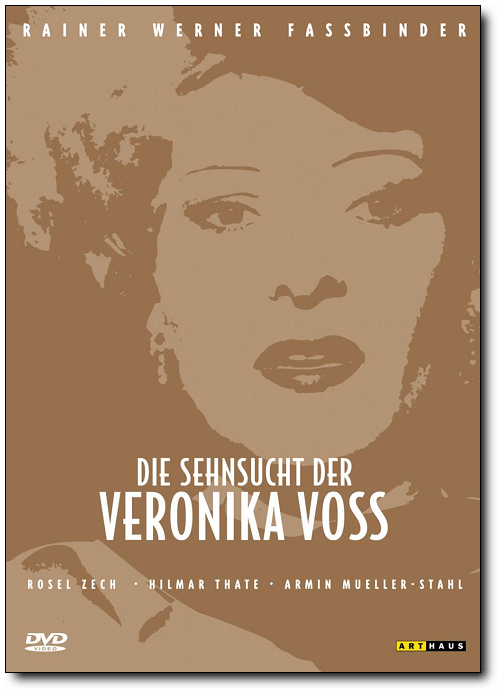 |
| 《维洛妮卡佛丝》电影海报 |
像一个人,却成为一种理想,对于卡佛丝来说,这是对自己的超越,所以她像一个人那样,打电话给只见过一面的罗伯特;所以她像一个人那样,去找罗伯特,并把他从女友身边带走,只为陪她一个晚上;所以她像一个人那样,在难受的时候要让他送自己去卡特兹的诊所。像一个人,就是去掉身上关于昔日超级电影明星的光环,就是褪去曾经的辉煌和荣光,就是忘记曾经的付出和得到,单纯地把自己当成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渴望爱的女人。即使她在那个夜晚,在死去的屋子里说出:“我喜欢诱惑无防备的男人”,那一种欲望也完全像一个正常女人那样的欲望。
关掉灯,点上蜡烛,告诉名字,或者是一种吻,像一个人那样不活在过去的记忆里,卡佛丝是朝着“现在一切都好了”的方向走下去的。但是,她无法真正像一个人,无法真正像一个女人,在她的内心深处,有着巨大的矛盾,像黑和白的对立一样缠绕着她,让她在小心翼翼走出来之后,又无奈而无力地回到梦幻的世界里。她就是那个带着光明和阴影的漂亮女人,她就是那个希望再现辉煌却又被抛弃的电影明星,无法忘记过去的一切,也无法走近现在的故事。
她总是问罗伯特,自己是不是很漂亮;她在两个人一起的时候,却告诉他:“我不想拍摄电影了,但是无法拒绝。”那借去的300马克买来的胸针无非是一种复旧的情怀,只有这耀眼的一瞬光亮才能照亮她自己。那间屋子曾经生活着她和丈夫,曾经见证着她的青春和爱情,见证着他的辉煌和荣耀,可是当一切都过去之后,只有那遮挡灰尘的白布覆盖在上面,所有的家具,所有生活的印记,都成为了逝去的过去,但是她偏偏要带罗伯特来,偏偏要点起蜡烛,偏偏要喝起美酒,甚至偏偏要上床。不是要忘记这一切,是要记起着一切,所以在床上,她开始难受,所以当罗伯特踢掉了一只古董的花瓶,她就开始大喊大叫,一定要罗伯特赔一只一模一样的,而且要放在原来的位置。
这里的一切都不可更改,这里的一切都不能破坏,所有的秩序、规则都在死去的状态里,但是一种死复活了她的虚荣,也复活了她的孤独,她重新变成高贵的电影明星,重新变成富有的女人,重新需要一种荣耀和膜拜。但是当她“复出”走进电影世界的时候,巴伐利亚3号摄影棚对她来说,却是一个噩梦,试镜几次她都找不到感觉,只好用甘油装作眼泪,表演一个虚假的故事,而最后的倒地,却只能证明在过去和现在的矛盾中,在光明与和阴影的对立中,她只是自己的一曲挽歌。
1944年的电影被取消放映,3年来只拍过一部电影,她的婚姻也完蛋了。这就是对于佛丝现在的注解,“这是一个自然定律。”在无可更改的定律面前,既要“像一个人”,又要复活自己的辉煌,无疑是一个悲剧的开始。而罗伯特,在一场邂逅中走进这个女人,走进这个故事,甚至走进她的欲望,对于他来说,都像是看见了另外一部正在上映的电影。罗伯特的女友对他说:“她疯了,你也会跟着她变疯。”佛丝的离婚丈夫对他说:“她只是灾星,你无能为力,她会毁了你,因为她是一个吸毒者。”光明和阴影,活着和死去,上升和堕落,就在佛丝怪异的现实里,但是罗伯特进入她的世界,不是为了一种爱,不是为了满足欲望,不是窥探明星的隐私,当然更不是感受那种变疯的生活,他说:“我要去救她,我不会让他们毁了他。”
罗伯特看见了对佛丝最大的威胁,就是卡特兹的那家诊所,因为佛丝的毒瘾就是在这家诊所里染上的,而一旦染上,她只能在自己痛苦的时候求助于医生为她注射吗啡,而在这种无法自拔的“救助”中,她把所有的财产都抵押了进去,实际上这就是一个阴谋。所以罗伯特的解救计划,就是要将佛丝带离这深渊,他的女友化装成空虚无聊的贵妇人,轻易得到了吗啡注射的证据,但是这样的证据在阴险的卡特兹医生及其助手、官员的联合下,变成了另一场悲剧,罗伯特的女友被他们撞死,然后被更换了处方,毁灭了证据。当罗伯特带领警察控告他们的阴谋时,警察却得不到任何证据,而正在房间里的佛丝却早已成为一个真正的病人,她拒绝离开,拒绝告诉真相,反而将卡特兹说成自己最好的朋友。
解救计划失败,其实是罗伯特无法真正走进佛丝的世界,无法在光明和阴影对立中看见一个真实的女人,她只活在过去的电影里,只活在烛光的夜晚,只活在旧花瓶的虚荣里,只活在药物的麻痹里,而罗伯特其实早就遇见了自己在故事中的结局,一个记者,爱好写诗,在偶遇佛丝的时候,他写道:“晚上听见了从未听过的事/安拉的第一百个名字/当莫扎特死时鼓点没有记下/对话在发源地得到领会。”这是他从未遇到过的事,而这件事的背后是一种死,一种没有记下鼓点的死,一种只在过去的对话里。而在调查佛丝的时候,在打字机上,他写道:“记忆的耗尽/我是五个玻璃球/前途一片渺茫/昨天是很好的一天/今天魔鬼就跟在了后面。”女友念出了诗,他却大发雷霆,因为他想到某种记忆耗尽的时候,前途渺茫,而“昨天是很好的一天”带来的结果是魔鬼出现在身后。
终于走不出那一间到处是白色的诊所房间,白色如同覆盖着那间老去屋子里的物品,白色如同遮掩了过去荣耀的那种炫目,白色,如同吗啡注入身体时的那种透明,是抑制一种痛却让人再无法摆脱。但是白色的世界并不仅仅只是卡佛丝一种悲剧人生的颜色,那一种毒并不只在这个女人的身体里,实际上,它是德国命运的写照,痛也是国家身上带着的痛。收音机里总是播报着战后德国的现实,一个国家的命运是回到曾经的辉煌,还是“像一个人一样”回归?但是在光明与阴影的矛盾里,和佛丝一样,无法摆脱。
佛丝过去的辉煌,就在纳粹德国的历史里,罗伯特女同事告诉他:“她是戈培尔的女弟子,演了不知道多少部电影。”用佛丝自己的话就是:“当一个女演员演一个想去满足一个男人的女人,她想把世界上所有的女人演成一个。她需要音乐,灯光还有酒。”在音乐、灯光和酒的世界里,一个国家其实是糜烂和腐朽的,是濒临死亡的,所以要想从那段历史中走出来,就必须自我救赎,正像和她一样经常去诊所治疗的特勒贝尔夫妇说的那样:“我渴望她最后的善行。”一对老人,曾经就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痛苦的伤害者,特雷贝尔的手臂上赫然刻着“7927”这个数字,他说出的一个词是“特雷布林卡”。这是关于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符号,所以老人在这个带着病毒的国家里,最后选择了用蜂蜜水自杀,“带着最后的甜味离开”,是想为自己的痛苦人生寻找一种安慰。
旧花瓶终归是碎了,有人却想要一模一样的东西来维持那一种逝去的辉煌,而这种感觉只能是佛丝最后赴死之前的梦幻,而在1955年,以佛丝为原型的德国女演员席贝丽·史密兹自杀,饱受离婚、病痛和麻醉剂折磨的她,曾经就是纳粹德国炙手可热的红人。1955年,是这个国家在最后的痛苦中迎来未知现实的一年,而1955年,这个国家的哲学家泰奥多·阿多诺写下了“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句经典句子,恐怖之后,死亡之后,还有什么可以拯救?当罗伯特以一个诗人的身份写下那几句诗的时候,在“前途一片渺茫”的现实里,在“昨天是很好的一天”的虚幻中,在“今天魔鬼就跟在了后面”的恐怖中,奥斯维辛却还在那里,在那间屋子里,在那只旧花瓶里,在那张报纸上,在“现在一切都好了”的一场“胜利”祝福中。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4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