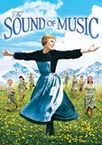2017-05-08 《音乐之声》:爱是一种向上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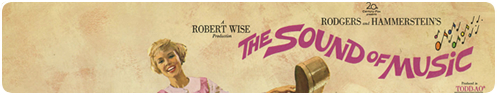
她终于回来了,这是她第二次走进这个森严、古板却渗透着快乐的地方,与第一次不同的是,她不再穿着所有衣服都送给穷人却只留下的那件粗布衣服,不再小心翼翼地敲响隔开了外面世界的铁门,甚至,这次回来,她也不再以一个家庭教师的职业身份独立在范崔普家庭之外,她回来,是因为有孩子,是因为有音乐,是因为有着欲罢不能的男女之爱。
玛利亚,一个和圣母一样名字的修女,离开和回来,在这转身而重新定义自己的过程中,的确发现了属于自己的东西,就如修道院的院长所说,离开修道院,“这是上帝的旨意。”而再一次离开而到达,却是寻找另一种神圣的爱,“如果你爱这个男人,并不意味着爱上帝少了。”爱不是一种谁多谁少的比例,爱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占有,爱不是在进修室里的躲避,爱是分享,爱是传递,爱是博爱。当玛利亚在修道院里被其他的修女看成是“问题人物”的时候,把自己的一生侍奉给上帝的他们或许也只是看见了爱的局部:她们说她爱惹麻烦,她们说她喜欢爬树,她们说她在弥撒上跳华尔兹,她们说她做什么都迟到。种种,似乎都远离了做一个修女的职责,似乎都背离了一个修行者的身份。
她们唱着“哈利路亚”,他她们做着弥散,她们在唱诗,她们祈祷,这是“她们”的宗教生活,但是对于“问题人物”玛利亚来说,她却在独自一个人的世界里,成为大自然的主人,“我在安特斯山里不会迷路,因为它是我的山。”那里有天空,有雪山,有河流,有平原,有小镇,但是在没有被玛利亚的歌声唤醒之前,它们是寂静的,无声无息地流动,无声无息地存在,“群山让我心中充满了音乐。”只有当玛利亚听从了远山的召唤,这个世界才被唤醒——召唤和唤醒,大自然和人类,其实都在一种相辅相成中成为一个爱的整体。
|
| 导演: 罗伯特·怀斯 |
 |
第一次抵达,其实她带来的就是一种爱,面对不苟言笑的主人范崔普,面对用哨子指挥的森严生活,面对孩子们对家庭教师的排斥,玛利亚也是面对微笑的,也是“做得比最好更好。”当范崔普像管理军队一样管理自己的孩子,那哨声响起的时候,玛利亚说:“只有对动物,才用哨子。”当孩子们在她面前说讨厌家庭教师,说她的衣服最丑,告诉父亲少管闲事,她却取消了哨声,让他们一个个报出自己的名字。作为这个家庭的第12个家庭教师,她似乎会和以往的11个家庭教师一样最后被离开,甚至会像上一个一样只待2个小时,但是那种微笑,那种爱,那种向往的目光,却让她走进每一个孩子的心里,让她激发每一个孩子的快乐心情。
|
|
| 《音乐之声》电影海报 |
把口袋里放着的蛤蟆说成是“送给我的特殊礼物”,把晚餐凳子上的松果看成是欢迎游戏的一种,把雷电夜担惊受怕的孩子聚拢在一起,对于玛利亚来说,世上一切的东西妒能发现其美好的一面,在“雷公和闪电对话”的隆隆声响里,她却唱起了歌,告诉他们如何去想那些美好的事物,美好的事物是水仙花,是绿草地,死天上的星星,是小猫的胡须,驱逐恐惧,看见美好,这就是玛利亚的人生美学,而这样的人生美学就需要用向上的目光,需要用音乐,用想象,用一种博大的爱。
而在阿尔卑斯山上,带着孩子们在草地上野餐,让他们感受大自然的风情,便是真正打开每个人心中的那扇窗——孩子们在哨子的声音中,在纪律生活里,在不苟言笑的学习中,其实就像上帝关上了门。所以在蓝天之下,在群山之上,在野草之间,他们找到了另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最动听的便是和自然之声一样美妙的音乐,Do-Re-Mi的音符第一次注入了孩子心中,七个音符,对应于七个孩子,就像是属于他们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在玛利亚弹奏和欢唱中完成了孩子们启蒙式的命名,音符是小鹿,是阳光,是漫漫的长路,是针线,是茶,是自己,这些关于音符的比喻,也闪烁着大自然的光泽,所以玛利亚带领孩子们唱响的不是音符,而是生活之爱,大自然之爱。
而真正激活那一种爱的是让音乐重新在死亡的沉寂之后回到这个家庭,从维也纳回来的范崔普得知孩子们在外面疯天疯地,还如顽童一般爬了树翻了小船,自然是对自己纪律生活的解构,于是大为发火,并且就地解雇了玛利亚家庭教师的职务,让她回到修道院。似乎路又走到了起点,似乎那扇窗也被关闭了,但是,这个房子里却传出了久违的音乐,缓缓流淌,一下子击中了范崔普,他走向正在唱歌的孩子,他也开始放声歌唱,他和孩子们抱在一起,他终于对玛利亚说:“谢谢你将音乐重新带回到这个家,你留下吧,”
音乐从那扇并没有关闭的窗户中传出,音乐带来的不是回忆,而是超越,而是突围——一向严肃的范崔普的脸上终于也显出了笑容。而音乐更是一种爱的表达,在第一次大型的派对上,在第一次和玛利亚相拥舞蹈死,他发现了她的美,她感受到了他的爱,大型派对其实是两个人的舞会,就如那位夫人所说:“你们是天生的一对。”不是郎才女貌,而是对于音乐,对于爱的契合。爱并不是刹那间降临的,当他们在分离之后重新走到一起的时候,范崔普说,从那么松果开始就爱上了,而玛利亚说,是从那哨声开始有了感觉的。松果和哨声,其实像是一见钟情的见证,但是对于同样喜欢音乐,同样内心隐藏着爱的他们来说,这只不过是一种契合,就在那时抵达,就在那时发生,于你于我,就是一个整体。
但这或者只是两女之间私有的爱情,当玛利亚离开之后第二次走进这个家,她似乎完成了自我的命名,曾经他和她,是主人和家庭教师,是舰长和修女,而现在,他变成了一个目光里含着爱的男人,她,变成了追求一种神圣之爱的女人,曾经的逃避,曾经的迷惑,“只有让他远离我才会安全。”玛利亚躲在修道院里,不敢面对前来寻找的那些孩子们,但是在宽容的修道院院长面前,这种躲避和害怕不见了,它们都变成了面对生活的勇气,“男女之间的爱也是神圣的。”作为一个修女来说,侍奉上帝并不是抹杀自己爱与被爱的天性,爱需要的是传递,需要的是容纳,而实际上,当玛利亚再次回去的时候,这种神圣性也让她和范崔普之间的爱超越了单纯的男女之爱。
男女之爱,在这里曾经发生过,也正在发生,他们是劳夫和莉莎之间纯正的爱,他们是范崔普和公爵夫人走向婚姻的爱,但是当这种爱没有了神圣性,它们就会变成自私的爱,脆弱的爱,劳夫在那一封封电报的传递中,最后在纳粹占领奥地利后变成了高喊“希特勒万岁”的投降派,而公爵夫人,爱着范崔普,却在发现玛利亚和范崔普之间动情的爱之后,偷偷地劝玛利亚回到修道院,让这个男人回到自己身边。所以自私的爱变成脆弱的爱,甚至变成了背叛——当范崔普最后逃离的时候,在修道院被身着纳粹衣服、拿着枪的劳夫发现,当范崔普对他说:“跟我们跑吧,你永远不会跟他们一样的。”但是劳夫还是大声喊道:“上尉,他们在这里!”
也许自私的爱才能衬托那种永恒的爱,玛利亚回到了范崔普身边,终于她不再是家庭教师,不再是修女,披上婚纱的那一刻,她甚至成了孩子们的妈妈,上帝关上了门,果真打开了一扇窗,“你寻求的是自己的生命。”所以爱是生命最本真的颜色,爱是内心最真诚的音乐。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实现爱的更大问题便是现实之困。这是一个战争正在发生的时代,这是一个国家正在陷落的时代,但是对于一个曾经是海军舰长的范崔普来说,内心永远是对于祖国的忠诚,永远是一个军人的勇敢,永远是一个男人的独立,当劳夫把电报送给他说出那句“希特勒万岁”的时候,范崔普对他只有一个字:滚;当在大型派对上,吉勒告诉他奥地利危险了,范崔普却讽刺他,你只能做一个为纳粹吹号的丑角;当纳粹终于占领奥地利,每一家都需要悬挂纳粹国旗,和玛利亚一起度蜜月回来的范崔普狠狠地扯下了那一面象征奴役的纳粹旗。
但是德国纳粹占领了奥地利,柏林来的电报让范崔普必须接受纳粹的任职,“拒绝的话全家将会受罚,接受的话……”在这个两难境地里,范崔普的担心更多在于孩子,在于妻子,而这无非是不想让爱成为牺牲品,也或者只有爱,只有音乐才可以解救他们。在萨尔斯堡音乐会上,范崔普家庭歌咏团演唱了启蒙式爱的《哆来咪》,演唱了美妙式爱的《雪绒花》,演唱了温馨式爱的《晚安,再见》——当在纳粹包围和监视的舞台上,范崔普和玛利亚深情唱起了《雪绒花》,歌声中是对奥地利的热爱之情,是对于生命的礼赞,“你永远含苞茁长,你永远守护我们的家……”在场的观众也跟着一起唱响了《雪绒花》,这是一种民族的力量,一种抗争的精神。
而终于逃离了纳粹控制的一家人,当告别了那个黑夜,登上阿尔卑斯山的时候,他们的心中又响起了美妙的音乐,回望故乡,是对于祖国一种不舍的情谊,而《攀越群山》里,他们的目光向上,看见蓝天,看见雪山,看见草地,看见云朵,爱是神圣,爱是勇敢,爱是自由,“你就站在这里爱着我。”生活就是一首关于爱的歌,响彻云霄,却又回归自我。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7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