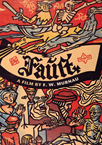2020-05-08《浮士德》:永恒的爱在一天之外

柴火在不断添加,火焰在熊熊燃烧,克雷登被绑在柱子上,作为罪人她接受了审判,也将走向死亡。但是在火刑现场,老年的浮士德不顾一切冲了上去,在烈焰中和年轻的爱人克雷顿吻在一起,当一种死亡变成了爱的仪式,火焰最终变成了太阳的光辉。而魔鬼和浮士德终结的合约,最终也变成了他和上帝之间的一场赌博:上帝说:“这里没有你的位置。”魔鬼却得意地说:“我赢了。”在他看来,克雷顿接受了死刑,浮士德因为爱而出卖了灵魂,他自然赢得了这场赌局的胜利,但是上帝对着得意忘形的魔鬼说:“因为一个字毁了你的合约: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在回响的字,一个带着悲苦和忧伤的字,一个化解人类所有罪恶的字,一个永恒的字,你知道是什么吗?”魔鬼此时才心生疑问,“告诉我是什么字?”上帝对他说:“那就是:爱!”
最后一个字是爱,它从上帝的嘴里说出,从浮士德的故事里得到证实,最终导致耳聋魔鬼的失败,而当魔鬼永远消失,最后的最后,落幕的剧情最后被定格的字就是:爱。一个主题词,不仅仅和浮士德最终得到的救赎有关,不仅仅是上帝和魔鬼的赌局有关,更成为F·W·茂瑙告诉所有人的一个关键词。为什么浮士德最后从年轻人变成老年人,在这场看上去已经输掉的赌局中会让爱成为一个永恒的字?当克雷顿的母亲在魔鬼制造的大风中死去,当克雷顿的哥哥在魔鬼的暗剑中死去,甚至当浮士德在克雷顿生下孩子的悲惨遭遇中消失,浮士德的确在这场和魔鬼的合约中输了,而且在克雷顿在大雪中孤立无援,抱着孩子却被别人嘲笑和拒绝,甚至最后孩子死亡被当成一种罪恶而处以火刑时,浮士德似乎都没有出现,“浮士德,快救救你的孩子!”这几乎成了克雷顿最后的呼喊,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初对克雷顿的爱就只是一种欲望,他不承担苦难,不拥有责任,不付出牺牲,甚至当魔鬼告诉他人们已经添上了柴火,你已经无法就她了,浮士德也已经垂垂老矣,像生命一样,所谓的爱已经终结。
但是在这个时候,浮士德进行了自我忏悔:“原谅我,原谅我的罪过,我宁可没有年轻过,我诅咒自己带来了悲剧。”正是这样的忏悔,让浮士德看到了自己的罪,也让他唤醒了内心深处未被泯灭的爱,所以即使不再年轻,他也冲入烈火中,抱着最爱的克雷顿,而克雷顿也感受到了他的爱,在两个人热吻中,所有的惩罚都变成了他们相爱的背景,这是伴随着烈焰而出现的升华,就在那一刻,不管是年老还是年轻,不管是曾经犯下什么罪,只要内心的爱存在,它就具有了永恒的救赎意义,而这种爱也超越了男女之间简单的个体之爱,变成了上帝预设的那个人类想要获得的爱,像一种至善的存在,变成了大爱,所以上帝告诉魔鬼这个世界再没有他的位置——没有了魔鬼的位置,就没有了罪恶,没有了灵魂的背叛。
当这场赌局最后变成了对于爱的阐述,实际上有一个转变,一方面是茂瑙对于歌德原著的改变,在除却了对于知识、宗教等的拷问之后,只剩下对于爱的考验;而另一方面,当浮士德和魔鬼打赌的那一天结束,浮士德说:“把年轻留给我,我们签一个永久的合约。”这是开始的影像演绎已经和前半部分有了明显的不同:单单就魔鬼的形象来说,起先的他是恶毒的,是丑陋的,是制造了种种陷阱的一个形象,但是在浮士德寻找克雷顿之后,魔鬼完全变成了浮士德身边的一个朋友,像凡人一样,变得可爱,甚至和浮士德一样,徘徊在情感的世界里:克雷顿手拿采来的花,然后一瓣一瓣摘下来,“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一种和花瓣数量有关的随机性,像是对爱情的不确定,但是却隐秘地透露出克雷顿对浮士德的那份爱,而魔鬼也学着克雷顿的样子,也拿着花瓣在一瓣一瓣地数着,“她爱我,她不爱我,她爱我,她不爱我……”面对克雷顿的姨妈马歇,魔鬼的这种举动完全挣脱了那种恶魔的形象,变成了一个有着喜怒哀乐的凡人。
浮士德自从遇到了克雷顿,不仅魔鬼形象发生了改变,整个电影风格也发生了转变,它不再压抑,不再阴暗,不再令人恐惧,那里是嬉戏的孩子,是美丽的花瓣,是如新娘一样的浪漫和幸福,而这也正是浮士德变成年轻人之后,激发他内心爱意的开始,即使后来魔鬼设计害死了克雷顿的母亲,用剑杀死了他的哥哥,还让克雷顿怀孕生子陷入世俗和宗教的惩罚之中,整个过电影风格也是明快的,紧凑的。而在克雷顿出现之前,在浮士德和魔鬼订下合约开始一场灵魂的赌博之时,整个世界让人感到压抑,也令人恐惧:魔鬼制造了人世的恐怖,将生命带入到了战争、瘟疫和饥饿之中,这是一个邪恶的世界:瘟疫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他们的呼喊、哭泣、忏悔和祈祷都不再有用,甚至牧师也死在魔鬼手里,而呆在书斋里的浮士德想要解救人类,也起不到任何意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浮士德呼唤黑暗之神,并且承诺自己和上帝以及诸神都脱离了关系,“我想拥有世界的力量和光辉。”也从这个节点开始,魔鬼和他来了一场赌局,浮士德也变成了魔鬼的影子:“我以魔鬼的名义救你们。”
| 导演: F·W·茂瑙 |
前和后出现的反差,在风格意义上是一种不协调,也正是这种不协调,茂瑙在忠实于歌德的剧本之后走向了自我设计的主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抛却了“浮士德”身上具有的多义性,而专注于一个爱字。但是尽管风格是不同意的,但是在整个电影里,电影的前半部分恰好成为了一种铺设:要完成灵魂的就是,要走向永恒的爱,需要的是从欲望世界走出来——前半部分浮士德的犹豫、害怕,以及和魔鬼签订合约,所有的出发点都是在欲望层面上展开的,因为欲望,所以魔鬼在和上帝对话时显得信心满满:“你知道浮士德吗,他像其他流氓一样,鼓吹善良却无恶不作,他想把生铁变成黄金。”这个浮士德就是欲望驱使下的浮士德,因为魔鬼看到了他属于人类的本质,所以才打赌能够将浮士德的灵魂从上帝那里赶出去,才可以毁掉他身上所谓的神性。
“没有人能抵挡邪恶,我赢定了。”当魔鬼如此定义浮士德定义人类,就是看到了人类身上的欲望之恶,而在这个意义上,魔鬼自己也变成了欲望的化身,甚至在欲望世界里也看不到爱。在人类面临灾难的时候,身为老教授的浮士德用了两种方式试图解救人类,一种是知识,他面对向他求助的女孩,把药水给生病的母亲喝下去,但是药水没有让母亲没有恢复,反而加速了她的死亡——这是知识之死;另一种则是宗教,很多人都来到了教堂,但是在魔鬼制造的瘟疫中,相信上帝的人没有免灾,甚至牧师自己也死了——这是信仰之死,“信仰没用,知识没用,我输定了。”浮士德如此感慨,不是知识没效,也不是信仰无用,而是这些所谓的知识和信仰,在功利性目的意义上,它们就是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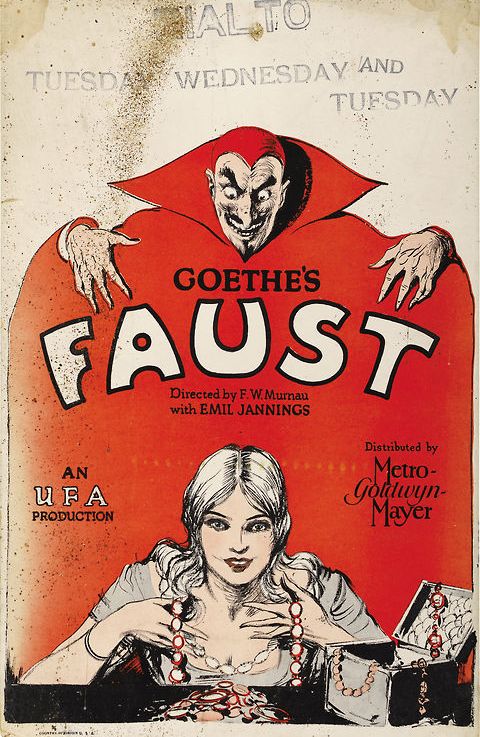
《浮士德》电影海报
当然,当魔鬼让他变得年轻,更是欲望的直接体现,“欢乐才是真正的生活。”魔鬼带他领略山川的壮丽,带他看见世界的美好,带他去帕尔马公爵女儿的婚礼,这些都是一种感官上的欲望满足,但浮士德面对漂亮的新娘,竟不顾身边的新郎和她上床,完全变成了欲望生活,而魔鬼就是要将一切可以被欲望呈现的东西给他,让他失去灵魂,才能赢得这场赌局,而浮士德也因此希望自己永远年轻,当一天的合约结束,浮士德恳求道:“签一个永久的合约吧。”对于魔鬼来说,一天的合约已经让他陷入到了欲望世界里,永久和约更会让他难以自拔,会失去最后的灵魂,所以他也答应了,恶让浮士德希望签订合约的目的也的确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但是正是从这个一天之外的合约开始,他有了对于欲望超越的机会,有了唤醒内心之爱的可能。
遇到克雷顿,就是慢慢从欲望演变为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茂瑙其实设置了纯为欲望的几个情节表现:马歇姨妈研制了可以让男人拥有所有女人的药水,一方面那些用这些药水的男人就是为了满足欲望,另一方面马歇的这些药水都是假的,无非是骗取他们的钱财,这又是欲望的体现;而魔鬼看到之后又在药水里加了一些特殊的成分,致使马歇在喝下药水后神魂颠倒,甚至喜欢上了魔鬼,而魔鬼也摘着花瓣想要知道马歇爱不爱自己,两个人也都被欲望控制了;魔鬼想要用项链控制克雷顿,因为戴上这条项链之后就能看见魔鬼的力量,就是想让克雷顿对浮士德的爱也变成欲望;魔鬼杀死了克雷顿的母亲和哥哥,又加害于浮士德,这当然是阻止他付出真正的爱;浮士德消失,克雷顿一个人生下孩子在风雪中挣扎最后成为罪人,也都是魔鬼设计让浮士德成为欲望的象征,在有罪的世界里失去克雷顿对他最后的爱。
一切都在欲望中展开,一切都变成欲望的具体表现,而制造这一切的都是魔鬼,或者说,魔鬼是欲望之恶的化身,他想要控制浮士德赢定这个赌局就是通过欲望的满足让他失去灵魂失去神性,而最后,魔鬼自己也陷入到欲望世界里,甚至他自己也难以自拔,所以浮士德命题也成了魔鬼命题。而浮士德从年老变为年轻,享受了繁华,遇见了爱情,他的确是在欲望的驱使下获得这一切的,但是正如上帝所说:“最美妙的是人们有选择善良和邪恶的自由。”这才是人类最大的意义,也正是在这个一天之外的合约里,浮士德慢慢找到了自己,慢慢找到了爱,在没有了束缚人的知识,没有了空泛的信仰之后,在超越了欲望之后,面对熊熊燃起的大火,面对自己年老的命运之后,面对一生都坚守着爱的克雷顿之后,他终于完成了自我的救赎,这是灵魂的回归,这是神性的保留,当然,它们都以最终极的爱的形式出现,“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在回响的字,一个带着悲苦和忧伤的字,一个化解人类所有罪恶的字,一个永恒的字。”这个字不在充满欲望之恶的魔鬼身上,只在作为至善的上帝化身的人类身上:是火刑之中的救赎,是一天之外的永恒。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913]
顾后:《日出》:现实是无梦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