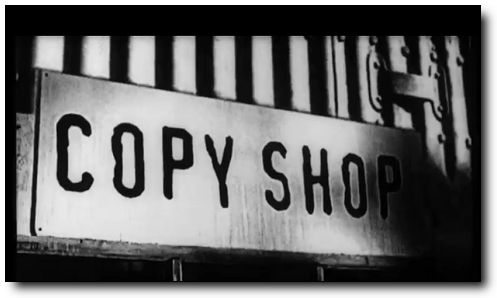2017-10-12 《复印店》:世界是无数的他们?

闪现、定格、重复,“COPY SHOP”的商店招牌以这样一种方式出现的时候,复印店的复制隐喻就已经明白无误地展现开来。但是当从物的复制,到人的复制,再到意识和思想的复制,形成一个被他们围绕的复制世界的时候,导演维吉尔·维德里希似乎并不只是在阐述一种机械复制的时代悲剧,在镜头的解读中,其实隐含着一种突围的努力。
突围之前是包围和陷入。这是一个从单数走向复数的过程。起先是在复印店工作的员工阿尔弗莱德·凯格尔的日常生活,他被闹钟叫醒,他起床,他走到卫生间洗脸、梳头,他下楼出门,他经过街道,他看见街上各式各样的人,他打开复印店的门,他从柜子里取出复印材料,他在复印机上开始复印,他在复印完毕之后拔下插头,关上门,返回家里。这是阿尔弗莱德·凯格尔的工作和生活,尽管有无数个动作,但是每一个动作的主体都是一个他,这是唯一的他,所以在一天这个被封闭的时间里,生活并非是重复的——尽管在起床洗漱的时候,他是站在镜子前看见了另一个自己,但是仅仅是作为一种照见自己的存在,镜子前真实的自己,镜子里的虚像,也并非形成一个镜像化的自己。
但是如果把这一天固定在唯一的一天,把他定义为一个人的他,这样的日常生活是正常的。但是维吉尔·维德里希给了他一个发现自己副本的机会。第二天还是被闹钟叫醒,还是起床洗漱,还是下楼出门,还是进入复印店,还是在复印机上复印文件,这样重复便出现了,而这样的重复本身也是日常生活的写照,但是维吉尔·维德里希显然用这样一种隐喻来隐射人之存在的无聊感。复制生活开始了,当阿尔弗莱德·凯格尔无意中把手放在复印机里的时候,那张纸上出现了自己的一只手,五指清晰,脉络清晰,这是一次意外的发现,而这种意外却直接让复制生活从物的状态过渡到了人的状态。
|
| 导演: 维吉尔·维德里希 |
 |
于是,无法遏制的人的复制开始了。又是起床、洗漱、出门、上班,但是在阿尔弗莱德·凯格尔后面却出现了一模一样的人,这是自我之外的一个副本,这个副本尾随着阿尔弗莱德·凯格尔本人,也是起床、洗漱、出门,但是尾随的意义并不是重复阿尔弗莱德·凯格尔本人的动作,他的尾随,他的偷窥,都在阐述另一种生活,一种区别于本人的行为,所以在复印店里,当阿尔弗莱德·凯格尔抬头看窗外的时候,发现门外有另一个自己。看与被看其实构成了一种关系,这是母体和副本的关系,而随着复制的不断深入,这种关系在数量上变成了一种灾难。阿尔弗莱德·凯格尔回家,尾随的另一个自己也回家,但是当在房间里的时候,他们一起发现了第三个自己:他被闹钟吵醒,他从床上起来,他在镜子前洗漱——而且他也发现了自己之外的另外两个自己。还是一种看与被看的关系,在彼此的观照中,母体和副本还没有被混淆。但是当在橱柜里发现第四个自己,在床上发现第五个副本,那种关系就慢慢解体了。
|
|
| 《复印店》剧照 |
也就是说,在不断复制日常生活中,在不断复制自己的过程中,那个最初的母体已经在数量的增殖中消失了,他在混乱中已经失去了可辨别的可能。而随着副本的不断增多,人的复制变成了一场灾难:到处是自己,自己被自己追赶,自己和自己相遇,自己经过自己,自己看着自己,无法辨认的自己,其实都不是自己。即使在复印店里拔掉了插头,关上了大门,这种混乱依然无法避免。从物的复制到人的复制,从静态的拷贝到动态的模仿,这是一种灾难的蔓延和扩展,也是对于人之存在的荒谬阐述。
但是这还不是最后的灾难,在启动人的复制之后,另一种更危险的复制开始了,那就是对于意识和思想的复制,当不知道是母体还是副本的阿尔弗莱德·凯格尔走出房间,他在街上再也看不见曾经和自己不一样的那些人,看报的他人变成了自己,遛狗的别人成了自己,卖花的女人成了自己——是他们变成了自己,还是自己变成了他们?当所有人都穿着同样的衣服,长着同样的面孔,一样在奔波,其实就是取消了人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也就是取消了人独特的意识和思想。这是集体无意识的世界,每个人都变成了副本,在没有差距、没有区别的现实里,人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甚至死亡。当阿尔弗莱德·凯格尔爬上高高的烟囱,他看到所有的烟囱上都站满了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而当他纵身跃下的时候,底下也都是被复制的自己——死亡有什么意义?一个人的死既不崇高也不卑微,既不是悲伤也不是刺激,它仅仅是无数人重复的动作。
物的复制是数量意义上的重复,人的复制是主体意义上的扁平化,而思想和意识的复制则变成了最后的无意义,很明显,从日常生活的单调机械,到人作为主体的丧失,所折射的是机械复制时代的一个悲剧,当从高高的烟囱跳下的时候,这种悲剧便以最荒谬的方式划上了句号:跳下去的是一个活动的人,而其实他只是一张复印纸,生命消失的瞬间,就像一张纸被撕碎,人的死亡又轮回到物的破坏和消失。复制的三个阶段造成人的副本化生存,但是在这个隐射当代人“群体性复制现象”的寓言中,是不是一切都是悲观的?
导演维吉尔·维德里希在制造这个时代悲剧的同时,却以另一种方式保留了某种希望,那就是母体并没有完全在复制中取消,并没有在混乱中永远消失,也就是说,在这种机械复制时代,副本背后还存在着一个隐形的母体,也就是唯一的自己。一开始就闪现的“COPY SHOP”是复制的征兆,但是这种征兆是如何产生的?当我们看到它在闪现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被镜头控制的,也就是说,复制只是镜头在复制,它以光影和声音的方式告诉我们,复制开始了。在复印店里,阿尔弗莱德·凯格尔看见了自己被复印的手,而在这种手的复印件之后,他也看见了自己在床上的那张照片,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潜在的主体:手是阿尔弗莱德·凯格尔自己复制的,那么在床上的场景是谁拍摄的?显然不是阿尔弗莱德·凯格尔,而是导演维吉尔·维德里希,也就说,他利用摄像机的功能,把阿尔弗莱德·凯格尔母体之外的场景推到他面前,从而变成他复制的东西,这种转换是隐秘的,复印机扫描声和照相的快门声配合切换实现了这样的主题,所以,在看似阿尔弗莱德·凯格尔主体被取消的复制过程中,导演维吉尔·维德里希完全变成了另一个生产者。
他拍摄,他复制,他推送,他制造恐惧和不安,而且在复制过程中,当人的复制不可遏制的时候,物的复制却停止了,为什么不能有租住的房子的复制品?为什么不能把复印店也变成无数个?人变成淹没的海洋,而所有外在的东西都保持了唯一性,这或者是导演维吉尔·维德里希的一种疏忽,甚至是败笔,但也为这个机械复制时代提供了突围的可能。在维吉尔·维德里希的镜头下,无数个副本的混乱状态中,始终有一个潜在的母体,这个母体看见了尾随的副本,看见了窥视的副本,这种看见就是一种主体的视角,而在他发现被无数的副本包围的时候,开始了逃跑计划,乃至最后爬上了烟囱,在这一系列过程中,他始终是那个母体,始终是那个唯一的自己,甚至始终是有意识、有思想的“第一个”,他所作的动作都是主动的,而这也在副本的淹没中保留了一种突围的方向。
导演是生产者,也是复制的制造者,所以当人是自己复数的生产者,唯一能打破的就是取消人的复制思想,从而回归到单一主体的现实里,当从高高的烟囱坠落而下的时候,一张纸被撕碎,而这也证明了结束这样的循环和复制,唯有破坏和解构才能最终完成——一片黑屏中,再无复制,再无副本,再无集体无意识。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895]
思前: 《瑞恩》:他活在艺术家的恐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