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25《愤怒的帕索里尼》:我写下你的名字:自由

我写下的是“疯狂的帕索里尼”,A4纸反面的电影笔记上,但后来发现错了,疯狂和发怒都是一种态度,但是疯狂似乎更在于自我主体的意识,而愤怒一定是有一个对象。但是当改成“愤怒的帕索里尼”时,似乎又感觉到某种误读。不懂意大利语,电影的片名是La Rabbia di Pasolini,但是当电影被播放出来,片名其实是La Rabbia——没有di Pasolini,也就是说,“di Pasolini”是一种电影主题的附加成分,或者可以称之为“帕索里尼拍的愤怒”的电影,或者可以说成是“帕索里尼关于愤怒”的纪录片。
当“愤怒的帕索里尼”变成“帕索里尼的愤怒”,词序的变化似乎隐含着对于电影主题解读的微妙变化,“帕索里尼的愤怒”比“愤怒的帕索里尼”范围更广,意义更多元,它既可以指帕索里尼自己的愤怒,也可以指帕索里尼拍摄的“愤怒”——世界对世界的愤怒,人对人的愤怒,阶级对阶级的愤怒,而这种愤怒一定是不同的世界、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阶级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正是这个多元化的“愤怒”,使得整部纪录片带有了更为广阔的视角,更为立体的层次,以及更为呼应的结构——在九万米胶卷上剪辑出的那些“象征性事件”,正好建立了战后关于“愤怒”的普遍性情绪。
而其实,电影里有着基于个人立场的“帕索里尼的愤怒”。这是帕索里尼1963年拍摄的一部纪录片,而实际上呈现出来的是2008年的修复版本,但是2008年修复的也并非只是1963年帕索里尼的版本,纪录片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于纪录片修复的解说,第二部分才是在“象征性事件中”关于愤怒的主题,而第三部分则转向帕索里尼的个体记录。“愤怒”出现在每一个部分里,而第一和第三个部分则更多是帕索里尼对于对象的一种“愤怒”态度。1962年帕索里尼接受《自由世界》采访时,宣布自己要拍摄一部纪录片,而且已经写好了解说词,但是制片人“或者出于政治考虑或者为了商业利益”,由一个人完成本来四个人的工作,乔瓦尼·古阿雷西成为这部片子的导演,于是,“帕索里尼愤怒了”——但是最终又同意了,于是,在这部纪录片里,主题部分有分成两部分:乔万尼剪辑的影像和帕索里尼剪辑的影像。
而在第三部分里,帕索里尼的“愤怒”则变得有些频繁,这是由几个关于帕索里尼的短片组成,“镇上话题”涉及到了帕索里尼拍摄《乞丐》《大鸟和小鸟》等电影时的场景,戴着墨镜的帕索里尼对于那些攻击自己的人感到愤怒,称他们是“卑鄙的联盟”,尤其对着想要采访他的记者说,这是对于私人生活的侵犯;还有一段来自迪诺·韦德1963年的电影《斯堪佐纳迪斯莫》,三个在舞台上做出夸张动作的女演员说自己是帕索里尼电影的主角,一个是妓女艾玛,一个是皮条客罗姆洛,一个则是吝啬鬼南多,他们在跳舞时表达了对于帕索里尼“愤怒”的支持:“我们要捍卫先知帕索里尼,他受到了攻击。”然后三个人开始唱起歌来,其中一句是:“只要我们三个,帕索里尼就富可敌国……”没有看过迪诺·韦德的电影《斯堪佐纳迪斯莫》,也不知道妓女艾玛、皮条客罗姆洛和吝啬鬼南多映射的是谁,但至少在帕索里尼的《乞丐》《罗马妈妈》等电影中,都有这些处于低层的妓女、皮条客和吝啬鬼,而他们对于帕索里尼的声援,在某种程度上和第一个片段帕索里尼自己的愤怒有着一种呼应关系。而第三个片段则是帕索里尼接受采访时说到了愤怒,一方面他所说的“愤怒”是自己的愤怒,而且说自己的愤怒难以贴上标签,只是意大利少数人的愤怒,但是这其实是个伏笔,并不会说自己的愤怒无足轻重就否定愤怒的意义,帕索里尼的用意在于批判:“意大利没有愤青,只有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愤怒是小小的愤怒;在意大利有独一无二的抵抗组织,他们的愤怒是组织上的愤怒,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方式;现在的意大利,革命只是一种借用道德的形式,而天主教只是在自我安慰……”意大利没有真正的愤青,所以没有真正的愤怒,无论是抵抗组织还是宗教形式,都不是真正的愤怒。但是帕索里尼却说到了一种愤怒的样板:“历史里最出色的愤青,是苏格拉底。他的愤怒不是革命者的愤怒,而是那种衣衫褴褛,在雅典运动场里的踟蹰而行的姿态所代表的愤怒。”
第三个部分对于解读“帕索里尼的愤怒”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帕索里尼在场,帕索里尼言说,帕索里尼愤怒,在他看来,意大利没有真正的愤青,没有真正的愤怒,所以他要愤怒,而他的愤怒是追随着苏格拉底的愤怒,是一种不是对于“借用道德的形式”的革命的继承,也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抵抗运动的实践,而是以愤青的身份对于政治生活的一种批判,于是从苏格拉底的典型意义出发,回到关于愤怒的问题:帕索里尼为什么要愤怒?似乎有了一种解读的进口。而从第二部分对于愤怒的主题阐述来看,乔万尼的剪辑和制作和帕索里尼1963年的版本又有着某种差异。
| 导演: 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 / 朱塞佩·贝托鲁奇 |
乔万尼的视角关注的是战后的世界格局,一种含混的现实,他的愤怒指向的目标是资产阶级,而这个资产阶级在他那里是残暴的,是卑鄙的,所以要愤怒。乔万尼的纪录片从意大利胜利日仪式开始,是胜利,是狂欢,也是死亡,是哀悼,当那些在战场上牺牲的士兵骨灰被运送回来,这个胜利日其实弥漫着哀痛的情绪,那些死去战士的家属和亲人失声痛哭,这是政治家最后的光荣,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却只是“三等舱的葬礼”,所以,“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都被它打败了。”它是比胜利和失败这个单纯的结果更深刻的关于生命的无力感,无论是在政治家的光荣面前,还是在三等舱的葬礼的悲伤面前,“生命的死亡都没有了意义”。当战争结束,战后的世界其实依然是一种无意义的开始,镜头里是1953年意大利的第一辆运煤车,是投产的钢厂,是“意大利将成为欧洲重新崛起的领头雁”的演讲,“卑鄙的资产阶级!”愤怒开始了,即使战后从苏联归来的战俘回到了乌迪内,这是一种生命的重生?即使意大利帕威尔的音乐节举行有人用鼻子吹奏乐器,这是美好生活的开始?即使电视问世带来了新的了解世界的方式,这依然是“一知半解的真相”。而且从意大利到世界各地,似乎这种卑鄙和残暴并没有彻底消失,朝鲜战争还在发生,所谓的协议签署,战俘释放,停火开始,这是一种“和平的希望”?而从英国到法国,从德国到澳大利亚,洪水肆虐,这些自然灾害更是带走了生命和希望,于是,愤怒的世界里没有自由,有的只是“人间的邪恶自由了”。
乔万尼的愤怒指向的是战后资产阶级的虚伪本性,是对于生命的漠视,而这种结局和战前有什么不同?所以,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都被它打败了。而转向1963年帕索里尼的纪录片,关于愤怒虽然也是在生命层面上,虽然也提出了关于自由的渴望,但是帕索里尼显然是站在诗人的角度,站在哲学的高度,用苏格拉底的愤怒来武装自己,来表达诉求,来批判现实。“为何我们的生命被不满和愤怒所主宰?”这是1963年的纪录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也是帕索里尼以“诗人的愤怒”倾注情感的一个线索。生命是世界的组成部分,是历史的微小单位,生命之存在和逝去,看起来是个体意义上的事件,但是折射的是一种人文意义的态度。其实帕索里尼对于生命的关注,选取了革命、宗教和艺术三个宏大主题,在这三个主题中,个人的生命其实是被掩盖的,他们是无声的群体,是绝望的个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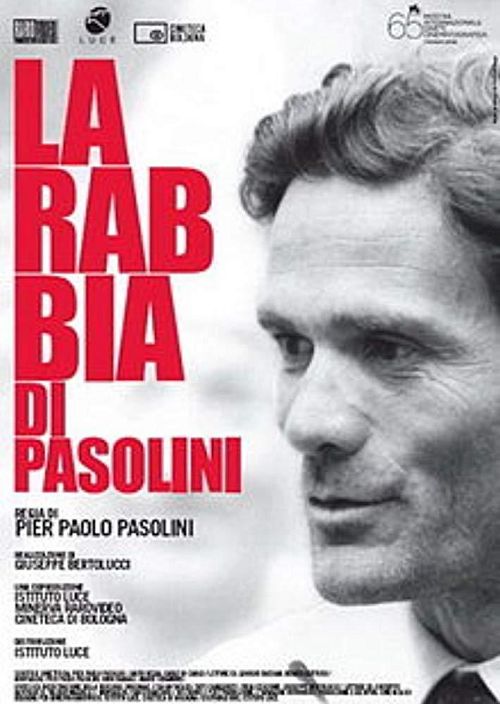
《帕索里尼的愤怒》电影海报
从匈牙利到埃及,从印尼到印度,从突尼斯到刚果,从欧洲到亚洲到非洲,其实战争远没有结束,对立一直存在,“这是黑色的冬天,黑色的夜晚,黑色的城市,黑色的记忆,黑色的和平……”一连串的黑色呈现了这个世界的黑暗现实,在以革命为名的斗争中,权力以不同的面目出现,而每一种权力的更替,都是为生命制造了黑色的结局,那些被绑住的黑人,那些寻找乳房的孩子,那些被驱逐的老人和孩子,“死亡风暴席卷了要求个体自由和尊严的人民……”而且对立和冲突甚至演变成对于有色人种的某种戕害,有色人种何罪?“唯一的颜色是人在面对自身黑暗时快乐的颜色,胜利中的唯一颜色是人的颜色……”所以即使对立消除,即使胜败有了结局,对于要求个体自由的人来说,依然是无尽的恐惧。
而从政治转向宗教,在信仰意义上个体会有自由吗?“一面红旗背叛了重现的上帝形象”,那个上帝的雕像在仪式结束后缓缓沉入了水下,重现的上帝消失了,世界走向了“诗人工业家”的开始,当机器转动起来,信仰依然在迷失,依然在沉沦。伦敦举行了伊丽莎白加冕仪式,她说了一句“上帝助我一臂之力”,人群高喊:“上帝拯救女王!”教皇的葬礼正在举行,主流的声音依然是对于宗教的渴望,甚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成为了兄弟,但是在葬礼之后是新教皇带着诡异的微笑;列宁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结束了沙皇官僚的历史,也结束了清教徒暴力的历史,但是那些苏联集体农庄的妇女,那些矿区里的工人,小镇上的建筑工人,他们真的在伟大的国家里成为被拯救者?
宗教依然是政治的一部分,而政治也无非是权力的争夺,“阶级斗争尚未结束”,于是,那些工人、小职员、苦难者、文盲群众,非洲的穷人,无产者,身上依然伤痕累累,目光依然是茫然和无助,“欢迎接着欢迎,胜利连着胜利”变成了对于这个世界的无尽讽刺,于是帕索里尼大声喊道:“我写下你的名字:自由!”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强调,但是自由之乌有,生命依然是一曲悲歌。而转向美国,所谓的民主国家,却在被制造的美中上演了资本的神话,却在现代的生活中成为道德的顽疾,那架飞机上的飞行员说:“文明在彼岸凯旋,我侵入天空,纯净的飞行之下是丑恶的世界。”只是飞行,一种脱离了束缚的自由,但是自由只是一种表象,丑恶的世界依然还在底下铺陈开来。
黑色是政治上的有色人种,上帝被一面旗帜背叛,现代生活是道德的顽疾,在这种种的形态中,个体的生命在何处?“孩子啊,母亲是个怪物,我们从未存在过。”所以帕索里尼要写下的自由也没有存在过,它只是在天空之上,最后飘散消失。欧洲、世界、地球,目光越来越远,却越来越遁入虚无,所以生命被不满和愤怒所主宰,所以帕索里尼记录愤怒也表达愤怒,而当戴着墨镜的帕索里尼痛斥侵犯了私生活的“卑鄙的联盟”的时候,他就是站在一个生命个体的立场表达愤怒,仿佛苏格拉底的复活,但是小小的愤怒,作为愤青的愤怒,也许也只是在表达一种态度,就像电影本身,愤怒之后,帕索里尼“最终又同意了”。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1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