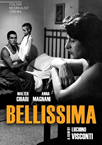2020-03-13《小美人》:一个母亲的成长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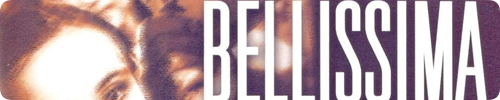
她终于喊出了“你们还没有玩够吗?”的质问,她终于仅仅抱着累坏了的女儿:“她哪儿也不去!”她终于返回了自己的家,对丈夫斯帕塔科说:“我再也不会让她去拍电影了。”一种回归,一种醒悟,一种誓言,是因为从那个被自己囚禁的世界里解脱出来,不是因为导演加码到了200万里拉让她在没有钱付出,也不是因为7岁的女儿玛利亚太小没有表演天分,而是她已经看透了所谓的拍电影只是一场骗局,更重要的是,她从一个迷途者变成了发现自我的人:美达琳娜,一个母亲,一个妻子,以及一个需要住在家里的女人。
美达琳娜回到了家,“我可怜的小房子。”这不是失望,而是新生的怜爱;看着已经入睡的玛利亚,深情地抚摸她的脸,这不是遗憾,而是一种满足;她对丈夫说:“你给我一巴掌吧。”这不是惩罚,而是懊悔的表达;最后她抱着孩子自言自语:“你这个疯子!”这不是蔑视,而是自我的醒悟——当美达琳娜从嘈杂、混乱、欺骗、到处是金钱话题的拍片场所回来,当她在女儿、丈夫的世界里重新生活,对于她来说,就是一种身份转换之后的仪式:她重新变成母亲,变成妻子,就是完成了真正的成长。
玛利亚,是她的女儿,这个七岁的孩子当然需要一种成长,当她在报名现场走失独自在水池边玩耍却被找寻了半天的母亲指责,似乎是一种成长;当她被母亲拉着去剪头发,坐在凳子上的她哭泣着喊:“妈妈,我要回家,我不想在这里。”这似乎也是一种成长;当她去舞蹈学校和那些学了三年的孩子一起做基本动作,因为无法完成而哭泣时,也似乎是一种成长;或者说,当她在选演员的舞台上朗诵、面对导演布拉塞蒂和周围人的目光,这也应该是一种成长;甚至在庭院里被陌生人教着学习如何成为一个要吃草莓的角色,这更应该是一种成长。对于孩子来说,成长是学习,成长是勇气,成长是痛苦,成长是哭泣,但是当一个七岁孩子失去了所有自主的能力,当她的生活完全被母亲所控制的时候,这根本不是成长,而是一种束缚,一种自我的迷失。
所以,关于成长,主体不是玛利亚,玛利亚是在一种缺失的状态中成为一个表象是成长的工具:她学习表演、学习发音、学习跳舞,她被修剪了头发、穿上了漂亮的舞蹈裙,成为走向梦想的主角,都是在偏离成长。所以真正需要成长的是母亲美达琳娜。而在成长之前,美达琳娜已经是一个母亲,一个妻子,至少在身份意义上她已经是成人世界的一部分,但是正是由于他所面对的成人世界,以及她想要为孩子构建的成人世界是一个不真实的世界,所以成长对于她来说也是缺失的,甚至说,她必须通过着种种的磨砺,体悟到了自身的幼稚,察觉到了自我的执迷,她才能真正返回自身,返回那个正常的身份,她才能完成成人所定义的成长。
她给玛利亚报名参加小演员的选拔,在剧场碰到那个赞赏说玛利亚可爱、具有演员天分的埃博托,埃博托告诉她,应该为女儿专业拍摄一张照片,也是美达琳娜便去找专业摄影师;在专业摄影师那里,碰到了刚好也在拍照的母女,她看到了穿着漂亮舞蹈裙子的女孩,于是又打听到可以给玛利亚报名舞蹈班,而且还去订购了漂亮的舞蹈裙子;之后拿着照片带着女儿参加第二轮选拔,又听说女儿的头发不够漂亮,于是又想办法让她去染发,去修剪头发……在整个过程中,玛利亚其实一直在这场选角的外围,她甚至仅仅是一个符合年龄标准的对象,自始至终她都没有积极主动地参与,而她被拉入其中,则完全是美达琳娜的想法——从一开始报名现场走失,便是这一种不在场和被控制的隐喻,玛利亚作为一个孩子,保持着童真,就是离开成人世界去水池边玩,而美达琳娜则四处找寻,最后当找到玛利亚的时候,则训斥她,甚至可惜穿着的那件衣服,因为玩耍而变脏了。
| 导演: 卢基诺·维斯康蒂 |
母女的冲突便是两个世界的矛盾,不管是参加舞蹈班还是去修剪头发,玛利亚都在不在场的状态中,而美达琳娜则强硬把她推了进去,所以在舞蹈班上她哭泣,在修剪头发时她叫喊,“妈妈,我要回家,不要在这里。”玛利亚渴望回家,正是美达琳娜空缺了让她回家的路。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不在场情况下,作为母亲的美达琳娜便开始进入到需要成长的角色中,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弥补女儿的位置,成为一个没有真正成长的女人。这是一种映射,一方面,美达琳娜的决定凌驾于女儿的想法之上,就是一种对于成长的僭越,她强拉着女儿进入各种培训班,完全不顾女儿的想法;她责怪女儿的发音不对,认为这是一种家族病;她处处鼓励她:“我们会成功的。”却是在失败的路上越走越远。
另一方面,她的这些举动也是对于家庭生活的背离。她平常是靠为别人打针服务来赚钱,为了女儿的成功她不断支出,所以她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赚钱,她甚至向别人推荐要不要打针,邻居骂她:“我可不想生病。”美达琳娜则告诉她,没有生病也可以打保健针,或者向亲戚介绍这门业务,似乎这种和疾病有关的服务变成了普通人的需求;而美达琳娜的丈夫也是做一些简单的服务工作,可以说一家人的收入微薄,但是随着女儿投入的加大,入不敷出的矛盾越来越显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美达琳娜选择一些便宜的服务,甚至在为女儿剪头发时,因为自己要去打针,所以希望有人照顾但又想少花钱,结果一个稍微比玛利亚稍大的男孩为她修建了头发,那一头的秀发和辫子被剪掉了,最后回家的玛利亚完全是成人的头型,这种和年龄相悖的发型让丈夫大为生气,而美达琳娜去为女儿参加比赛的所有开支都被隐瞒,当这一切被发现的时候,两个人大吵了一顿,丈夫斯帕塔科甚至对她实施了暴力,而且还想抱着玛利亚离开这个家,只是在邻居对美达琳娜的声援中,斯帕塔科才压住了愤怒。

《小美人》电影海报
把自己的想法凌驾在女儿之上,瞒着丈夫增大开支背离家庭生活,这两方面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种社会化问题:对女儿教育的干涉和操纵,是身为母亲的自己缺失了真正的教育;社会的畸形需求制造了一大片以拍电影为名的骗子:无论是所谓的导演布拉塞蒂,还是介绍他们去专业摄影师那里拍摄的埃博托,无论是专业摄影师、舞蹈来师、美发师,都成为了畸形社会的产物,他们从来不劝阻,不干涉,只要为了得到钱,几乎丧失了职业道德。而所谓的导演、所谓的工作人员,更是成为了骗子,他们以拍戏为名非法赚取父母的钱,莫名进入美达琳娜家里的那个陌生女人说,要教玛利亚如何表演,甚至说自己以前就是一个演员,“现在没戏演了。”而美达琳娜对她是谁都一无所知;埃博托和她拉近乎,说演员入围的名单自己掌握着,所以要进入其中必须那点钱来,“没有付出怎么有回报?”即使么美达琳娜知道这是一场骗局,但她还是一位只要用钱就可以让女儿成功;而导演布拉塞蒂最后在决定谁能入围时,竟狮子大开口要200万里拉——或者正是这个巨额的价格,才使得美达琳娜开始醒悟,当她看到剧场混乱的局面,才知道从自始至终这一活动本身就是一混乱——剧场的混乱,正是社会的混乱,价值观的混乱。
但是,美达琳娜能一步步被诱骗,一步步陷入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自我的缺失——作为母亲的缺失。她让女儿去参加电影选角比赛,内心的一个愿望不是为了女儿的成功,而是为了弥补自己曾经的缺憾。当那个据说曾经演过戏的妇人来到家里,似乎触动了美达琳娜埋没依旧的情绪:“演戏到底是什么?”她提出的这个问题激活了她自己的演戏情结,面对着镜子,她看着镜中的自己,然后喃喃自语:“这是不是演戏?”镜子外的自己是现实中的自己,镜子里的自己是戏剧中的自己,它们互为镜像,美达琳娜便找到了那个影子:“如果我当初愿意的话……”言下之意就是我应该走上演戏这条路,所以她从女儿身上找到了这种弥补缺憾的机会,她在女儿面前一直强调的一句话是:“我们会成功的。”——不是女儿一个人会成功,而是“我们”会成功,也就是将女儿和自己绑缚在一起,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也变成了一种互为镜像的关系:女儿演戏就是我在演戏,女儿成功就是我在成功。
不是对于自己表演能力的自信,也不是为了失去曾经机会的遗憾,实际上在本质上:美达琳娜想要摆脱这样的生活。每天为别人打针,家庭收入微薄,这是底层的生活,在美达琳娜看来便是失败,所以在她看来演戏是一条捷径,而且女儿如此可爱,如此多才多艺——正是这种镜像般的存在,美达琳娜不是为了让女儿在学习中达到所谓的成功,而是急于求成,别人训练了三年的舞蹈,她几天就想学会;拍摄照片、订购舞蹈裙都是为了从最简单最有效的层面,让女儿看见成功的希望,而这反而越来越成为失败的现实:女儿的哭泣,丈夫的大骂,自我的沉迷,成为一种走向悲剧的结局。
但是,骗局和金钱还是唤醒了她,丈夫和女儿还是让她返回,只有真正看见了需要成长的女儿、需要爱的丈夫,需要温暖的家,美达琳娜最后那一句“你这个疯子”,才能让自己从“疯子”迷局里走出来,才能在一种母亲的成长仪式中完成自我命名。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