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2-21《且介亭杂文二集》:带着枷锁的跳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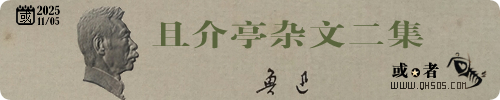
文学的修养,决不能使人变成木石,所以文人还是人,既然还是人,他心里就仍然有是非,有爱憎;但又因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热烈。
——《再论“文人相轻”》
是非分明是不是如口号家因反对“文人相轻”而投一切文人以轻蔑?爱憎热烈是不是像庄子所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文人不是木石,当然有感受感觉和感想,观点不同,想法不一,甚至文风有别,这是文人会遇到的常态,但是如果把是非分明和爱憎热烈度看成是“文人相轻”的理由,不仅是拉大了“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距离,甚而至于就成了因反对相轻而投以一切“文人”以轻蔑的口号家,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中反而加重了“相轻”的恶弊。
在“文人无行”的批评之后,是“京派和海派”之争,而现在当“文人相轻”变成一句口号,在鲁迅看来,对于文坛来说,当然是另一种更大的危险。“文人相轻”来源于曹丕在《文选》中的一句话:“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只是因为局限于自己最擅长的文体,只限于文学交流,在鲁迅看来是“仅限于制作的范围”,但是却演变成了文人间的攻击、诬赖、造谣:施蛰存说“他自己也是这样的啊”,魏金枝说“他的亲戚也和我一样了呀”,都超出了“文非一体”的讨论范围,“是混淆黑白,真理虽然大哭,倒增加了文坛的黑暗的。”这一种黑暗似乎来源于《庄子》的那句话:“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他们就是把这句话当做是“危急之际的护身符”,庄子的境界是超脱、达观,但是在文人那里却成了反击的工具,所以“喜欢引用这种格言的人,那精神的相距之远,更甚于叭儿之与老聃”。
文人相轻,让“真理哭了”,而真理到底是什么?一方面鲁迅认为批评家或者文人批评需要“各各‘指其所短,扬其所长’固可,即‘掩其所短,称其所长’亦无不可”,一面有所长,那时一面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另一方面也不能为“文人相轻”所“吓昏”,一律变成了拱手低眉,不敢说也不屑说,于是文人都成了充风流的寡妇,装古雅的恶少,销淫书的瘪三,“这是怎样的批评家或文人呢?”在这样的情况下,鲁迅认为“他先就非‘轻’不可!”要在所长中明确是非和好恶,也要在非“轻”不可中不一团和气——当鲁迅指明了挽救真理的方法,“文人相轻”似乎在现实意义中并非如此简单可以避免与解决。在《“文人相轻”》一文之后,鲁迅又作了《再论“文人相轻”》《三论“文人相轻”》,一直到《七论“文人相轻”》,用这七篇系列文章揭示“文人相轻”的本质,寻找不让“真理哭了”的方法,更坚定了自己作为文人的坚决态度。
《再论“文人相轻”》指出“今年”的文人相轻的一个新特点,就是:“不但是混淆黑白的口号,掩护着文坛的昏暗,也在给有一些人‘挂着羊头卖狗肉’的。”文坛上的纠纷早就超出了文笔的短长,鲁迅强调,文人不应该傲慢,也不应该随和,而是表达自己的态度:“只是唱着所是,颂着所爱,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为此,魏金枝在《芒种》上发表了《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一文,对鲁迅开始了论战,魏金枝认为,是非难定,爱憎为难,“譬如有一种人,……在他自己的心目之中,已先无是非之分。……于是其所谓‘是’,不免似是而实非了。”但“至于非中之是,它的是处,正胜过于似是之非,因为其犹讲交友之道,而无门阀之分”的。是非之间似乎也是一个文人自己的标准问题,似乎也是一种派别的区分,所以,“天下的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鲁迅认为这只是一种“假揩眼泪”的做派,最后掉进的是“无是非”的深坑里,“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都说成了“朋友”,鲁迅在《三论“文人相轻”》中批评说:“论‘文人相轻’竟会到这地步,这真是叫作到了末路!”但是鲁迅似乎觉得论争还未结束,在《四论“文人相轻”》中又针对魏金枝以为现在“往往有些具着两张面孔的人”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在魏金枝看来,不同的人在是非问题上最后的方法是“自己另找讲交道的朋友”——鲁迅入碗内,这种所拥护的文人想起,并不是因为“文”,而是为了“交道”,而朋友的交道又分成几种,对于文坛来说也是危险,“已成年的作家们所占领的文坛上,当然不至于有这么彰明较著的可笑事,但地方究竟是上海,一面大叫朋友,一面却要他悄悄的纳钱五块,买得‘自己的园地’,才有发表作品的权利的‘交道’,可也不见得就不会出现的。”
此后鲁迅关于“文人相轻”的文章走向了某种陈词总结中,在《五论“文人相轻”》中他指出了“轻”之术:一种是自卑,拖出敌人一起做“畜生”,一种是“埋伏之法”,“是甲乙两人的作品,思想和技术,分明不同,甚而至于相反的,某乙却偏要设法表明,说惟独自己的作品乃是某甲的嫡派”;第三种是补救之法,“是某乙的缺点倘被某甲所指摘,他就说这些事情正是某甲所具备,而且自己也正从某甲那里学了来的。”《六论“文人相轻”》则指出了文坛上的“两卖”:卖老和卖俏,但文坛不是养老堂,当然也不是妓院;《七论“文人相轻”》则从炯之的《谈谈上海的刊物》一文的观点出发,指出了“两伤”的后果,而这种斗争带来的“两伤”,在鲁迅看来是可怜的时代的产物,“凡有可怜的作品,正是代表了可怜的时代。”而唯一要从可怜的时代不被“两伤”,就需要热烈的憎,“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
“他的剑是绝望的疯狂,而每一刺是各样的谋杀!”爱成憎,憎而谋杀,这是文人该有的态度,也是对于“文人相轻”这种可怜时代的鄙俗最后的行动。鲁迅反对文人相轻,在“七论”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是扬其了所长,也是“非轻不可”的决然。在《“题未定”草》系列文章中,鲁迅就是实践着自己的观点,就是在能杀能憎中能爱能文。翻译《死魂灵》,鲁迅几乎躲在了书房里,对于译文他的疑问是:“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在翻译问题上,主张“硬译”的鲁迅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但是文章还没翻译,就被林语堂称为“西崽”——“西崽”,是旧时西洋人对雇佣的中国男仆的蔑称,在林语堂的文章中,文坛上的“西崽”是“既赶时髦,生怕落伍,于是标新立异,竞角摩登”的人,鲁迅认为西崽的可厌不在于职业,而在于“西崽相”,“这‘相’,是觉得洋人势力,高于群华人,自己懂洋话,近洋人,所以也高于群华人;但自己又系出黄帝,有古文明,深通华情,胜洋鬼子,所以也胜于势力高于群华人的洋人,因此也更胜于还在洋人之下的群华人。”这其实间接地和林语堂进行了论战,也对于如何面向外国文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世界文学史,是用了文学的眼睛看,而不用势利眼睛看的,所以文学无须用金钱和枪炮作掩护”。
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张露薇在《略论中国文坛》中注明了一句话:“偷懒,奴性,而忘掉了艺术”,他所针对的是“硬译”问题,更是针对从日本复译苏联文学作品的做法,“从苏联到中国是很近的,可是为什么就非经过日本人的手不可?我们在日本人的群中并没有发现几个真正了解苏联文学的新精神的人,为什么偏从浅薄的日本知识阶级中去寻我们的食粮?这真是一件可耻的事实。”无疑这些话也是在抨击鲁迅,甚至在张露薇看来,鲁迅参加高尔基四十年创作庆祝会是完全不合适的,“中国也有鲁迅,丁玲一般人发了庆祝的电文,……然而那一群签名者中有几个读过高尔基的十分之一的作品?”鲁迅回击说:“就是在文艺上,我们中国也的确太落后。法国有纪律和巴尔扎克,苏联有高尔基,我们没有;日本叫喊起来了,我们才跟着叫喊,这也许真是‘追随’而且‘永远’,也就是‘奴隶性’,而且是‘最“意识正确”’的东西”,最可怕的倒是如林语堂所说并不叫喊的人,而对于高尔基庆祝会,鲁迅“招供”说自己读得很少,甚至十分之一的作品究竟是几本也不知道,但是发电文或者不发电文都不要紧,重要的也是“追随”的做法,而张露薇这样说在鲁迅看来只不过是拿着鞭子抽打奴隶的知识阶级,而自己只不过是奴才,“那一个和一群,有这么相近,却又有这么不同,这一张纸真隔得利害:分清了奴隶和奴才。”
奴隶和奴才只隔着一张纸,鲁迅针对林语堂、张露薇等人的抨击,也进行了反唇相讥,在他看来,这似乎都犯了“文人相轻”的罪,罪状便是“吹毛求疵”,他也说自己犯了这样的罪,当然鲁迅在这里只不过是施用了讽喻,区别攻击和讽刺,鲁迅自有观点,在《论讽刺》中他指出,“写实,现在的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非写实的讽刺就是造谣和污蔑,就是文人相轻的谩骂,而在答文学社问的《什么是“讽刺”》中,鲁迅更为详细地谈及了讽刺的方法和意义,他认为,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不一定有实事,但必须有事情,不是捏造,不是污蔑,不是揭发隐私,也不是记那些骇人听闻的奇闻和怪现状,“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
对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的事情进行揭露,这样的讽刺作者会被被讽刺者所憎恨,但鲁迅认为讽刺作者一定是善意的,“他的讽刺,在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如果没有善意没有热情,讽刺最后也变成了“冷嘲”。关于什么是讽刺,像是鲁迅对于《文人相轻》的一种观点补充,而其实,鲁迅所说的善意、热情,以及真实,也意味着自己慢慢退出了论争的舆论场,这似乎是鲁迅的一次转变,他在《序言》中说:“我有时决不想在言论界求得胜利,因为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报告着大不吉利事,我的言中,是大家会有不幸的。”所以为了内心的冷静和外力的迫压,“我几乎不谈国事了”,写了几篇被禁止,正当的舆论就像国土一样“即于沦亡”,所以在几乎不谈国事上,鲁迅只是在《论“人言可畏”》中,针对阮玲玉自杀这一社会事件发表了看法,而他所针对的也并非是中国人的国民性,并非政府的漠视,而是在“她们的死”中反思了新闻记者的道德操守,“‘有闻必录’或‘并无能力’的话,都不是向上的负责的记者所该采用的口头禅,因为在实际上,并不如此,——它是有选择的,有作用的。”
不预备自杀,也不会轻而易举自杀的鲁迅其实也是对于当下的“舆论”提出了批评,而除了这一篇稍微涉及“国事”之论的文章之外,鲁迅更多的精力则放在了文学、文坛和文人身上,这或许是他对于文学本体的回归:他在给叶紫《丰收》做的序中说:“这就是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他在为萧红《生死场》做的序中说:“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他在《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中对于两个时代的文学样式进行了比较,六朝小说写的是人事,“文笔是简洁的;材料是笑柄,谈资;但好像很排斥虚构”,而唐代传奇则走向了另一条路,“神仙人鬼妖物,都可以随便驱使;文笔是精细,曲折的,至于被崇尚简古者所诟病;所叙的事,也大抵具有首尾和波澜,不止一点断片的谈柄;而且作者往往故意显示着这事迹的虚构,以见他想象的才能了。”甚至鲁迅还谈到了创作漫画的要义,“漫画的第一件紧要事是诚实,要确切的显示了事件或人物的姿态,也就是精神。”谈到了中国木刻出现了“境界”,“它所表现的是艺术学徒的热诚,因此也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
论述文学的本体和主体,鲁迅的转向是一种回归,在《不应该那么写》中对于有志于创作的青年提出了不应该去看所谓“小说作法”,“小说法程”之类的书,关键是要积累文学的遗产,创造文学的环境,“读书人家的子弟熟悉笔墨,木匠的孩子会玩斧凿,兵家儿早识刀枪,没有这样的环境和遗产,是中国的文学青年的先天的不幸。”环境和遗产是中国文学青年所缺少的,但是在中国新文学走过来的这些年里,中国青年所需要的环境和遗产正在形成,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全面回顾了从一九一七年新文学运动开始到一九二六年中国小说的创作情况:从《新青年》提倡“文学改良”,到后来提出的“文学革命”;从鲁迅提到自己一九一八年创作短篇小说开始了“文学革命”,到《新潮》《现代评论》《莽原》等刊物的出现;从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创造社“为文学的文学”,到浅草社、沉钟社、莽原社涌现的小说创作群体……鲁迅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所做的序似乎在写史中保持了某种客观,无论是对自己的评价,还是对曾经有过论战的创造社、《现代评论》、凌叔华的评价,鲁迅过滤了更多的个人因素,“文学团体不是豆荚,包含在里面的,始终都是豆。大约集成时本已各个不同,后来更各有种种的变化。”
但是,在说到莽原社的“内部冲突”,说到狂飙社的“狂飙运动”,说到高长虹,则表达了是非分明、爱憎热烈的观点,“所谓‘狂飙运动’,那草案其实是早藏在长虹的衣袋里面的,常要乘机而出,先就印过几期周刊;那《宣言》,又曾在一九二五年三月间的《京报副刊》上发表,但尚未以‘超人’自命,还带着并不自满的声音——‘黑沉沉的暗夜,一切都熟睡了,死一般的,没有一点声音,一件动作,阒寂无聊的长夜呵!’”这是尼采作品中的句子,当变成“狂飙运动”在沉沉黑夜中发出的声音,“正是狂飙社的进军的鼓角。”但是这一种鼓角,对于鲁迅来说,只是在一九二六年曾经响起,而到了不谈论国事的一九三五年,又归于了沉默,甚至在鲁迅那里变成寂灭,“书店是不能不陆续印行新书和杂志的,所以还是永远有陆续被扣留,查禁,甚而至于封门的危险。”这是鲁迅在《后记》中提到的现实,这是他重新谈论的国事:
九月二十五日的《中华日报》云——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会工作紧张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自在沪成立以来、迄今四阅月、审查各种杂志书籍、共计有五百余种之多、平均每日每一工作人员审查字、在十万以上、审查手续、异常迅速、虽洋洋巨著、至多不过二天、故出版界咸认为有意想不到之快、予以便利不少、至该会审查标准、如非对党对政府绝对显明不利之文字、请其删改外、余均一秉大公、无私毫偏袒、故数月来相安无事、过去出版界、因无审查机关、往往出书以后、受到扣留或查禁之事、自审查会成立后、此种事件、已不再发生矣、闻中央方面、以该会工作成绩优良、而出版界又甚需要此种组织、有增加内部工作人员计划、以便利审查工作云、如此善政,行了还不到一年,不料竟出了《新生》的《闲话皇帝》事件。
以审查为名创造“相安无事”的环境,把审查会成立当成是“善政”,这便是鲁迅所面对另一个“黑沉沉的暗夜”,在几乎不谈国事的沉默中,在文人相轻的环境里,在扣留查禁成为常态的社会里,不是“第三种人”的鲁迅,不为艺术而艺术的鲁迅,不写帮闲文学的鲁迅,却在沉寂中发出了一点声音做出了一件动作,“凡是发表的,自然是含胡的居多。这是带着枷锁的跳舞,当然只足发笑的。”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0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