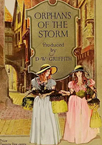2024-02-21《暴风雨中的孤儿》:关于命运的三重构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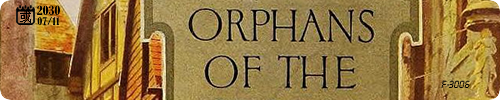
大卫·格里菲斯1921年的“最后一分钟营救”表现得更为成熟,也更为扣人心弦:贵族骑士沃德雷被法国大革命的“法庭”宣判死刑,孤儿亨丽埃特因为“窝藏贵族”也被判死刑,两个人被推上了囚车;丹东在法庭上发表了“伟大的演讲”,高大的他怒斥独裁者,要把权力还给人民;囚车上的亨丽埃特和盲人姐妹露易丝深情告别,囚车向三公里外的断头台而去;丹东率人骑马向着断头台而去,一路疾驰,“记恨的雅克”却命人将大门关闭;亨丽埃特的行刑时间已到,她被押解着走上了断头台,头也被安放在锋利的铡刀之下,丹东冲破了刑场的大门,振臂高呼中闯入了断头台——在亨丽埃特即将被断头的千钧一发之极,丹东冲上了断头台,解救出了亨丽埃特,将她抱起,并让皮埃尔和沃德雷获得了自由……
依然是平行剪辑,依然是交错叙事,甚至依然是快马疾驰赢取解救的时机,当然,最后也依然是解救成功,1921年的“最后一分钟营救”惊险性与紧张感,甚至是格里菲斯影像叙事的最后一次高潮,因为断头台指向的死亡和快马崩腾指向的生存,在时间的较量中呈现出窒息的一刻。而丹东所代表的英雄式人物和亨丽埃特的“孤儿”身份,在这部电影中却成为关于命运的两个维度,在个体意义上,丹东的解救是一种报恩行为,亨丽埃特被卷入大革命,则是个人命运的沉浮写照;而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中,不论是丹东作为“国家英雄”,还是亨丽埃特代表的贫民,在法国大革命中都维系着国家命运,在这场风起云涌的革命中,生与死超越了个体,成为国家出路与政权建设的一个命题。
这二重维度的命运构建,正是格里菲斯这部电影片名的所指,“暴风雨中的孤儿”,“孤儿”指的是亨丽埃特和露易丝姐妹的个体命运,但是这种个体命运又笼罩在国家生死存亡的“暴风雨”之中。格里菲斯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讲述姐妹的命运沉浮,不如说将姐妹的命运融合进国家命运的思考之中,以个例解读大革命的得失,以个体关照大革命的走向,这种结合的戏剧性是明显的,以小见大的叙事风格也是对革命的一种思考,而这个故事的起点就在“生命的旅程开始了”——露易丝和亨丽埃特成为了“姐妹”,一起在成长中成为了相互依靠的一家人,“本剧拉开了帷幕”。
他们在瘟疫夺走了父母之后成为了“孤儿”,而且因为被瘟疫感染,露易丝更是双目失明,失去父母和双目失明成为“孤儿”身份的标签。但是在“孤儿”的命运中,露易丝和亨丽埃特却要冲破命运的束缚,她们决定到巴黎来寻找医生,医治失明的疾病,而巴黎又成为“孤儿”命运新的困境,在这里她们人生地不熟,在这里她们没有地位和权利,甚至没有更多的钱,“孤儿”在法国大革命迁前夕的巴黎也成为了“穷人”的代表:在路上遇见的普拉尔列侯爵因为觊觎亨丽埃特的美貌,命令手下的拉拉弗勒实施抢劫计划,在一个黑夜将亨丽埃特劫持到自己的宴会上,而失明的露易丝被乞丐中的恶棍带走,成为赚钱的工具……“孤儿”陷入更大的困境,他们的命运也逐渐从个体走向了群体,并成为法国大革命“人民”的一部分。
| 导演: 大卫·格里菲斯 |
而其实,在巴黎之前,“孤儿”之所以成为孤儿,也并非是完全个体意义上的,露易丝是亨丽埃特的父亲在鹿特丹的阶梯上捡到的,露易丝的胸前挂着的项链上写有一张纸条,她是被遗弃的,她的过去成为了一个谜。而这个谜,格里菲斯并没有让观众去猜疑,在“本剧拉开了帷幕”之前,可以说是对露易丝真相的一次交代,她原是贵族的孩子,但是她的父亲在和贵族比剑时不幸身亡,无助的母亲只好让露易丝被人抱走,但是抱走的贵族没有履行诺言照顾她,反而遗弃了,幸好被亨丽埃特的父亲救起,当露易丝在农民家里长大,露易丝的母亲却变成了利纳雷斯伯爵夫人,“她的过往没有让爵士知道。”所以,不论是露易丝还是她的母亲,在隐藏起过去的时候,他们都成了命运里的“孤儿”,而这个造成“孤儿”的体系就是贵族体系:露易丝的父亲比剑,母亲另嫁他人,露易丝被遗弃,不正是反映了贵族的虚伪和道德的缺失?而在这种虚伪和缺失中,露易丝成了牺牲品,她跌落到了最底层,也失去了视力,这是她身上彻底“去贵族化”的标志,但是亨丽埃特的父母拯救了她,亨丽埃特将她视为亲姐妹,照顾她,前往巴黎救治她,甚至一生都要陪伴她,如果无法治好眼疾,亨丽埃特甚至自己不嫁人也要做她永远的“眼睛”,这又体现了穷人的仁慈和爱,它和那个贵族体系形成了完全不同的道德世界。
那么,当两个人来到巴黎,无情卷入巴黎贵族社会和革命潮流,更是让个体的命运成为国家命运的一个缩影。从贵族变成孤儿的露易丝,在巴黎成为恶棍赚钱的工具,她在街上乞讨,她吃不饱穿不暖,她被关在地下室里,这是命运凄惨的写照,更是最底层的代表。而亨丽埃特在被普拉尔列侯爵诱拐之后,一心想要寻找露易丝的她又被“记恨的雅克”盯上,又被卑鄙的罗伯斯庇尔发现,可以说她是被动卷入这场革命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她遇到了骑士沃德雷,沃德雷的爱感染了她,她也爱上了沃德雷;她认识了丹东,丹东在一次和保皇党人的冲突中受伤,是亨丽埃特救下了他……无论是“记恨的雅克”、罗伯斯庇尔等恶的代表,还是沃德雷骑士、丹东等人,亨丽埃特被动卷入到巴黎的“风雨”中,也成为法国大革命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也由此将个体的命运深深刻进了革命所指向的国家命运中:个体命运中遭遇的欺骗、暴力与仁慈、爱,成为革命的两面,而这场由人民开始却被贵族窃取了成果的革命,也在这两面性中呈现出了它的复杂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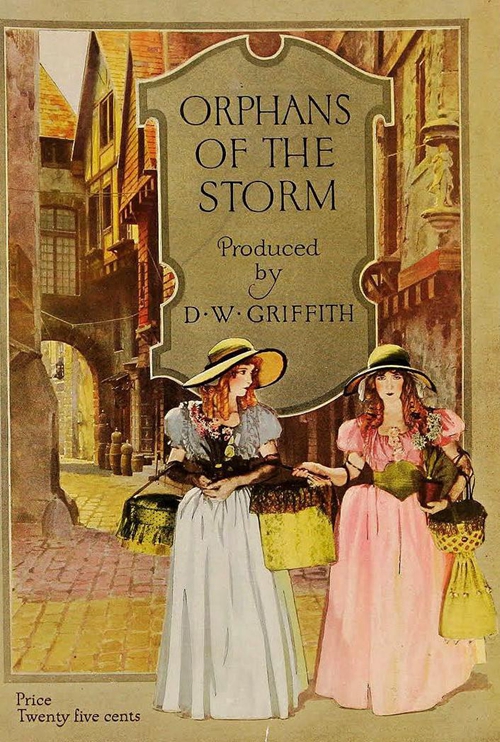
《暴风雨中的孤儿》电影海报
但是格里菲斯对于这场革命的立场是明确的,“记恨的雅克”从一个社会底层的存在,到革命中成为法庭的法官和刽子手,“记恨”贵族其实就是觊觎权力;猥琐的罗伯斯庇尔一直保持着“等待”的姿态,当革命爆发他窃取成果,成了独裁者,国王路易十六在革命中被送上了断头台,而罗伯斯庇尔建立的政权依然在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中成为另一个独裁者;同样,沃德雷和丹东则成为格里菲斯镜头下的真正革命者和英雄:骑士充满了爱,他是唯一在普拉尔列侯爵的宴会上挺身而出帮助亨丽埃特的男人,他敢于反抗叔叔利纳雷斯伯爵让他和公主订婚的决定,因为那只不过是伯爵巩固自己权力的计划,更重要的是,他爱上了善良、美丽的亨丽埃特,他们的爱情和地位无关,这是一种纯真的爱,贵族对于他来说,这不过是一个虚设的身份,所以在法庭上他因为贵族身份被控诉,“我的确是贵族,但我没有和人民为敌……”而丹东呢,更是反对独裁的真正革命者,他把人民放在第一位,他领导人民推翻封建统治,他更是号召人民打倒独裁统治,所以沃德雷和丹东身上体现的是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公平、爱和仁慈,而这也正是无数的“孤儿”要成为拥有权力的“人民”,所需要的革命。
由此,两个孤儿之间的爱和整个社会所呼唤的爱结合在一起,将个体命运和国家命运融合在一起,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风格让整部电影具有了更深的主题,而格里菲斯的画面语言也充满了隐喻性:亨丽埃特和露易丝最开始对调的命运是对社会权力结构的一种讽刺,亨丽埃特和露易丝隔着阳台而不能在一起,眼睁睁看着彼此分离,撕心裂肺中是对恶的力量的控诉;在审判时亨丽埃特希望法庭不要大声宣布自己的罪,因为她担心“妹妹看不到,听得到”,而在被押解上囚车时,姐妹脸贴着脸,是爱的一次升华……两个人之间传递着爱,也被无情地分离,也正是“人民”具体而微的表现,而这种“人民”的遭遇指向了国家命运的出路:只有爱和仁慈的社会才能让人民成为主人。但是“人民”却在大革命中成为了暴徒,他们狂欢,他们记恨,他们是断头台的刽子手,究其原因,是因为“人民”是被利用的人民,是拥有私心和泯灭了爱的“人民”,所以这些“人民”不是真正的人民,不是革命的真正主体。
但是“最后一分钟营救”还是让革命演绎着正义与爱,亨丽埃特从断头台上被解救下来,沃德雷获得了自由,露易丝的眼疾终于被治好了,而沃纳雷斯伯爵夫人也终于认了自己的亲生女人,当然亨丽埃特和沃德雷也最终在一起了。这是幸福的大团圆,这个大团圆的结局是对个体命运“最后一分钟营救”的结果,更是让这场革命回归秩序重建正义的象征,因为罗伯斯庇尔被送上了断头台,独裁政府被推翻。从个体命运到国家命运,当然只是命运的两个维度,格里菲斯借用法国大革命,更是在强调第三种命运,那就是人类命运。从电影中的故事拉开帷幕之前,电影打出的字幕就阐述了格里菲斯的目的,我们既不要封建帝制下的国家,也不需要罗伯斯庇尔建立的无政府状态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法国大革命“正当地”推翻了一个“恶政府”,却同样建立了一个独裁政权,而真正的出路就是建立“善”的政府,而这正是“我们”美国的目标——从法国大革命到美国“革命”,格里菲斯的目的很明确,所以在电影中美国大使会送给法拉叶侯爵一个礼物,以表达建立民主政府的想法,所以“麻脸雷霆”丹东才会被格里菲斯注释为“法国的阿伯拉罕·林肯”。
从法国到美国,从革命到民主,从丹东到林肯,格里菲斯已经明确表达了电影的主旨,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种超越国界的人类共同理想,不正是关于命运的更高层级:从个体命运到国家命运,从个人到人民,最终一切的命运都是仁慈、爱、正义和自由,它们属于的是整个人类。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