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8-18《镜子》:另一面,也不是你的领地

青苔在生长,木头在腐烂,石头不说话,水塘泛着光,在灌木丛之外,生长与腐烂、沉默和反光组成了静与动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不体现着矛盾,它走向更远的远方:在杂草丛生和断垣残壁中,玛丽娅端着脸盆,和儿子阿廖沙站在那里,当他们回望树丛后面的房子,静观变成了行动;玛丽娅带着阿廖沙和玛丽娜穿过草丛,这时候挂在牛车上的被单滑落了下来;三个人继续前行,当他们渐行渐远,望着他们背影的是母亲,她站在十字形状的电线杆旁,眼中是泪,却又带着笑容;三个人已经渐渐隐没在远处,母亲还是站在那里,云杉的纸条遮挡了离去的他们,音乐声渐渐消失,如剪影一般的母亲变成了最后的影像。
玛丽娅和阿廖沙、玛丽娜的母女三人看见的是杂草,是残垣,是枯井,当他们走向远方时,他们成为了被看见的对象,而母亲变成了观者——观者成为被观者,这是看见的双重性,它们以相同的方向保持了看见的单一性。但是这种看见的单一性甚至最后画面的抒情意义,却在突兀而至的“跳帧”中被破坏了:在母亲静静站在那里成为最后的剪影时,画面突然跳到了一处小酒馆,三个男人围着桌子或者拿起酒杯,或者低头不语,两个男人在问其中一个“进去干什么”,而其中一个又问另一个:“你是作家?”作家叹息说:“我的灵感佣用尽了。”此时后面掀开门帘的男人出现,这时,三个男人中的一个对后面的男人说:“如果我回不来,就告诉我的妻子。”
小酒馆里的四个男人,在一场并无所指的对话中,为什么母亲最后的守望会变成关于进去和回来的讨论?以为电影进入到了另一个场景中,而且其中有着可联系的线索:那个说自己灵感用尽的作家不正是电影中和母亲在田野中偶遇的男人?演员安纳托利·索洛尼岑深邃的眼睛说明了这一切,在母亲目送结束之后转入作家告别灵感枯竭状态而“进入”,似乎也是一种合理:在他遇见坐在横着的树枝上抽烟的母亲之后,两个人产生了若即若离的关系,男人问母亲:“这是去托姆西诺的路吗?”母亲告诉她:“你不应该在灌木丛哪儿就拐弯。”拐弯意味着不是去托姆西诺的路,但是男人却笑了,他甚至慢慢靠近了母亲,他说母亲一定没有结婚否则怎么不戴戒指;他要了一支烟,说自己是一个医生,因为忘了钥匙,又问她有没有钉子;他坐在母亲坐过的树枝上却不小心掉了下来,然后大笑地说:“我发现了奇怪的东西:树从来不匆忙,不像我们,我们总是行色匆匆。”他接着说:“有空到托姆西诺来,我们那儿经常很热闹。”之后他站起来,开始离开母亲。
母亲和男人发生了偶遇,但是偶遇中透露出的是一种暧昧,男人提到的结婚戒指,匆忙的人,和远方的托姆西诺,似乎都是一种诱惑,是诱惑抽烟的母亲和他一起离开,当男人慢慢走远时,他转过身回望母亲,此时原野上吹起了一阵风;他再次前行,再次转身,风再次吹起……在如此反复之后,他终于消失在母亲的视线中。诱惑者必定是闯入者,这就是一个进入和回去的故事,而三个男人讨论的也正是这个问题,是不是那个自称作家的男人就是这个去往托姆西诺的医生?演员安纳托利·索洛尼岑串联起了两者。当医生在风中最终离开,他再也没有出现在后面的故事里,故事留下了太多的想象:当男人拐进灌木丛的这条路而遇见母亲,像是人生的一次不经意的转弯,而这样的转弯却是一个关于父亲消失的寓言:“这条路是从车站经过伊格纳契耶沃的小路,每年夏天,在离我们战前住过的村子一公里处,拐了个弯儿,弯弯曲曲地经过稠密的橡树林,一直伸向远方,通往托姆西诺。”在旁白中,这条路通向了两个方向,两个方向交代了两个男人:“如果他从灌木丛那边向房子走来,那他就是父亲,如果不,那就不是父亲。那就是说,他再也不会来了。”
从灌木丛向房子这边走来的是父亲,否则就不是父亲,“他再也不会回来了。”当父亲成为不回来的失踪者,男人在某种意义上取代了他的位置,甚至只是在偶遇的那一刻取代了他,而即使男人在不断起风的原野上回望最后离开,对于母亲来说,这也构成了她之后可能的回忆,在身为军人的父亲再也没有回来,母亲的内心似乎也为这个偶遇的男人保留了一个位置。而到了我——既是故事的见证者、旁观者,也是自述者的“作者”,这个和母亲有关的隐秘故事又呈现出另一个暧昧的版本,“我”在镜头之外,问妻子玛丽娅的是“他”:“听说他是在乌克兰,是个作家,你该不会想嫁给他吧?”两个人已经离婚,正在讨论关于儿子伊格纳特是不是应该去军事学校,而我对“他”做出了评价:“到现在什么也没写成,谁也不知道他,大慨已经四十岁了吧?这就是说,是个无能之辈。”
玛丽娅和我讨论另一个男人,而且是玛丽娅可能嫁的男人,这一种暧昧关系更直接和三个男人讨论时作家说自己灵感已经枯竭取得了联系,于是一条隐秘的线索从母亲的邂逅到前妻的婚姻被建构起来,而与三个男人关于进去和回来的对话形成了呼应,甚至成为解读母亲和父亲、我和玛丽娅关系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但是这只是一种误读,甚至变成了想象:因为突兀出现的三个人在酒馆的那个场景其实是另一部电影,因为在同一个文件夹中,当《镜子》播放结束之后便跳到了另一部电影当初看过的那个时间点——这一部电影是塔可夫斯基在《镜子》完成四年之后拍摄的《潜行者》。
一个谜团被解开,1975年的《镜子》和1979年的《潜行者》,是时间两端的独立存在,其中的暧昧、怀疑终究没有成为下一个故事的开始,仅仅是演员安纳托利·索洛尼岑的“串场”,仅仅是塔可夫斯基一致的诗意,或者仅仅是其中透露的“作家”和医生的身份,为什么可以建立这样一个合理化的关系?这是在观者层面上的建构,看见就像站在远处的母亲一样,让原先的观者变成了被看见的对象,而《镜子》是不是也在现实与想象、进去和回来、回忆和真实中构建了双重的视觉维度?一部电影和另一部电影,一条线索和另一条线索,似乎并不是这一边和那一边的隔阂状态,即使如那个在灌木丛中遇见的医生所言:“这全都因为,我们和大自然相互不信任。都是因为一种不信任,匆忙,或者……因为没有时间思考。”不信任也并非可以将这一边和那一边完全隔离开来,那一些风和记忆带来的是含混。
| 导演: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
但是,塔可夫斯基在《镜子》中的确想要分离出了这一边和那一边的不同状态,这就是镜子作为物的存在具有的属性,它立在那里,当人走近,在看见自己、看见可以被照见的镜像时,总是希望在镜子后面找到东西,这是从镜像“进入”的状态。对于现实来说,这面镜子背后所要找寻的东西便是过去,便是记忆,便是历史。父亲没有从灌木丛那边向房子走来,父亲再也不会回来了,所以我要进入和父亲有关的那段记忆和历史:那里是房子里燃起的大火,狗在吠叫,扑救者站在打火前手足无措;那时孩子们读着达芬奇的画,回来的父亲想把伊格纳特带走;那时母亲和他离婚了,看着伊格纳特一天天长大,母亲的担忧是:“伊格纳特越来越像你了,我有些害怕。”那时的玛丽娅问我,“你和母亲是怎样一种关系?”她自问自答“她希望你变成婴儿。”父亲当了兵,父亲回来过,父亲又离开了,当父亲再也没有从灌木丛那边走向房子,父亲变成了缺席的人。
历史和记忆是不是也变成了缺席?从个体意义上来说,只剩下了坐在树枝上抽烟的母亲,手指没有带戒指的母亲,和医生邂逅的母亲,以及想让我变成婴儿的母亲——也许我成为一种投影,母亲才不会害怕,而其实母亲从来都生活在害怕中。黑白影像中,急匆匆坐车又在大雨中赶往印刷厂的母亲就生活在害怕中,因为报纸上的一个字可能写错了,她全身淋湿的她找到了那张大样,仔细校对才发现并没有写错,于是那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这是一个可能拼错的单词带来的害怕,正像印刷厂里的那个男同事所说:“有人负责做事,有人负责害怕。”害怕在那个年代成为了和做事一样的“工作”,它是常态,而这种常态构成的历史是隔阂,更是对立:母亲和叶丽扎维塔之间发生了矛盾,起先叶丽扎维塔在安慰母亲,并递给她梳子,但是之后她说母亲像玛丽娅,就是大尉列皮亚法舍的妹妹季莫菲耶夫娜,母亲像她是因为在叶丽扎维塔看来,她总是在父亲面前命令他,“你的整个生活就是‘给我提水来”,实在佩服你丈夫的忍耐力。”母亲和叶丽扎维塔发生了争吵,但是当争吵僵持的时候,母亲想要去洗澡,脱光了衣服一个人在洗澡间,水突然就停了,于是她自己笑了起来,而叶丽扎维塔在母亲离开之后,感慨道:“尘世间的日子已经过去半辈子,我却在阴暗的森林里迷了路……”
两个女人的争吵,似乎涉及的是命令,“给我提水来”在叶丽扎维塔看来,似乎远离了夫妻之间关系的和谐,但是母亲却在自己洗澡时遭遇了停水,“给我提水来”的命令变成了湿淋淋的生活;而叶丽扎维塔攻击母亲似乎成为了废除命令的胜利者,但是她的感慨更触及颓废的人生,迷路的何止是她?给我提水来而遭遇停水变成湿漉漉的现实,是不是也是一种迷路?从家里奔忙而来只为一个字是不是写错了,是不是也是一种迷路?迷路而找不到方向,就是因为害怕,害怕无处不在。那个在训练场里练习射击的马尔科夫是不是也是一个害怕者?当向后转变成了360度的转身,原地回来就是在解构教练的命令,而马尔科夫认为向后转就应该是这样的;而当教练让他把父母找来时,马尔科夫说自己的父母都死了;之后的训练中,教练让大家扔手榴弹,马尔科夫却扔出了一个真实的手榴弹,教练为了救其他的孩子将手榴弹压在了身下,这是生死攸关的时刻,所有人都笼罩自害怕之中,但是一片寂静之后,炸弹没有爆炸,马尔科夫笑着说:“这是一个哑弹。”
害怕无处不在,这是父母亲缺席构筑的历史,或者在尘世的日子中迷路,或者在命令的解构中湿身,而唯一可以终止害怕的就是像手榴弹一样是一个“哑弹”——这是一种沉默,这是一种失语,不管是主动的沉默还是被动的失语,都构成了镜子后面无声的记忆。一个叫扎里伊·尤里的技校学生患有严重的口吃,医生对他进行治疗时,让他把所有的力量都转移到手指上,这种力量当然包括“紧张感”,当手指张开放在后脑勺上,当用力往后拉,当手指紧绷,力量的传递消解了压迫感,于是,医生说:“现在我取消这种状态,你就开始说话,只是要响亮,清晰,自然,轻松,不要害怕自己的嗓音,不要害怕自己的说话能力。”在“一,二,三”中,扎里伊·尤里开始说话,而且响亮地、清晰地说了一句:“我能够说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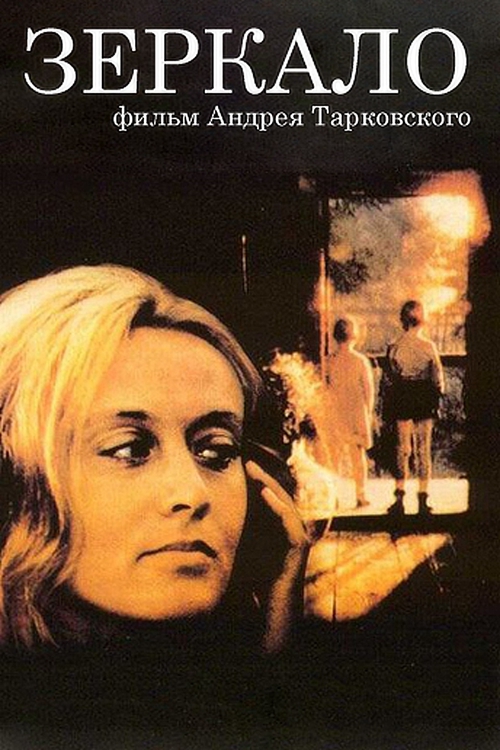
《镜子》电影海报
生理上的不能说话,通过力量的转移可以恢复言说的能力,这是对紧张的消解,但是在精神意义上,无法言说和失声是不是可以治疗?父亲有严重的咽喉炎,当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没有说话,一只鸟在他怀里想要死去了,但是画外音是父亲吟诵自己的诗歌:“心灵不能脱离躯壳,/犹如躯体要有衣服遮挡。/没有意愿,没有行动,/没有构思,也没有字行。/一个没有谜底的谜语:/谁将返回,翩翩起舞,/在那无人欢跃的广场上?/于是,另一个灵魂,在我的梦中,/穿着另一身衣裳。/它闪亮着,徘徊着。”鸟活了过来飞走了,只有灵魂脱离于身体,才能在没有谜底的谜语中,在没有字行的言说中活着,而这何尝不是另一种缺席?而在“我”的故事里,喉咙的生理疾病又如父亲那样发生,三天没有和谁说话的我甚至已经放弃了言说,“我甚至觉得,沉默是件好事。反正说话也不能传达一个人感觉到的一切。言语似乎是无力的。”
记忆的镜子后面是沉默,是失声,是疾病,而这种个体的记忆其实也和一个国家的历史有关,在历史的镜子后面,则是更多的沉默和失声:镜头里是横渡锡瓦什湾的军事行动,是布拉格广场的游行和镇压,是柏林街上的希特勒尸体,是莫斯科的战役,是原子弹爆炸……他们曾经是新闻,现在是史料,那一个个镜头里传递的是无声的恐惧, 是不是像口吃的尤里一样用身体力量的转移来恢复言说的能力?是不是如诗人一样在灵魂的飞升中找到语言?是不是像我一样以放弃苍白的言语方式保留记忆?一个国家的历史并不只是恐惧,还有隔离,西班牙邻居说着自己的母语,学着斗牛士的样子,当他们在异国他乡生活,他们如何言说?“我再也不回西班牙了。”母亲这样说。而西班牙人无法在俄罗斯这块土地上生活,那么苏联人自己是不是也是失声的存在?
“是俄罗斯,是她的一望无垠的疆土消化了蒙古人的入侵,使鞑靼人无法通过我们西部边境,把我们留在后方,他们退回自己的沙漠去了……”伊格纳特念着这一段文字,叙说着俄罗斯的独立历史,但是当赶走了鞑靼人,当基督教文明得以拯救,他们却依然生活在历史的隔阂中,“这种生活使我们仍然是基督徒,却把我们变得与基督世界格格不入……”甚至他们与欧洲疏远了,无法参与任何一个伟大事件的孤独就是一种沉默,所以选择的道路是“变换祖国”:“变换我的祖国,或者变换一段历史,除了我们祖先的历史,即上帝赐予我们的历史……”伊格纳特朗诵的是普希金1836年10月19日写给恰达耶夫的信,当这段历史造成的沉默以“变换祖国”的方式言说,是不是历史这面镜子照见了现实?它更在伊格纳特的在场中形成了缺席:他是在玛丽娅的要求下念出这段文字的,但是在念完而转身之后,屋子里没有了玛丽娅,空空如也的世界仿佛是一个梦,而历史是不是也是一个空洞的梦?
从个体到民族,镜子背后的历史和记忆是沉默的,是无声的,是迷失的,甚至是病态的。但是镜子之存在的真正意义是从镜像中发现镜子前面的东西,或者说从镜像里看见另一边,而这似乎就是《镜子》的真正意义,在那个从灌木丛离开的医生说出那句关于人与人不信任的话之后,父亲的诗歌形成了画外音:“你拉着我,穿过潮湿的丁香树丛,来到镜子的另一边,这是你的领地,当夜幕降临,我便受你回赐……”你和我可以进入的是“镜子的另一边”,这是属于自己的领地,那里有上帝,有温暖的手,有祝福,有晨曦,当然更有不再沉默的话语,它是建设的力量,“一座座城市,像海市蜃楼,/奇迹般地建起,又向两旁闪开去。/薄荷在我们脚下生长,/小鸟伴我们旅途,鱼儿跳跃在水面上……”
但是,镜子的另一边真的是自己的领地?“于是,嗓音变得浑厚有力。/你的话揭示了新的意义:沙皇。”言说不是为了建设新的自由国度,而是回到了历史,或者说,另一边的镜子其实就是无从逃脱的镜像,它在相似过程中将现实重新带入到历史之中:我和父亲一样患有咽炎,母亲其实就是玛丽娅同一个人,妻子担心我长得越来越像母亲……个体如此,国家和民族何尝不是如此?离婚和战争,缺失和死去,似乎从来没有停止,“天翻地覆就在眼前,命运,像手持剃刀的疯子,对我们紧追不放。”于是,镜子里的火焰还在燃烧,没有摩西;镜子里的屠杀还在发生,没有救赎;镜子里的沉默还在继续,没有词语——它没有可以逃逸的出口,它困在时间的内部,这一边和另一边,禁锢成为永远的苦难记忆。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0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