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8-28《善恶的彼岸》:一种未来哲学的序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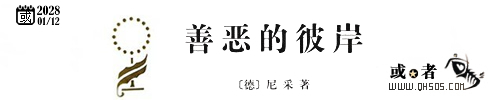
欢迎友人查拉图斯特拉,客人中的客人!现在世界欢笑,灰幕已经拉开,光明与幽暗的婚礼,已经到来……
——《终曲:自高山之上》
风和云在激荡着,鸟儿在展翅着,当一切升入更高的蔚蓝,是为了以下来的步伐进入其中,是为了庆祝一致的胜利:激荡而鸟瞰,展翅而俯冲,力量聚集在那里,只为等待着某一时刻的到来——到来的是友人查拉图斯特拉,是客人中的客人,是带着锤子的人,“朋友们,你们在哪里?来吧!时间到了!时间到了!”
尼采在欢呼“节日中的节日”,尼采在欢迎“客人中的客人”,尼采自己自高山之上下来,所有这一切注定是一个开始,那就是“一种未来哲学的序曲”。“它的基础,诸种想法,第一次以种种方式写下或草创的东西,乃属于我的过去:即那段诞生了‘查拉图斯特拉’的谜一样的时期:它们是同时发生的,从这一点上或许便可以得到一些有用的指点,去理解刚才提到的这部困难的作品。”这是1886年夏天到秋天的时候,尼采所写的关于《善恶的彼岸》所站位置的描述,同时发生是开始,也是结束,当查拉图斯特拉已经诞生,已经自高山之上下来,它就是宣告了“一种未来哲学的序曲”,但是在这个序曲已经吹响的时候,它指向的是另一种终曲:“愿人们是出于一个类似目的而使用这本从这些想法中生长起来的书!或者把它当作一条重重盘匝的小径,它总是一再悄悄引向那片火山活动的危险地带,刚才提到的查拉图斯特拉福音的发源地。这部‘未来哲学的序曲’当然不是、也不应该是对查拉图斯特拉谈话的评论,也许倒是一个暂时性的术语汇编,在其中,那部书——一部在任何文献中都没有榜样、没有先例、无与伦比的书——所做的概念上和价值上的最重要更新,总算一度出现并且得命名了。”
暂时性命名,一部没有榜样、没有先例、无与伦比的书,是要从重重盘匝的小路过去,是要引向火山活动的危险地带,所以不是从《权力意志》中剥离出来,也不是《查拉图斯特拉》的重复,而是“一种未来哲学的序曲”的准备。但是指向未来的序曲,一种开创性工作需要的是在回头中荡涤一切的旧观念、旧学说、旧哲学以及旧道德,1885年6月尼采写下的《序言》就是张开了批判的弓,朝向“哲学中的一切教条学说”:它以“一切均已成笃定之论的庄严姿势”,它给崇高、绝对的哲学家大厦打上了基石,但是那只不过是“高贵的幼稚和粗浅”,它长着一张以求永恒的恐怖怪相,实际上是言语游戏,是语法上的诱导,是民众的迷信,是“对那些非常狭隘、非常人性且太人性的事实所做的某种鲁莽的普遍概括”。这一种哲学中的教条学说就是以柏拉图对纯粹精神和自在之善的发明为起点,以基督教和教会的千年压迫为形式造成的精神紧张,也正是这种教条论的恶劣、危险和谬误,正是基督教的压迫和紧张,才有了批判的力量,“我们还拥有它,拥有精神的十足窘迫和精神之弓的十足紧张!可能也还拥有箭,拥有使命,谁知道呢?拥有那个目标……”
哲学中的一切教条缘何造就了“善恶的彼岸”?那张弓被拉满,那支箭已在弦,尼采的批判从对“哲学家的成见”开始。哲学家的成见,是固化了那种叫做“求真理的意志”,尼采开篇就提出了问题:当哲学家对求真理的意志拥有足够的真诚,那么为什么不是非真理?为什么不是未知状态?甚至无知?“真理的价值问题来到我们面前,——或者,是我们来到这个问题面前?在这里,我们当中谁是俄狄浦斯?谁是斯芬克斯?看起来,这仿佛是问题和问号的一次幽会。”问题和问号幽会,问题回到了问题本身,而问题的实质是“某种东西如何可能产生于它的反面”?质问变成了反问:真理出自谬误?求真的意志出自求欺骗的意志?无我的行为出于自私自利?反问变成了否定,因为,“最高价值物必定有一个另外的、自己特有的起源,——从这个速朽的、诱惑人的、欺骗人的渺小世界里,从这团妄想和欲望的乱麻里,是推导不出它们的!”
但是只有一种人相信反面性的存在,并且产生于它的反面,那就是形而上学家,“形而上学家的基本信念就是相信价值的相互对立。”所以很明显,相信价值相互对立的形而上学家,自然是住在速朽的、诱惑人的、欺骗人的渺小世界里,自然是在这团妄想和欲望的乱麻里。对立产生判断,或者就是一个假性判断,而旧哲学家的可怕之处并不在于假性判断,而是以一种放弃假判断的方式放弃生命、否定生命,这种放弃反而是对绝对之物、对自在之物,对自身相等之物构成的纯粹的信仰,并以此来衡量现实,甚至来伪造现实——也许更可怕的是,他们用了一种“颇见美德的喧哗”来避开所谓的真诚问题,逃避他们的错解和迷失,当然也为他们的幼稚和孩子气寻找借口——尼采把他们叫做戏子,那些“狄奥尼修斯的谄媚者”,那些僭主的嬖人、佞臣,虚假、虚伪甚至伪善的存在,“那种表演,让我们这些挑剔者发笑,在审查老道德主义者和道德布道者们的巧妙算计方面,我们了无乐趣。”
尼采认为,只有坦承不真之理,才能超然自立于善恶的彼岸,哲学家的成见就是用求真理之意志来构建他们的道德论,这样道德论把所谓的彼岸建立在善恶的对立中,本身就是一种成见:求真理的意志是一种虚无主义,“这是虚无主义,是疲乏欲死的绝望灵魂的标记:无论这样一种美德能够做出多么英勇的姿态。”因为他们把求真理的意志说成是“因为能力而可能”,能力完全带上了对现实置之不理的催眠功能;求真理的能力也是基督教传授的所谓灵魂原子论,他们不同于物理学的方式解释世界,而是以柏拉图式律令来制服世界,“以他们的‘最省力’原理和最傻瓜原理提供给我们的那种享受。”而求真理的意志来自于哪个主题?是笛卡尔所说的“我思”之我?是叔本华所说之“我意愿”之我?是那种纯粹而赤裸地将对象抓住的自在之物?尼采说,一种思想的出现,不是在“我意愿”之时,而是在“它意愿”之时,不是“我思”,而是“思”需要“我”作为条件,所以在尼采看来,哲学家应该是命令者和服从者,应该以服从者的方式察觉到“通常紧随意志行为之后的强制、推挤、按压、抵抗、运动等感觉”,应该借助于“自我”这个综合概念得以让自己越过、骗过这种两重性,“一个有所意愿的人——,是对自己内部某个服从于他,或者他相信服从于他的东西下命令的。”所谓的自由意志,作为主体既下命令又把自己与实施者设为一体,只有统一体才可以享受战胜反抗的喜悦,才能对自己判断,而真正克服反抗的也是他的意志本身。
哲学家的成见是把求真理的意志变成了虚无主义,变成了基督教的灵魂原子论,变成了“我思”式的民众成见,而这一切就是在道德视野中把意志变成一种自因,像上帝一样,自因便是矛盾,便是悖论,便是“逻辑上的强奸和反常”,在破的同时,尼采建立了自由意志的核心精神,“我们越过道德,直接行驶开去;也许就这样,因为我们把船开过去了,因为我们敢于这样做,所以我们压垮了、捣碎了自己剩余的道德性……”意志就是自我立法、自我服从、自我意愿的一种“生命现象”,就是不断超越自我的“意愿足以行动”的统一体。但是尼采的破和立并没有在此终结,甚至只是打开了一个口子,她需要更深入地进入其中,需要再拉满那张弓,需要更彻底地揭露哲学家戏子的身份——如果哲学家的成见为求真意志戴上了道德的帽子,那么哲学家的殉道则完全是一种伪道德:他们为真理献身,就是把潜藏在他们身上的宣传家和戏子的成分完全公开化,“不过是一出萨蒂尔剧,不过是一段剧后打诨,不过是持续不断地证明,一出漫长的悲剧结束了:暂且假定每种哲学在其形成过程中都是一出漫长的悲剧。”这种戏子的表演,它就是一种犬儒主义。
| 编号:B82·2220618·1844 |
尼采区分了道德意义下的历史分期,在他看来,人类最漫长的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行为的价值或无价值是根据它的结果被推导出来的,也就是说,行为本身和行为的来源很少为考虑到,指引人类行为之善恶的,“是行为之结果或者恶果的追溯效力。”这就是人类的前道德纪;而称为道德纪的时期,则是把一件行为的来源阐释为意图,意图导致了行为;之后的时期被称为逾道德纪,在这个时期,“行为的决定性价值,或许恰恰是在行为的非意图成分中得到证明的”。道德的分期,不同之处在于行为和意志之间的关系,而现在的哲学家们立足于相信“当下已知”,并且在“只讲道德”中建立自由的精神——这是道德上的天真?天真的背后是揣摩“事物的本质”的那个欺骗性的原理,“每—种深刻的精神都需要一张面具:更有甚者,在每一种深刻的精神周围都持续生长着一张面具,因为这种精神所传递的每一个词语、每一个步伐和每一个生命迹象,都持久地受到虚假亦即浅薄的解读。”所以在对这种面具式的道德进行批判之后,尼采再次回到了自己关于权力意志和自由精神的“立”的体系中:必须自己考验自己,必须自己独立和对自己下命令,必须知道佑护自己:独立性的最强考验,“只要我们生来就忠诚而心怀嫉妒地做孤独之友,我们各自特有的最深沉的子夜和正午的孤独:——这样一个种类的人便是我们,我们这些自由的精神们!”
哲学家不再是立法者和服从者,不再有自己考验自己的权力意志,是因为颠倒了意志和行动之关系,是因为道德变成了欺骗性原理,是因为自由精神彻底戴上了面具,他在《宗教人》《道德的自然史》《我们的学者》《我们的美德》《民众与祖国》中再次拿起锤子,狠狠砸向欧洲的虚无主义、形而上学、犬儒主义。“宗教人”的词义就是“宗教造物”,宗教意义上的人是怎样一种存在?它是牺牲者,对精神的所有自由、所有目的和所有自身确知的牺牲,所以它也是奴化,也是自嘲,也是自残;甚至他在孤独、斋戒和节欲中,变成了宗教神经症患者。“为了上帝之故而爱人类”,这是一种看起来高尚实际上最怪癖的感情,尼采甚至认为“对人类的爱就毋宁是一种愚蠢和兽性”,而这便是权力意志的权力化的产物,“这个世界的掌权者在圣徒面前学到一种新的恐惧,他们预感到一种新的权力,一个陌生的尚未被克制的敌人:——它就是“权力意志”,是它迫使他们在圣徒面前停下来。他们必须对他提出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尼采在这里提出了“群氓”的概念,“在古希腊人的宗教性中,最让人惊讶的是那满溢出来的充沛的感激:——这是一个高尚的人种,他们就是这样面对自然和生命的!——之后,当群氓占据优势,恐惧也在宗教中蔓生开来了;基督教做好准备了。”
群氓便在欧洲人身上赋形,这是一种上帝和人类之间的等级化产物,更是人类丧失自我权力意志的悲剧,“此等人类已经以他们‘上帝面前的平等’主宰了欧洲的命运,直到最终一种渺小化的、近于可笑的种类,群盲动物,某种与人为善的、病恹恹的平常货色,今日之欧洲人,终于被栽培出来……”而欧洲出现的群氓道德也是在所谓道德进化史中出现的现象。道德,和自然相对,和过度的自由相对,但是当自然的道德律令加在人类之上,则变成了服从,这不是自我的立法和服从,而是对“信仰”“理性”和权力的服从,“你应该服从,无论对谁,长久如此:不然你就会毁灭,就失去对自己的起码尊重”——朝向上帝,人类便称自己是群氓,他从服从变成了顺从,顺从又变成了美德,“今日欧洲的群盲亦端起了架子,仿佛他们是唯一得到允许的一种人类,并且把那些使他们得以变得驯顺和容易相处的对群盲很有用的特性,美化成真正的人类美德:亦即公共意识、热心、为人着想、勤奋、适度、谦逊、谅解、同情。”而所谓的学者,早就把哲学看成了认识论,把自己变成了作诗者、收集者、旅行者、猜谜者、道德主义者、观看者——没有了立法者、命令者、服从者,只有作为工具和镜子的平庸之辈,“他等待着,直到某些东西到来,同时细敏地准备着,即便是精神造物的轻盈足迹和溜滑的行踪也逃不出他的镜面和皮肤。”
而欧洲人,后天的欧洲人,现今的欧洲人,“带着我们所有危险的好奇、我们在伪装上的花样和艺术、我们在精神和感官中酥软的、泛着甜味的残忍,——倘若我们应该拥有美德,我们估计将只拥有这样一些:它们会学习跟我们最亲熟、最衷心的偏好,跟我们最热烈的需要最好地相处:来吧,让我们到我们的迷宫里找找看吧!”民族的澎湃,爱国的忧愤,都变成了形形色色的情感泛滥,欧洲的民族化变成了对霸主的培养,“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伪善,并且将之称为它的美德。——人们不认得自己身上最好的东西,——人们不能认得。”而自我标榜所谓的“高尚”,其实就是从野蛮开始,更完整的人,就是“更完整的野兽”。好与坏,善与恶,高尚和卑鄙,带着二元论的等级制,终于演化为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主人道德的判断标准就是“对我有害者,即本身有害者”,“人类的高尚种类感觉到是自己在确定价值,他们并不一定要让自己为人称许”,而奴隶道德是有用性道德,“在奴隶的思维方式里面,善人必须是没有危险的人:他好脾气,容易骗,也许有点儿蠢,一个老好人。”——高尚和卑微,主人和奴隶,二元论的道德观所建立的是教育和教化中的隐瞒,是自欺和虚荣中的伊壁鸠鲁主义,更是建立在民众成见上的群氓。
“一个高尚灵魂不会自己在自己身上寻找、发现、也许也不会丧失的根本确知。——高尚的灵魂对自身持有敬畏。”尼采最后回到了真正哲学家的立场,阐述了高尚的真正意义,“高尚之标志:从未想到要把我们的义务降低为每个人的义务;不愿意让度和分摊出自己特有的职责;将特权及其行使算作他的义务。”回到自由意志,回到权力意志,回到生命本质,回到自我的立法、命令和服从的维度,而这就是未来哲学、未来哲学家该有的样子,这就是真正自由、高尚的精神,“从今以后,用这样一张拉紧的弓,人们可以射向最远的目标了。”
尼采的箴言和间奏曲
“以自身为目的的知识”——这是道德布下的最后陷阱:人们于是又一次深陷其中。
人们在他的上帝面前最不诚实了:他不允许有罪过!
对某一物的爱是一种野蛮:因为这种爱的施行会给所有其余者带来麻烦。对上帝的爱亦然。
作为占星术士的智者。——只要你把星星感觉成一种“居于你之上者”,你就还不具备认识者的眼光。
谁达到自己的理想,就恰恰由此超越了它。
有些孔雀在众目睽睽之下藏起它们的尾羽——并把这个叫作它们的自负。
在和平环境中,好战之人便自己对自己动手。
凡蔑视自身者,当此之际其实总还重视着作为蔑视者的自己。
一件理清了的事就不再跟我们有什么相干了。——那位呼吁“认识你自己”的神衹——以及苏格拉底?——以及“科学人”?——是什么意思啊!也许是在说:“不要再牵涉到你自己了!要客观!”
本能。——房子着火时,人们便连午餐也忘记了。——是的:不过他们会在灰烬上补一顿的。
沉重、消沉的人恰恰是通过那些让他人沉重的东西,通过恨和爱,而变得轻松,暂时来到他们的表皮。
为自己的不道德而羞耻:这是阶梯之一级,在这条阶梯的最高一级,人们也会为自己的道德而羞耻。
什么?一个伟大的男人?我总是只看到出演自己理想的戏子。
今日,一位认识者或许很容易感到自己是上帝道成兽身。
不是他们的人类之爱,而是他们人类之爱的无力,阻碍今日的基督徒把我们——烧死。
没有道德现象,而只有对现象的某个道德诠释……谁感觉到自己是被预定去观看而非去信仰的,则一切虔信者于他都太过嘈杂和纠缠:他抗拒他们。
我们生命的那些伟大关头就在于:当我们争得勇气,敢将自己的恶更而命之为我们的至善。
感性经常催促爱快快生长,以至于根基一直虚弱而易于动摇。
这是一个妙想:上帝当初想当作家时去学了希腊语——他学得并不特别好。
连姘居也被腐蚀了:——通过婚姻。
魔鬼对上帝有最广阔的视角,因此他远远避开了他:——魔鬼就是认识最古老的朋友。
人们为了他们的美德而受到最好的惩罚。
一切可信度,一切好良心,真理的一切视觉假象,皆从感官而来。
在复仇和恋爱中,女人比男人更野蛮。
下半身是人不那么容易把自己当作神的根据。
我所听过的最贞洁的话:“在真正的爱中,是灵魂包裹了身体。”
对我们做得最好的事情,我们的虚荣想的是:它正好可以当成对我们来说最困难的事情。论某些道德的起源。
被一个时代感受为恶的东西,通常是以前曾被感受为善的东西的不合时宜的尾音,一一是某个更古老理想的返祖遗传。
围绕英雄,一切皆成悲剧,围绕半神,一切皆成萨蒂尔剧;而围绕上帝,一切皆成——什么?也许皆成为“世界”?——
出于爱所做的,总是发生于善恶的彼岸。
自杀的想法是一种强劲的安慰剂:人们靠它很好地度过了一些很坏的夜晚。
人们确实是用口说谎的;不过,用那张说谎说出来的嘴,他们倒是道出了真理。
基督教给爱欲灌毒药:——爱欲没有被毒死,却因而蜕变成恶习。人们最终爱的是他们的欲望,而不是所欲望者。
谎言中有一种无辜,是对某件事情深信不疑的标志。
在一个人受诅咒之际行祝福,是不人性的。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7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