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0-13《永远的莫扎特》:自杀是唯一的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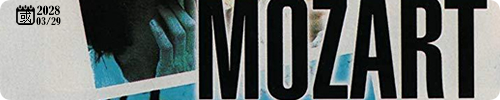
莫扎特的音乐出现在最后:一部名为《宿命的波兰舞曲》的电影上映,在首映之前,有人弹奏了莫扎特的音乐,有人说:“莫扎特的音符太多了。”有人则说:“莫扎特的音乐温柔而轻率。”在钢琴的旋律中,哈尼和莎娜坐在那里听着,而导演维克却独自一人走上楼梯,然后在楼梯的尽头坐下来,掏出一支烟吸着——当他远离了观众,远离了电影,思考中的他是不是成为宿命之一种?电影是不是就如莫扎特的音乐一样,既是温柔轻率的,也呈现了“音符太多”的无力感?
“永远的莫扎特”,音乐一定指向了永恒性,而电影呢?虽然首映中知事也来了,观众也到场了,但是电影内部的困境却并没有化解:“我们破产了……”这是电影放映遇到资金的问题;“很多人跑了,但是电影已经封镜了……”剧组人员离开了电影,封镜只是一个仪式;在首映式的时候,有孩子站在影院门口想观看这部电影,却被赶走了,因为孩子不适合观看电影……这就是电影的现状,这种现状和电影片名形成了某种互文,“为什么是宿命?”永远的莫扎特,不是音乐的永恒,不是艺术的永恒,而是宿命变成了电影的永恒,就像身为导演的维克坐在那里吸着烟,进入到了无法摆脱的宿命状态中。
这当然是一部已经拍摄完成的电影,在完成时态中才具有“宿命”的意义,但是未完成的电影呢?正在发生的电影呢?《宿命的波兰舞曲》是从拍摄到完成的一部电影,在一开始的时候,36名符合剧情的演员就被招入进来,这部以10万美元的价格获得拍摄权的电影,无疑代表着一种产业发展的方向,但是一部名为“宿命”的电影在这种产业机制中必然走向“宿命”——戈达尔以“戏中戏”的模式再一次指向了“电影何为?”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本质是:电影如何成为一种对现实的关照?艺术有没有真正的永恒?或者这就是对电影艺术本体论的探讨,而哈尼的那一句话几乎揭示了现实的困境:“过剩的现代人,已经没有了热情,没有了同情心,他们和未来联结的婚姻一样,已经变成了空谈——根本没有爱。”当现代人没有了热情,没有了同情心,电影里也根本不会有爱,而没有爱的艺术是不是也是空谈?
现实的困境被揭示出来,而现实的困境本身就是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的一个主题词便是:“卡米尤要和詹洛姆一起去萨拉艾维。”人物:卡米尤和詹洛姆,目标:萨拉艾维,事件:一起去。这才真正构成了一部电影,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去演那部爱和偶然的电影。”这部电影和爱有关,和偶然有关,爱和偶然无疑站在了过剩的现代人的反面,甚至站在了商业电影的对面,实际上,卡米尤和詹洛姆并不是去演一部电影,而是进入电影,参与电影,因为现实才是一部真正的电影——现实是冒险的,因为萨拉艾维就是发生着战争的前线,现实是反抗,要去充满危险的地方,卡米尤的母亲就反对说,“这就是自杀!”但是得到的回答是:“自杀才是唯一的真理哲学性命题,反抗是人类的第一页……”
| 导演: 让-吕克·戈达尔 |
实际上对于这一家人来说,电影出现了分歧,电影走向了两种状态:父亲维克得到了电影《宿命的波兰舞曲》的拍摄权,他当然要全身心地投入到电影的拍摄中;但是这部电影却被卡米尤认为是荒唐的,她要去演的是那部“爱和偶然”的电影,是要在自杀的冒险中揭示人类的反抗,即使家人反对,她也会和朋友詹洛姆一起去,甚至洛瑟多听说了之后也要和他们一起,“生与死只是一条线,过去了就是地狱。”两种电影成为了关于现实的异构,一种是表现宿命真正要拍的电影,一种是用自己的行动来演绎爱和偶然的电影,一种是工业体系下的电影,另一种则是将哲学转化为行动学的实践。
但是维克为什么一开始要和他们一起?“卑怯也好,混沌也好,却是重复。”这是维克对现实的注解,在他看来,冒险和反抗一直在重复,欧洲的90年代就是走着30年代的老路,也就是说,他们所谓演绎爱和偶然,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人演绎了,他们只不过是重复,根本没有变奏的乐器——就像莫扎特的音乐,是一种重复而永恒的存在。但是说出这番话的维克已经深谙了电影的本质,而这或许也是一种宿命,他和他们一起离开家,也是为了在他们的行动中感受并未消失的激情。在这趟旅行中,洛瑟多跟着卡米尤和詹洛姆,也是为了发现爱和偶然,在阿尔洛河边,卡米尤说起了一套哲学,“我是我,但我不是我,我身体产生的不是我的感情……”自己和另一个自己,肉体和精神总是处在分离的状态中,在这种哲学的指引下,卡米尤就是为了找到“我为什么存在”的哲学命题,而受其影响,洛瑟多有着对“自杀”的某种向往,她说起自己曾经被警察的车装过,差点就死了,但是没死,“死在书本里是很美的事。”
卡米尤提出“我为什么存在”,洛瑟多向往很美的死,詹洛姆说:“坚持住,战斗!”三个人进入的就是一部不是宿命的电影,维克和他们一起开启了旅行,但是他认为历史就是重复,没有偶然,也没有我,他洞悉了这个世间最残酷的现实,“以前的宇宙也像你一样,后来老了,失去了。”他对卡米尤这样说,语气中带着太多的宿命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独自搭上了一辆卡车,离开他们重新开始了那部电影的拍摄——这是他们真正分道扬镳的标志,当现实就是一种重复,爱和偶然也成了宿命,而现实之外存在着电影,它是宿命,也可能是另一种创作。于是在分道扬镳之后,三个人慢慢靠近萨拉艾维,也终于走上了冒险之路:他们看见了坦克,他们听到了炮火,他们经历了战争,当然,最后他们也完成了死亡,“萨拉艾维,西欧的娼妓。”墙上的这句话成为对现实最无情的揭露,而他们以死亡的方式完成了萨拉艾维式的反抗。

《永远的莫扎特》电影海报
一部电影在战火纷飞中被拍摄,的确,他们看起来就是一种自杀行为,他们演出的爱和偶然也成了死亡的必然。而另一边当维克离开他们进入剧组,他开始了好莱坞式的电影拍摄行动中。但是,这是一部怎样的电影?一部被资本控制的电影,一部导演没有自由的电影,一部完全是宿命的电影,“要加入演技,演技可以代替语言。”那个剧组人员的话无疑就是电影拍摄的宿命言说,而在电影拍摄中,维克看到了另一种反抗,另一种自杀,以及另一种爱和偶然:那个穿着红裙的女主,在大风制造啸叫的海滩上,说着剧本里的话,也说着剧本之外的话,“自从失去职业依赖,在缓慢的空虚时刻,存在的悲伤和灵魂深处的思考……”“我的存在只有我,这不是虚构,作为人,我要杀了他们……”倒在沙滩上的时候,她却说:“死了才好……”从第52个镜头,到53、54、55、56个镜头,再到115个镜头、445个镜头、517个镜头、608个镜头,女主一直在对维克说着同一句话,“死了才好”终于变成了真正的死亡,于是有人喊道:“好的,停!”
一部电影在拍摄,女主在用演技言说,一部电影在阐释“宿命”,女主却在反抗,一部电影在表现死亡,女主的死亡才得以真正完成。这就是电影?维克看见了发声的一切,听到了她的呼喊,但是他只是一个导演,他无法左右电影,甚至于现实也完全注解了电影——这是一部没有完结的电影,现实在弥漫,在扩张,现实就是电影,所以,他说:“结束是假定的话。”在这个意义上,身处电影工业生产线上的维克,在逃离和进入中,发现了电影真正的宿命,自杀成为一种反抗,战斗成为自我的存在方式,“死了才好”是对现实的无情控诉,但是对于维克来说,在电影的宿命中,他也无力改变这一切,低头也罢,无语也好,他只是完成了一个任务,而在公司破产,人员离去,电影发行失败的情况下,电影就是一种空谈,它无力深入那个现实,却被现实残酷地解构了。
自杀是唯一真理性哲学命题,在现实中自杀是反抗,在电影中自杀是剧情,而反过来,反抗杀死了现实,现实又杀死了电影,没有永远的莫扎特,只有宿命的莫扎特。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