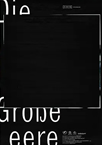2023-11-25《大空虚》:去人类化的景观社会

这是一个静谧的世界,山川无声,岩石无声,大地无声,天空无声;这是一个静翳的城市,高楼依然,街道依然,广场依然,高架依然,却不再有人;这是一种静止的生活,一帧一帧的画面出现又消失,每个场景持续10多秒的时间,画面几乎没有变化,就像静止了一般……静谧着它们的静谧,静翳着它们的静翳,静止着它们的静止,在深秋的影厅里,只有黑暗中发出的呼吸声。
但是,静谧、静翳和静止却并不是没有声音,在画面全部呈现为空镜头的时候,声音反而变成了一种叙事:一开始并没有声音,在自然状态中,声音消失变成了一种自然;后面便出现了类似白噪音的声音,像在啸叫,不仅叫醒了耳朵,甚至在破坏听觉系统;那黑暗中的霓虹灯次第亮起,接触不良导致电器发出滋滋的声音;大约三分之二处,出现了旁白:“是的,我活在黑暗时代!天真的话是愚蠢的。”朗诵布莱希特的《致后代》成为电影中唯一的人声;之后人声消失,是森林是河流是雷雨发出的自然之声……声音沉寂,声音持续,声音爆发,既有物之声,也有人之声,既有自然之声,也有技术制造的声音。
几乎静止的画面,不同声音混杂的叙事,声画不是合一也不是对位,它们的组合所产生的效果就是“大空虚”。电影片名“Die Große Leere”,英文为“The Great Void”,“大空虚”像是直译,而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的“西湖荣誉”评优单元翻译的中文片名为《遗迹》。的确,从自然形态的山川大地到人类居住的城市,再到摄影机进入的具体的家,空间的改变具有一种不断缩小的线性逻辑,也越来越接近人所拥有的生活,这里所呈现的一切都可以看做是“遗迹”:从大海边生锈的机械,到城市里的道路高楼,再到房间里的床、水槽、墙,都是某种遗迹,而遗迹指向的便是人,不管自然遗迹,还是人类活动遗迹,或者是身体相关的遗迹,都刻上了人类的烙印,而当它们都成为遗迹之后,反倒折射出人之消失的现状。
| 导演: 塞巴斯蒂安·梅茨 |
因为遗迹一定是人类留下的,一定是人类制造的,一定是人类生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遗迹”的命名表达了塞巴斯蒂安·梅茨对人类社会的某种审视,它指向的是人类被抽离之后的境遇,这就是一个充满不真实感的世界:在整部电影中,没有出现一个人,无论是远离城市的山川,还是人类生活的城市,甚至还散发着家庭气息的房间,都没有人经过,都没有人出现,这是一种人迹消失之后的荒诞感:在平时车水马龙的街道,现在却没有一辆车,没有一个行人,一切都是空空荡荡,但是红绿灯还在变化,仿佛它们还在维持着交通秩序;夜晚的城市一片漆黑,高楼大厦里也不再亮起一盏灯,但是电器接触不良的滋滋声传来,画面右下方的霓虹灯闪烁着,之后是画面左上方的霓虹灯开始闪烁,右上方的霓虹灯也开始闪烁,渐次亮起的霓虹灯照亮了夜晚的这一片区域,但是依然没有人出现。
遗迹的出现和人类有关,而在只剩下遗迹的世界里,人类也成为了不在场的遗迹,塞巴斯蒂安·梅茨制造的这个景观社会消除了人作为主体的存在,只剩下绝对的静默,绝对的荒凉,但是没有人并不意味着人真正的消失,而是没有人显现,他们在别处,在未知的别处,在封闭的别处,在镜头外的别处,如此,整个世界便呈现出一种末日状态,只有河水在流动,只有鸽子在飞翔,只有红绿灯在闪烁,而“末日”的到来本就指向人类的终点,因为只有人类才有末日,对于其他物种来说,末日几乎是无意义的存在。“遗迹”强调的是人类化,塞巴斯蒂安·梅茨却又以去人类化的方式制造了末日的景观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讲,电影的荒诞感和不真实感更像是塞巴斯蒂安·梅茨刻意表达的——在映后的交流上,电影音效师就讲到了电影的一个秘密:在美国拍摄的是城市部分,在德国拍摄的事自然部分,那些城市无人的状态是通过后期将车和人都抹掉了,也就是说,技术达到了无人的真实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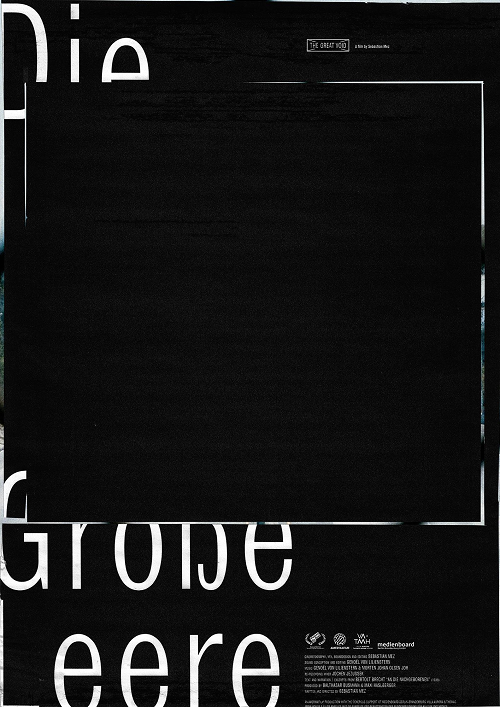
《大空虚》电影海报
真实感的画面传达的恰恰是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所以影像就成为了一个在观者内心制造绝对静默和荒凉的文本,塞巴斯蒂安·梅茨通过这个文本阐述了人被抽离之后的“遗迹”,正是为了在这个世界被物化的过程中把人这个主体也物化了,因为当世界变成巨大的遗迹,世界也就成为了一个留存的物,人也变成了其中的一部分。但是,“遗迹”呈现的是某种表象,如果按照“遗迹”的叙事,当那只蝎子从黑暗中爬出来,如果画面中出现一只手,然后啪的一声将它打死在墙上,留下了死亡的“遗迹”,是不是完整地阐述了遗迹的出现过程和最后被物化的景观?所以,“遗迹”只和人类有关也将主题窄化了,而“大空虚”则表达了世界的存在状态,它指向的是消失,是陌生,是荒芜,塞巴斯蒂安·梅茨正是通过“大空虚”的绝对化意义,去除了人类的存在,也去除了人类所代表的文明、科技、思想——布莱希特的《致后代》被吟咏的时候,“我活在黑暗时代”就是对这个世界的控诉,当这里只有不公而没有怒火,当不再“以善回报恶”,当“道路通向泥沼”,还有什么是意义?还有什么是可说的,还有什么必要留下遗迹?
大空虚的反面是喧嚣,是浮躁,是紧抓住的欲望和权力,甚至是一切的娱乐化,当那台吊扇不断加快旋转的速度最终变成影像交叠的矩阵,李小龙在内的电影世界是不是就是景观社会的一种写照?而人类也在真实世界失去了显现的可能成为一种影像化的标本,它们被复制,被展现,成为遗迹,却不是鲜活独立的人。但是在这“大空虚”的世界,塞巴斯蒂安·梅茨并没有指出最后的出路,他只是静态地呈现,只是冷静地观察,只是静默地记录,也许世界本身就是这样,它一直在通向末日之路上,它一直就是去人类化的存在——当塞巴斯蒂安·梅茨通过科技手段完成了无人的直观呈现,是不是也在反讽着自己在技术主义下的“遗迹”生产?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2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