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7-13《文学空间》:作为渊源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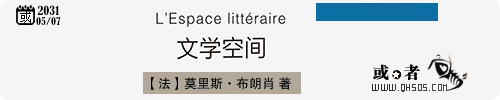
阅读仅仅使书,即作品变成——成为——作品,超越创造它的人,超越在其中所表达出来的体验,甚至超越一切传统使其成为可支配的艺术资源。
——《作品与交流》
的确被命名为“阅读”:拿起莫里斯·布朗肖写作的《文学空间》,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在摘录、回味和思考中最后合上了书——一种阅读的过程最终完成。的确是对作品的阅读,从眼前作为物的一本书到感受书中的观点,再到若有所思和偶有所获,这是阅读带来的意义?阅读是对一本书的阅读,阅读是对一本作者写成的书的阅读,阅读是将读者的自己放进作品中的阅读,但是为什么布朗肖要说阅读“从不问书本,更不会问作者”?为什么他把阅读看成是“是使书写成或被写成”而没有作家这个中介的过程?——布朗肖写下这些关于阅读的话,是不是在进行自我否定?
他说,“阅读不要求有天赋”,它只是揭露了“这种对天生特权的求助”;他说,阅读所要求的是“无知”而不是知;他说,阅读不是一种重新书写,也不要求读者自己投入到书中;他说,阅读并非谈话,也不进行讨论,更不是询问……实际上,布朗肖所定义的阅读是摆脱了一切作者的阅读,是让阅读接近书本身的行为,只有把书当成一个无作者的书,不建立从作者出发的关系,不听从于“文本”,阅读才能让作品成为作品,超越创造它的人,从而具有一种阅读本身的体验:“这个在场的、陶醉的和透明的是的自由就是阅读的本质。”它是自由的,是纯粹的,是触及了本质的,是无休无止的——在“永不开始永不终止的东西的空无的深处”。而且更进一步,阅读甚至比创作更积极,更具有创造力,“虽然她不制造任何东西”。而在这个意义上,布朗肖认为当阅读作品让作品打开空间产生了“迎接它的那阅读”,它就是建立了交流:这是一种“变成读的能力,变成能力和不可能性之间,变成与阅读时刻联在一起的能力和与写作时刻联在一起的不可能性之间的开放的交流”。不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交流,也不是读者获得和作品的交流,而是作品自己与自己交流:作品永远保持着未完成的状态,作品永远呈现着起始和最初的决定,“取消了作者的那时刻也就是这时刻,作品在此刻向自身开放,阅读在开放中获得根源。”这就是“空无”,它触及了进展的内在深处,它不再画上休止符,“阅读在自身当中留下了真正在作品中起关键作用的东西,因此,它最终独自承担着交流的全部重担。”
阅读是一种无知,阅读是一种空无,它让作者处在被摆脱的位置,它让作品不再是完成的状态——布朗肖的《作品与交流》这一章节所阐述的“阅读”和“交流”,探讨了阅读的本质和交流的意义,但是不可否认,一切的阅读还是以作品和作家为出发点的,或者在物的层面上,作家制造了作品,作品处在完成的状态中,所以阅读的思考本质上还是作品的思考:它如何总是处在原初状态?它如何需要自我交流?它如何让阅读成为“顷刻间逾越的纯粹的是”?这诸多的“为什么”,其实要解决的唯一一个问题是:文学是什么?在开篇中,布朗肖其实就明确了文学作品的属性:它的孤独“向我们揭示了一种更具根本性的孤独”。这种根本性的孤独是排除个体主义孤芳自赏式的孤独,是不寻求差异的孤独,是“既不是完成的,也不是未完成的”孤独,毋宁说,作品的唯一状态就是“存在着”。
在这里,布朗肖首先把创作的人置于一边,是作品本身将“已完成创作的人”打发了,而且,被打发者并不知道自己被打发了,这就是一种“无知”,“作家从不知他的作品是否已完成。”在这个意义上,不是作品属于作者,而是作者属于作品,作者是一种空无的存在,只有这样,作者才会在没有完成的时候卷入一项幻想之作,作品不再理他,而作家也从不读自己的作品,这就是“勿读我的书”。在这里布朗肖解构了作者和作品之间的关系,在未完成的状态中让作品和写作保留了可能性,“作品就是决定本身,它把作家打发走,把他删除,把作家变成劫后余生者,变成百般无聊、无所事事者,变成无生气的、艺术并不依赖的人。”无知和空无的作者会再次拿起笔,他用一只不是被命令驱使的手,不是应当拿起笔的手,不是呈现为“惩罚式握笔”,而是用另一只手让写作变成“成了永无止境、永不停歇的”事。
当写作是永不止境的发现,作家才能向着普遍,才能以卡夫卡的方式让“他”代替“我”从而走进文学。在布朗肖看来,“他”是可以变成任何人的我自己,是变成另一人的他人,只有这样,我所在之处再无法向我说话,那个“我”才不是他自身——从“我”被“他”代替的那一刻起,写作就成为“投身于时间不在场的诱惑”,我们才能接近孤独的本质,“当我独自一人时,我并非独自一人,但是,在这现时中,我已经以某人的形式回到了我自身。”这就是“无人”,不是这人也不是那人,不是个体的你和我,而是无名的、无人称的存在,是非真的、非现实的存在,这就是根本性的孤独——布朗肖的无知、空无和无人,构成了否定性的存在,而这种否定性是对传统文学的一次解构,更是以肯定性的方式重建起拥有根本性孤独的“文学空间”。
| 编号:H38·2240411·2090 |
这就是马拉美所说的“我感觉到一些由写作这唯一行为所引起的极其令人不安的征兆”,根本性的处境、极端的事被“写作这唯一的行为”所把握和阐明——什么是“写作这唯一的行为”?布朗肖认为,马拉美把写作置于一种唯一的行为中,是因为认识到了话语的双重状况,一种状况是“未加工的或直接的话语”,它表现为“沉默”,“……也许为交流话语,每人只需在他人手里静悄悄地拿起或放下一枚硬币……”未加工的话语与诸物的实在相关,当叙述、教授和描写,就是显示诸物的在场并“再现”它们;另一种则是本质的话语,它远离诸物,使它们消失,既让“一种本质的事实”不在场,又通过这不在场把握事实,然后“将它移植到它的近乎震颤的消失中”,这就是思维,诗歌的意义就是在这种本质的话语中“自言自语”,以此所建立的就是文学空间。
“在那里,话语不再是其自身,只是已消失东西的表象,它是想象物,永不停歇,永无止境。”这是文学空间的点,它是存在却是不成为任何东西的存在,是任何东西不会完成的存在,布朗肖给了它一个名字:渊源,作品就是“作为渊源的作品”,“凡属于这另一时间者,也必定属于闲散的空无的深度——在那里,存在永远成不了任何东西。”作品是作为渊源的作品,所以作品永远不是完成之时的作品,而是摆脱了一切束缚的作品,是“那个唯一值得付出代价去实现的东西”,“只关注辉煌成功的人,其实是在寻找这个一事无成的点。”布朗肖从卡夫卡的经历探讨了这一作品的“要求”,战争的爆发、订婚的危机,卡夫卡遇到了人生的困难,甚至处在可怕的崩溃的状态中,于是这些不幸的遭遇让他开始展现他的作家人生,而卡夫卡的写作就是进入到这样一种空间里,在渊源处,永在渊源处,“卡夫卡越写作,他对写作就越没有把握。”当他以“新的灵魂转生”完成文学变体的时候,他实际上“虔诚地沉湎于写作这种根本的谬误”,让作品自我完成,所以卡夫卡就是“诗人”的代表,“对于他来说甚至连一个世界也不存在,因为对于他只有外部,只有永恒外部的流淌。”
渊源的作品,无止境的作品,自我完成的作品,“作品把献身于它的人引向它经受自身不可能性考验之处。”在这个意义上作品就是一种体验,是与存在的接触中实现自身的更新,但却是“不确定的检验”,它追求的不是不确定,而是被不确定所确定的——从渊源处,在永不止境处,作品的这种不确定的确定,就是死亡,“因为死亡是极端。谁把握住死亡,谁就能高度地把握自己,就会与艺术所能及的一切相联,就是具有全面的能力。”死亡总是被回避、被逃离,是因为死亡本身在死亡面前逃避,因为它是可能的,而当死亡成为我的权力时,死亡当然更会成为可能,所以死亡从来不是那种已给出的东西,而是那种要去做的事,这就是布朗肖赋予渊源的作品的一种使命,“即我们应当积极地去掌握住的、成为我们的活动和我们自制力的源泉的东西。”死亡是一种折磨,当死亡成为使命,就意味着“欲以自身死亡的典范价值来主宰这个死亡”,这就是自杀——在某种意义上自杀消除了死亡,它向生命提出了一个问题:生命是可能的吗?自杀是可能的吗?“自杀无疑保留着做出特殊肯定的权力,它始终是一件不能仅仅说成自愿的事件,它是一件经久不衰并超出预谋的事件。”
死亡是体验,死亡是作品,它在马拉美的《依纪杜尔》中,让死亡在自杀中得到了净化,“而且是一种不在场的净化,一种使不在场成为可能并从不在场中汲取可能性的尝试。”但是马拉美在最近的版本中修改了作品,使得作品变成了依纪杜尔的独白,独白把苍白无力的“我”从文章中体现出来,于是这个个人化的声音无法再面对死亡的使命,再无法成为纯粹的命运,“我们只拥有意识的在说话的在场,这意识在已成为它的镜子的夜,只瞻望它自己。”和马拉美不同,里尔克所描写的死亡抵达了“正确的死亡”,它是忠于自己而死的死亡,是忠于死亡的死亡,《马尔特》就是发现了无个体的死亡,“它是我们力量的过度,使之过度的东西,如果我们能再次把这力量变成我们的力量,那它会使之成为神奇的。”在这里布朗肖指出里尔克的体验是创造了死亡的空间,把诸物放置在内部空间里,可见之物变成了不可见之物,这就是使命,就是话语,“它是诗歌的空间,是俄耳甫斯诗歌的空间,诗人当然无法进入其中,诗人进入其中只是为了消亡,在这空间中,诗人只有保持一致才进入裂口的深处,这裂口把诗人变成一张无人理会的嘴,正如它对待聆听寂静的分量的人,就是作品,是作为渊源的作品。”
马拉美把不在场看成是一种否定的力量,让它避开“诸物的实在”,让我们从事物的重压下解脱出来,而里尔克却把不在场看成了诸物的在场,这是存在之物内心的在场,被封闭在死亡绝对不确定性中,死亡便成为了不完成的东西。里尔克的死亡体验所完成的是死亡的创造和死亡的转变,那么这个文学空间中,作品成为渊源的存在,是不是需要灵感?灵感是什么?布朗肖将它比喻成夜,不是“一切都消失了”的夜,而是“一切都消失了”的显现的夜,“但是这另一种夜是人们找不到的死亡,是自我遗忘的遗忘,这遗忘在遗忘内是无休止的回忆。”从白天到夜,这另一种夜需要的是把自己变成一种劳作,一种逗留,一种挖地洞式地打开,“总有这样一种时刻:在夜里,兽会听到另一头兽的声音。这是另一种夜。”它就是诗歌空间中的灵感,是俄耳甫斯的目光,“灵感意味着俄耳甫斯的灾祸和对他的灾祸的确认,而灵感并不会作为补偿而预示着作品的成功,同样它不会在作品中肯定俄耳甫斯的理想的胜利和欧律狄刻的幸存。”
这里就有了布朗肖对灵感阐释的另一个面向:缺乏灵感,它是俄耳甫斯目光中的灾祸,不会肯定地成为欧律狄刻的幸存——正因为灾祸存在,灵感的缺乏才会是一种创造力。在这里,布朗肖把灵感的本质归为与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写作”:自动写作摆脱了常人的目光,它以自由的方式与“睡眠的体验”关联在一起;自动写作消除了束缚取消了中介,对于它,无人再拥有权利,它也不属于任何人;自动写作不是说的能力,在这种语言中,我一无所能,我从不说话——当安德烈·布勒东在《第一宣言》中让诗人“随心所欲地继续吧。请信赖喃喃细语的取之不尽的特性”,就是让灵感变成用之不竭的存在,让写作成为永无止境的过程,“灵感,这种不会结束的游荡的话语,就是漫长的不眠之夜,而作家正是通过避开它的方式来拒绝它才开始真正写作。”
从作品摆脱作者成为未完成的存在,到文学的体验追求不确定的确定,从灵感的缺乏成为一种创造力,再到自动写作连接起自由之夜,布朗肖的这些阐述都是通过作品这个起点完成的,而通过“阅读和交流”打破对作者的依赖,让作品成为作品。布朗肖无疑完成了从孤独的作品到阅读这一文学行动的构建,而回归到文学的本质,他认为就是一种“完成”的体验,完成是一种“唯有自由永驻其中的真正的世界的建构”,它的意义是未完成,是正在完成,是试图完成,“艺术必须成为自己的在场。艺术欲肯定的东西,就是艺术。它要寻求的东西,它试图完成的东西,就是艺术的本质。”当文学的完成是未完成、正在完成和试图完成,在渊源之中,它永远处在“开始”的位置:它让作者成为一种“无人”,它让作品成为无止境,它让灵感成为缺乏,它让阅读成为“无知”,永远以孤独的方式通向未来:
这种孤独是对未来的理解,但也是因无能为力而致的理解:预言式的孤立,它在时间之内始终宣告着开始。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