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8-04《我们一无所有》:回忆是唯一真实的资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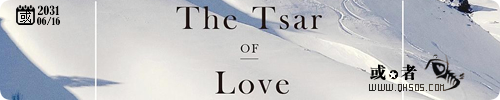
狱卒摇摇头,“整个地窖只有一间单独禁闭室,里面只关了你一个人。”
——《花豹》
在被关押的地窖里,罗曼敲击着墙,像摩斯密码一般地开始和未曾谋面的狱友对话:罗曼问:你是教徒吗?对方回答:“我是神学院的学生。”对方轻敲:“这里是圣彼得堡的最高处,景观最佳。”罗曼回应:“这些牢房没有窗户,牢房在地窖。”在封闭的牢房里,在阴暗的地窖里,在看不见自由和明天的世界里,敲击然后对话成为罗曼活着的希望,他最后希望这个神学院的学生出狱后把自己的告白交给弟弟沃斯卡的儿子弗拉基米尔,告白是关于沃斯卡的,“他爸爸的脸孔,你一定要跟他说他在哪里可以看到他爸爸的模样。”沃斯卡因宗教激进主义受到了司法裁决,他散步的是“天堂之门等着为我们敞开”,遭到逮捕之后,身为哥哥的罗曼利用自己对画作审查的机会,将沃斯卡的肖像嵌入了上百张照片和画作中,“年轻的沃斯卡,年老的沃斯卡,人群之中聆听演讲的沃斯卡,在田野和工厂里努力工作的沃斯卡。”
沃斯卡变成了画作中并不起眼的肖像,罗曼用这种创意留住了沃斯卡的样子,他希望后代能够从这些画作中复原前一代人的模样,所谓流传,大约就是一种“印像”的保留,就像十九世纪画家普尤特·札哈洛夫的那幅《午后的空旷牧野》,经典之留存,就在于不掺杂任何其他的东西:“画中一片空旷的牧野沐浴在午后的日光下,牧野缓缓攀升,升到画布上端三分之一之处。一道白色的石墙斜斜地越过田野。一栋小屋,一口水井,一座延伸到半山腰的香料作物花园,矗立在朦胧的阴影之中。画中看不到半个人影,呈现静止状态,甚至连只迷路的山羊都没有。”但是,在一九三七的圣彼得堡,这就像是一个幻象,当罗曼告诉狱友弟弟沃斯卡“在一切的背景里”,他自以为留存着的肖像“在他们所有人的后方”,但是走出牢房被行刑之前,狱卒告诉他的一个事实是:“你隔壁没有牢房。”整个地窖只有一间禁闭室,禁闭室里只关了一个人。
这是一个将希望碾碎的结尾,地窖里只有一间禁闭室,禁闭室里只关了一个人,何来隔壁?何来敲墙的对话?何来神学院学生?何来将消息带给沃斯卡的儿子?又何来一种流传?这当然荒谬的,就像是罗曼做了一个梦,醒来是比现实更为残酷的命运。无法将这个秘密告诉别人,无法让沃斯卡的后代看到先辈的“印像”,这也许并不是最主要的,当隔墙的对话者不存在,当神学院的学生是虚无,希望就像信仰一样,被轻易解构了:在死亡面前,从来没有所谓的救赎,这座圣彼得堡的牢房在地窖里,它也从来没有一扇窗户。而这样的现实也是沃斯卡命运的一种写照,他之所以成为异议分子遭到逮捕,就在于他坚信宗教可以解救受罪的灵魂,坚信“天堂之门等着为我们敞开”,当政治力量取代了宗教激进,当政治集权摧毁了个体命运,这里没有可以打开的窗,没有隔墙的对话者,没有信息最终的传递者,只有封闭、黑暗,以及历史不被解救自噬的结局。
第一章的题目是《花豹》,也是对这一残酷现实的揭示:罗曼回忆小时候和沃斯卡去动物园,看到关着老虎的兽笼,在铁栏杆后面,就是一只在慢吞吞、静悄悄踱步的花豹,“这么一只凶猛的野兽居然如此颓萎,既是神奇,也是羞愧。那是我们第一次亲眼见证监禁。”花豹的命运就是被监禁的命运,罗曼在牢房生活中,唯一想要学的一个词就是波兰文的“花豹”,牢房让波兰文老师教罗曼学习波兰文的目的是让他承认和波兰间谍有关,因为他们在罗曼审查修复的画中找到了他和波兰间谍秘通的“证据”,懂得波兰文是让罗曼招供的最好办法,但是受到污蔑的罗曼唯一想学的一个词就是花豹,“Kocur”这个词对于他来说不只是一个波兰文,而是对自身命运的一次控诉,甚至当波兰文老师教他这个词之后,他对她产生了感情,“她的声音传达出慰藉,让我感觉自己依然活着。”甚至那一句“我爱你”也不再是滥情、感伤和荒谬,它成为了罗曼活着并让“沃斯卡”活下去的希望。
但是当一切变成了历史自噬的结局,“花豹”也个温暖的词也变成了冷酷的词,它别无他意,就是监禁,就是牢狱,就是毁灭。第一章的《花豹》,一九三七年的“花豹”,圣彼得堡的“花豹”,作为A面的一章,也是全书的开篇,而从一九三七年“圣彼得堡”的A面开始,历史被打开了,它从A面到“中场休息”,再到B面,像一盒卡带,最后在“让我如愿。拜托。”中关闭,历史就是这个从A面开始播放到B面最终结束的封闭区间:从一九三七年到二〇一三年是历史的时间轴线,从圣彼得堡到基洛夫格勒是历史的空间区间,在时间和空间共同组成的历史里,没有打开的窗,没有隔墙的对话者,没有“我爱你”的温馨,只有“里面只关了你一个人”的无力感,而这就构成了安东尼·马拉所说的“我们一无所有”的境遇,当每一个个体都成为历史叙事中的“花豹”,所谓被嵌入的肖像,不是后来者寻找希望的符号,而是被历史裹夹着再无自我的象征。
实际上,当马拉构筑了历史的残酷封闭论,他的文本也成为历史封闭论的一种,但是一个美国的作者如何深入这个异域的历史?从一九三七年到二〇一三年,从圣彼得堡到基洛夫格勒,时空构筑的历史属于一个叫苏联-俄罗斯的国家,属于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国家和民族构成了历史封闭论的最封闭世界,在没有任何外来者被描述的世界里,马拉却以他者视角构筑了一个异托邦——马拉出生于1984年,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艺术硕士,荣获斯坦福大学“华莱士·斯特格纳奖学金”,并在斯坦福大学教授小说创作……从马拉的生平来看,他几乎和这片土地没有任何关系,既不是出生在80年代的苏联,也没有亲历苏联的解体和车臣战争,当然更没有和苏联政治相关的记忆,而当他用厚重的文本构建一个异域世界的历史,是不是仅仅是一种“他者”的虚构?甚至会不会是对苦难、迫害、集权等的美国式俯视?
| 编号:C55·2240418·2102 |
这样的猜想并非没有道理,当一个他者深入那一段历史是不是本身就是虚构?而马拉的虚构似乎来源于一句话,“回忆是唯一真实的资产。”这是距离罗曼最后走出圣彼得堡地窖76年后的一次策展上,在无数沃斯卡肖像被看见的时候,一名年轻男子说的话,而这句话正出自被驱逐出苏联来到美国的纳博科夫,身为流亡者的纳博科夫成为美国公民,却以另一种目光回望那片土地,对于他来说,回望就是对历史的审视,因为他曾经经历,因为他曾经目睹,因为他曾经受伤,因为他曾经就是一头花豹,所以在他的回忆里,历史是具象的,是现实的,是可触的,更是真实的,而马拉将“回忆是唯一真实的资产”这句话变成对整个文本解读的线索,是不是只是在嫁接他人的情感?是不是在虚构一种苦难?是不是在引用一种历史?
不得不承认,马拉在构筑这个封闭历史的时候,创作中的“卡带结构”是一种创新,打破线性叙事模式,也是他所追求的一种风格,关键是在文本的构建中,显出了他对政治、人性、战争审视的宏大视角。从一九三七年圣彼得堡的地窖开始,一段苦难的历史就此打开了口子,从沃斯卡成为异议分子被逮捕被审判,到罗曼审查画作被污蔑,以“花豹”为开局并不只是讲述兄弟间的故事,“花豹”所映射的是一代人的命运,或者那个神学院的学生并非是在幻觉里,狱卒的话也许也是一个骗局,而最后“里面只关了你一个人”甚至是一种更大的阴谋论——否则为什么二〇一三在圣彼得堡又举办了和罗曼有关的画展,他把沃斯卡嵌入画中的那些照片和画作不是最后还是公布于众了吗?“花豹”为开始,其实是一个政治权力扼杀信仰、人性的悲剧性历史的开端:散布“天堂之门等着为我们敞开”受到了审判,他们被定性为宗教激进主义者;罗曼在地下隧道修复画作,要将一个格罗尼兹的领导人画入油画的前景中,这是对历史、艺术的篡改,是对政治的讨好;因为有关芭蕾舞优伶的画作中出现了挥动的那只手,罗曼被举报、被审查之后入狱,因为他们怀疑他和波兰间谍有关,在莫须有的罪名中,罗曼学习了波兰语,最后被定罪……马拉在《花豹》中,给出了对应于纳博科夫那句引语的话:“历史是个我们始终动手修正的错误。”
而历史在马拉看来,需要不断进行修正,而真正害怕的是经过不断修正,它最终指向的却是可怕的、致命的错误。普尤特·札哈洛夫评论自己一八四三年的画作《午后的空旷牧野》是:“那是一幅次选之作。”而在修正的错误中,历史也便成了“次选之作”。从罗曼和芭蕾舞优伶的“故事”引向了“一九三七年至二〇一三年”的基洛夫格勒,一九三七年有关的历史和葛丽娜的外婆有关,而她就是那个被画在画作上芭蕾舞优伶的原型,因为卷入波兰地下运动组织被逮捕,在劳改营即将被获释前夕,警卫们听到了“隐约挣扎、一声尖叫、衣衫撕扯破裂”的声音,最终劳改营的营长成为了葛丽娜的外公。葛丽娜是这个政治犯和权力拥有者的“外孙女”,出生于一九七六年的葛丽娜开始了一段和自己有关的历史,她和科里亚恋爱,在囤积了冶炼厂毒性废水的人工湖泊边散步,最后坐上了富豪欧列格·沃洛诺夫那部镍银色的奔驰轿车,而排名全国第十四富豪的欧列格·沃洛诺夫利用向外国投资客、贪官污吏、黑帮老大筹募的资金,买下采矿集团大部分股权。
在基洛夫格勒,还发生了“身边种种晦气的事件”,比如莉迪亚的母亲薇拉,因为妈妈在一九三七年的时候拿了面粉做面点,竟被莉迪亚举报,根据官方的版本,薇拉目睹她妈妈闯入军需处的福利社,带着一百公斤面粉和一个塞了十二只活鸡的布袋潜逃。她的举报被《真理报》赞扬,一位委员听了之后回答:“国家和人民虽为一体两面,但你是两方的英雄。”薇拉成为英雄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但是后来,她的生活越来越糟,在朋友介绍下,在老家基洛夫斯克替贩毒集团工作;女儿莉迪亚透过网络远嫁美国,但是随后被遣返,却不幸撞见帮派贩毒,“刹那之间,她再也无法思考,再也无法反省,只能任由她的鼻息随着子弹飘出她的躯体。”当然还有葛丽娜曾经的恋人科里亚,他在昔日恋人拍电影、上电视、获得各种演出机会的风光之时,却在战争一线,一九九五年科里亚头一次被派遣到车臣,二〇〇〇年他以佣兵的身份重返此地,最后,在车臣一个埋了地雷的山坡播种莳萝,度过一生最后的时刻;还有格罗兹尼乡土博物馆副馆长兰斯兰,一直守护着车臣古画,但是在家乡妻女因误触地雷而亡,娜迪亚,是一名文物修复师,因战火失去了右眼视力,受鲁斯兰邀请,修复古画……
在这部马拉所构筑的历史中,政治腐败、工业污染、机械化对劳工的碾压、边境战争、黑帮毒品不一而足,个体在这样的历史中变成了一只只的花豹,但是将这些历史串联起来的并不是时间和空间,而是那幅“次选之作”的画,它辗转在不同人手上,它被抹除和添加中得到“修复”,它见证了历史,而最后,它并非是要回归“原作”,“山坡之上,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沐浴在渐渐西沉的橙黄光影。那株黄杏树、那道石墙、那座香草作物花园,那两个在山坡上的人影,跟画中一模一样。”这是不是对于“次选之作”的最后突破?或者这种充满了温馨氛围的修正正是对历史的一种态度?从“花豹”开始的历史,马拉将个体的无力放在了宏大叙事中,但是他就像对待存于历史的画作一样,最后完成了修改:最后一章是《终曲》,不再有一九三七、二〇〇〇、二〇一三等时间的标注,也没有圣彼得堡、基洛夫格勒、格罗兹尼等地名,“外太空,年代不明”完全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组成的历史,它飘逸在历史之外,死去的科里亚复活,坐在太空舱里,听着弟弟艾列克赛录制的卡带,呼唤着艾列克赛的名字,除此之外,还有手中的莳萝种子,还有葛丽娜唱起的《胡桃钳夹子》……
“终曲”就是对历史封闭论的一次彻底解构?外太空就是对历史存在论的一种超越,但是这个外太空计划并非只是一种浪漫的虚构,这是科里亚父亲的一个计划,当初提出这个计划就是因为当核战争导致末日来临,那么世界上最后一个活着的人将是俄国公民,“他将高高在上,翱翔于外太空。”从父辈的计划变成科里亚的现实,历史当然不再成为主宰,但是为什么在末日降临的时候,最后活着的人、高高在上的人会是俄国公民?马拉的“终曲”是不是在讽刺一种沙文主义?正是在这种沙文主义中,“终曲”不是逃逸,而是继续,外太空不是为诺亚方舟而建造,而是真正的末日,“我们已一无所有,我的末日将至。”于是站在那片大地之外的马拉,站在历史之外的马拉,又残忍地设置了一个难以逃离的历史循环:“从头到尾再播一次。从头开始。让我如愿。拜托。”
我们永远无法生活在“午后的空旷牧野”,我们永远是铁栏后面的花豹。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0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