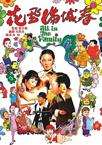2024-12-25《花飞满城春》:喜迎新春“抖包袱”

1975年,沈殿霞28岁,她扮演了胖妞,在对子铺里想要偷东西被胡万年的老鼠夹夹住了手,留下了没有结婚哪来的孩子的疑问,为第一个故事的“戏中戏”引入了关于孝的话题;1975年,洪金宝23岁,在“花飞满城春”的喜庆音乐中出场,拉黄包车的他完全是炮龙套的;1975年,成龙21岁,那时的他还不叫“成龙”,还是单眼皮,但是在跳出车把的演绎中展现了他的身手,更重要的是作为第二个故事中“小唐”的扮演者,成龙不仅在电影中露了点,还左抱右拥,既有处女身的玲子,又有风骚的老板娘,最后弄得腰酸背痛,还在“花柳”广告前徘徊。
28岁的沈殿霞、23岁的洪金宝和21岁的成龙,在1975年的《花飞满城春》中“现身”,而这部由朱牧导演的电影,编剧注明是“司马克”,他就是李翰祥,改名的李翰祥不仅从台前的导演变成了幕后的编剧,电影的拍摄投资方也由邵氏变成了嘉宝,但是电影依然延续了李翰祥擅长的市井风月路线,但是这部电影更是一种应景:它在1975年2月8日上映,农历是腊月廿八,也就是说这天距离中国传统春节还有两天,电影完全是为了香港春节市场而制作——开场和结尾的动画造型中有中国生肖兔,喜庆、吉祥是主基调,配上满满中国风的“花飞满城春”歌曲,在这个意义上,这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贺岁片”。
既然是贺岁,喜庆就是主调,好笑就是效果,快乐就是目标,电影开场的鞭炮、舞狮的环境烘托,对对子、数来宝、俏皮话的运用,都营造了节日的喜庆气氛,而李翰祥在片中设置的各种桥段就取材于中国传统相声——刘宝瑞的《化蜡扦》,他将这一切元素结合起来,变成了电影版的“抖包袱”:胖妞开场后让同行的男人和胡万年对对子,一个字一个字地对,结果“上大人”就对成了“下小狗”;胡万年想象自己年老患病,面对三个儿子伸出一个手指指着东房,当儿子们问是不是东房里有股票、存折,胡万年却说东房没人为什么点着灯?这活脱脱就是《儒林外史》严监生的形象?而一句“能源缺乏”又和香港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胡万年夫妻省吃俭用变成了苛刻,挂着的咸菜变成了“望梅止渴”;三个儿子为了得到母亲身上的元宝,从一开始让母亲吃窝窝头、铁蚕豆,到百般讨好,竟然说出了“孝敬是权利”,最后母亲去世,三个人争论时小儿子说:“她死在我的档期……”
| 导演: 朱牧 |
从中国传统相声中取材,又加以改编,结合了香港当下的生活元素和习惯表达,这部电影也完全是笑话、段子的集合。而在主题上,第一个故事具有很强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子,那就是孝,只不过朱牧和李翰祥运用了讽刺的手法,甚至充满了夸张性的表达,胡万年在临死前问三个儿子如何办理葬礼,大儿子和二儿子说起了如何设灵如何抬棺,都被吝啬的胡万年否定了,三儿子却说出了自己的计划,不仅不花钱,而且还赚钱,那就是把尸体一块块切下来,然后拿到东市去卖,胡万年当即表示反对,不是因为小儿子天理难受切割尸体赚钱,而是认为卖肉的地方不对,“要拿到南市去卖,东市不给现钱。”老爷子一辈子是守财奴,三个儿子当然继承了这一特点,而第二次想象中,王莱扮演的胡妻就利用三个儿子的这种心态,和女儿设计了假元宝的计谋,三个儿子为争取孝敬的权利,讨好母亲,最后才知道上了母亲和妹妹的当,由此也讽刺了“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
如果说第一个故事还有主题性意义,那么第二个故事就缺少了道德劝诫和讽刺的意义,叙事上破碎,情节上也几乎是拼凑,而且涉及的也是市井风月、赌博:河南逃荒者“元宵买粽子”走投无路,最后看中了彩票;车行老板即使妻子和小唐乱搞,也不当回事,只要自己能中彩票就行,“谁也别拦着我!”玲子的父母要将她卖身给老头,玲子故意用了红鸡蛋染液制造破处,老头有怀疑似乎也并未真正起疑心;玲子父亲中了七十多块彩票,不管女儿大手一挥:“都喝酒去,我请客!”如此,电影也呈现了众生相,只不过在风月、赌场的情节设计上,除了有点好笑也并非其他。
讽刺也好,展现也罢,当然,贺岁的目的就是博人一笑,而香港电影很长一段时期内,这种娱乐化的电影占据了市场主流,注重戏剧性、感官性也造就了七十年代“拳头与枕头”的故事风格类型。

《花飞满城春》电影海报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