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6-08《反叛的戏剧》:造就了现代戏剧的辩证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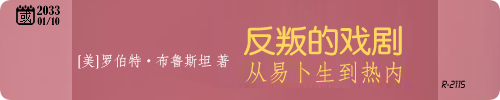
祭司把镜子转而对准那些还傻坐在碎石上的人。他们看着镜中的自己,神情痛苦地定在原地;然后,恐惧袭来,他们跑开,用石头狠狠掷向祭坛,气急败坏地诅咒祭司。祭司在愤怒、脆弱和讥讽下颤抖,同时将镜子转向虚无。他身处虚无,孤身一人。
——《反叛的戏剧》
在这个寓言之前,还有另一个寓言:在露天神庙里,大祭司以献身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表演,他身上的鲜血从祭坛上喷涌而出,观众们开始惊叫,然后神庙开始倒塌,城市开始解体,星球脱离自己的轨道……但是在灾难迫在眉睫的时候,画面却静止了,观众们虽然又不安的情绪,但是他们还是按照次序陆续立场。两个寓言放置在一起,罗伯特·布鲁斯坦的用意是明显的,他以并置的方式解读着教会戏剧和反叛戏剧的本质区别:在教会戏剧中,大祭司的献身,鲜血的喷涌,神庙的倒塌,城市的解体,以及星球的失控,带来的就是一种灾难,但是“画面静止了”,灾难被定格,所有的一切都呈现为一种“画面”之内的景观,观众们惊叫、不安、距离灾难一步之遥,但还是在难以言喻的宁静中走出了神庙,走出了舞台。
灾难并没有真正发生,灾难本身就是一出戏剧,“罔顾不断变化的世界在信徒面前上演老套的故事。”但是反叛的戏剧却不同,“反叛的戏剧是一座庙宇,这座荒诞的建筑模样丑陋,在这之中履行职务的祭司不信上帝、缺少教义,也没有多少信徒。”但是大祭司是存在的,而且他是“表里不一的传教士”,他散播着叛逆的福音,他试图用自己的理念取代传统的价值观,想从莉痛苦和挫败中自创一套仪式,大祭司具有的反叛性就在于他的有一面镜子,镜子就是戏剧大师创作的戏剧,这面镜子尽管也是一种画面的展现,但是它不是静止的,也永远不会被定格,它在大祭司的手中呈现出不同的景观:当这种反叛是救世性反叛的时候,戏剧家们反抗上帝的同时让自己取而代之,所以祭司看见了镜子中自己的形象;当反叛变成社会性反叛的时候,戏剧家们反抗的是传统、道德和社会价值,祭司就把镜子对准了观众;而在存在主义反叛中,戏剧家们所反抗的是自己的存在状态,祭司就把镜子对准了虚无,虚无的世界里它也是孤身一人。
救世性反叛、社会性反叛、存在主义反叛,这是布鲁斯坦对反叛戏剧划分的不同种类——他的“存在主义”采用的并不是哲学流派的定义,而是出现于17世纪晚期更中性的原始意义,存在主义就是“有关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不如将存在主义反叛说成是“存在性反叛”。布鲁斯坦认为,救世性反叛是现代戏剧的初级阶段,它是反叛戏剧中最主观、最宏大也是最自负的戏剧,当尼采说“上帝死了”,反叛而救世的主人就变成了超人,它是来自神话和宗教的的伟大反叛者:路西法、梅菲斯托费雷斯、该隐、犹大、唐璜等,他们是法外之徒,寻找着超越传统法则的满足感;而社会性反叛以现实主义的虚构风格形成了对英雄的“低模仿”类型,“英雄是我们中的一员,我们同他身上的普遍人性产生共鸣,并以我们所体验的可然律来要求诗人。”而存在主义反叛则是反叛戏剧的最后阶段,如果说救世性反叛是强力而积极的塑造着超人,那么存在主义则是在绝望中塑造了低人一等的人,他们憎恨现在,他们恐惧未来,所以他们退回到过去,而且他们把存在本身也作为了反叛的来源和目标。
从救世性反叛的积极态度,到社会性反叛在人性中寻找共鸣,再到存在主义反叛对存在本身的反叛,布鲁斯坦的这一划分正是在对神、英雄和人的三种反叛,无论哪种反叛,一方面都是浪漫主义的一种表达,另一方面都和尼采的影响有关,“当尼采宣布上帝死亡时,他也宣布了一切传统价值观的死亡。”这其实就是教会戏剧传统被解构的隐喻,所以当大写的上帝死去,反叛意味着一种虚无主义,而“超人意志”就构成了反叛的另一种动力,反叛戏剧家接过了尼采的挑战,在戏剧世界里以抗拒的姿态对抗着现代必然性的法则。从教会戏剧走向反叛戏剧,而且反叛被布鲁斯坦看做是现代戏剧最主要的基因,那么反叛是解构意义的还是再造上帝意义上的建构?
首先从对反叛戏剧的划分来看,布鲁斯坦将其看成是一种具有内在承续性的阶段,对神、英雄和人的反叛就构成了这三部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所举例的那个寓言就需要进行修正:当祭司用镜子实现一种反叛,那么在救世性反叛阶段,他在镜子中看到的就不应该是自己,而是一个死去的上帝,或者说,他的那面镜子已经是被打碎的镜子;在社会性反叛中,他把镜子对准观众,而观众所代表的正是社会的规则,在对准观众的同时,镜子说形成的镜像就是社会景观的反面;而在最后,镜子里显出的才是那个虚无的存在世界。从打破镜子到审视观众再到显现虚无,这代表着反叛的三个阶段,但是关键问题是,祭司还在,镜子还在,这样一种存在是不是意味着反叛是不彻底的?布鲁斯坦也承认,戏剧家创作反叛戏剧,目的是不断探索自己人格的可能性,不管是表现还是劝诫,不管是演绎他人还是审视自己,都带着浪漫主义的特色,都是尼采非理性的表现,所以,“现代戏剧没有同传统形成彻底的决裂。”
| 编号:X14·2250424·2297 |
另一方面,三个阶段是被布鲁斯坦分期的,但是戏剧家并不只是单纯属于其中的一个阶段,他把易卜生和斯特林堡大致划为救世性反叛,契诃夫和萧伯纳则主要属于社会性反叛,阿尔托和热内属于存在主义反判,但是这种划分并不绝对,易卜生就跨越了反叛的全部三种类型,萧伯纳偶尔也会进入存在主义反叛的领域——布鲁斯坦只是为了解说将反叛戏剧分类,但是没有将戏剧家们进行武断地归类。从这一方面来说,这种解读是科学的,但是这里出现的问题是,这种划分来阐述反叛戏剧是不是会陷入一种泛化的问题里?实际上,当戏剧在现代哲学、科学的转向中进入现代时期,它不可避免地会告别传统的戏剧,不管是所谓的教会戏剧还是非教会戏剧,都在时代的发展中面临重新洗牌,在这个意义上,所有具有现代性的戏剧都可以视为反叛戏剧,而布鲁斯坦所选择的八位戏剧大家也只不过是他掺杂着更多个人喜好的结果。
在《序言》中布鲁斯坦将自己的这一工作看成是有着雄心勃勃的意图,正因此,“无疑是有点冒昧的。”这种冒昧性一方面体现在他把“反叛”统一盖在了戏剧活动之上,“正是这一戏剧活动,通过共同理想和共同目标将最重要的现代戏剧家们联系在了一起。”另一方面,联系在一起的八位作家真的客观代表了反叛戏剧的最大集成者?1990年这本书进行在再版,从初版到再版,经过了25年,“这25年里戏剧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布鲁斯坦25年后再次审视这项雄心勃勃但有点冒昧的工作,显然对于最初的选择有了新的看法,尤其在对戏剧家的选择上,在25年前他说贝克特还不够成熟,还没有完成“足够多样的剧作体裁”的剧作家,但现在发现这是一个“重大的疏漏”,“我很遗憾没有为他单独开辟一章。”同时他认为如果可以重写还必须再加上一章,那就是对“后奥尼尔时代”的美国剧作家进行阐述,包括大卫·马梅特、山姆·谢泼德、大卫·拉贝,以及颇有远见的导演罗伯特·威尔逊,而按照这个逻辑,还应该有后萧伯纳、后布莱希特、后皮兰德娄、后契诃夫的戏剧家……
“再版”的说明其实是对25年前所说的“冒昧”的修正,在这个意义上也正是因为反叛戏剧本身就是现代戏剧的共同特性,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一种反叛精神。一方面选择八位戏剧家作为成熟的代表人物,是对于反叛精神的一种窄化处理,而另一方面,当反叛成为现代性的一个本质标记,布鲁斯坦论述的这八位代表性戏剧家是不是又被泛化了?这和他划分为三种类型的标准一样,尤其是其中的社会性反叛是不是真的具有反叛性?反叛是李尔王口中不断重复的“不要”“没有”“绝不”,它是否定 ,是抗拒,是革命,是解构,甚至是对反叛自身的反叛,这种反叛之反叛构成的就是否定之否定,“当反叛的戏剧家把反叛作为自己的中心命题时,他也以现实的名义批判反叛;他把自己和反叛的角色同化时,他也否定了他们。”在布鲁斯坦看来,反叛的意义就是体现了一种辩证法,它是思想和行动的冲突,是理念和实践的矛盾,是解构和建构的互逆,“造就了现代戏剧的辩证核心。”但是社会性反叛真的是一种基于和传统决裂的否定?
在布鲁斯坦所选择的八位戏剧家中,易卜生和斯特林堡是最具颠覆性和革命性的反叛者:易卜生以个人主义反抗着一切的社会秩序,国家、社会、教会以及家庭都被他看作是自由的敌人,“易卜生主义真正的精髓在于反抗一切确立的秩序,他要破除的旧习不仅包括他那个时代的制度,还延伸到了他自己的信仰和主张。”在他的第一部戏剧《布朗德》中,易卜生用反叛寻找内心释放的出口,在《群鬼》中,易卜生认为进步观点的重要性和无用性,《罗斯莫庄》中,他对人提升自我的可能性既憧憬又绝望,在《玩偶之家》中,他猛烈地抨击构筑在谎言上的婚姻,而在《野鸭》中,他保守地表示在某些情况下,国民的愚蠢完全是生存所必需。1869年,41岁的易卜生在《致我的朋友,革命演说家》的短诗中宣告了自己的革命:“我很愿意凿穿方舟!”而在《群鬼》中他在笔记中写道:“整个人类都走上了歪路。”从革命到绝望,易卜生一直没有改变反叛的本质,而当他在《建筑大师》中描写了感到绝望的反叛者,反叛在他那里也成为了反叛的目标,“易卜生在这30年间都在同心灵和思想上的怪物英勇搏斗,反抗一切限制个人自由的世俗势力和神权势力。”
和易卜生相比,斯特林堡更显偏执和极端,这首先就表现在他的人生经历上,分析斯特林堡的个人生活,布鲁斯坦认为他的童年是典型的恋母模式,所以他仇视强大的父亲;但是他的恋母又是矛盾的,他把母亲称为“灵魂的乱伦”,并在戏剧中将母亲塑造成纯洁的圣母和淫荡的妖妇,就像在《到大马士革去》里写道的那样,“在女人身上我寻找能借我翅膀的天使,而我却落入世俗的臂弯,她用塞满翅膀羽毛的被褥使我窒息!我寻找埃里厄尔却只找到凯列班,我想要飞升时她拖我下降,而且总让我想起我的坠落……”斯特林堡患有严重的偏执症,他对迫害的恐惧和对崇高的幻想交替出现;这种偏执让他走向了“恶魔崇拜”,他练习巫术,他崇拜神秘,他研究转世,他的身上留下了硫磺的严重烧伤,而他把自己看做是和魔鬼定立了契约、效忠路西法的叛逆者。所以他的冲突心里、偏执性格、恶魔崇拜都投射在反叛戏剧的创作中,可以说,反叛戏剧也构成了斯特林堡的性格文本,他借《到大马士革去》的无名氏之口决心“废止现行的秩序,要粉碎它”,想象自己是“毁灭者、瓦解者、煽动世界之人”。最后他又用自己的死证实了反叛者自身的悲剧,死前抱着《圣经》喃喃自语着“万物皆可赎罪”。
虽然易卜生和斯特林堡个人经历和戏剧作品都是极为丰富和多样的,但布鲁斯坦还是将他们看做是救世性反叛的代表,他们举起镜子最终砸碎了它,也砸碎了镜子中的自己。布鲁斯坦认为社会性反叛的代表是契诃夫和萧伯纳,但是他们的反叛与其说是否定和颠覆意义上,不如说是在批判意义上的。契诃夫也在反对秩序,也在否定现实,但是他摒弃的是个人主张,他的反叛没有指向性,他以温和、客观和冷静的方式,是在批判当时的俄国社会,“他的反叛有两种形式,一是针对人物,二是针对环境,或者说制约人物的力量。”而恰恰是一种批判,所以它反而是一种建构,就连布鲁斯坦也承认,“他的的戏剧表面上透着对人生的厌倦和精神的空虚,内里却充满了活力和反抗。”这种反抗的活力就成为了契诃夫的参与观,“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只能出于反抗政治的需要,才能参与政治中”。同样,作为清教主义者的萧伯纳,他坚持着革命信条,不是为了彻底否定和颠覆,而是成为革命的撰稿人,甚至鼓吹政治、道德、艺术和宗教上的改革,“萧伯纳是不能赞同想象的不可能论的政治不可能论者,他总是要把理想上的反叛转变为社会行动。”这种行动的表现就是决定进化的生命力,就是解决社会道德问题的超人。
契诃夫和萧伯纳都是在反叛中希冀找到一条构建的道路,所以本身反叛就是不彻底的,而且反叛只是形式而已目的就是更积极地行动,在这个意义上,布鲁斯坦将他们看做是社会性反叛的代表,把社会性反叛的批判看作是一种反叛,这就是对现代性的反叛精神的一种误读。而反观存在主义反叛,救世性反叛的种种特质似乎又回来了,而且呈现为另一种不同的反叛,那就是把镜子对准了虚无的世界和虚无本身,并在对镜之中阐释了反叛本身的辩证法:“他一半是圣僧,一半是红尘中人;他一半是道德家,一半是恶德者;他一半是狂热的理想主义者,一半是冷嘲热讽的绥靖主义者。”布莱希特是不同身份的混合体,他的戏剧在间离的伟大创造中被演绎,他的思想在理性的非理性中走向形而上学;皮兰德娄把一切都看成是面具,把存在看成是罪恶,把生命看成是悲剧,他强烈反对一切社会体制的形式,极度鄙视乌托邦理想和乌托邦理想主义者,他连自己也否定了,“作为一个人,我想要告诉其他人,我一心想要报复自己的降生。”奥尼尔把上帝看作是物,它是《发电机》中的涡轮机,是《奇异的插曲》中的“电气表演”,是《泉》中的生物遗传,“他仿佛一个羸弱无力的人,因为见不得阳光而紧闭门窗,从他那饱受痛苦和磨难的自我中诞生出了伟大的反叛戏剧。”
安托南·阿尔托的生活是疯狂、混乱甚至病态的,他一生都受到精神疾病的折磨;让·热内是声名狼藉的同性恋和小偷,他是主流世界之外的底层存在,但是阿尔托和热内却在“残酷戏剧”里演绎着最具存在主义意义的反叛,“一切真正的文化都要依靠野蛮、原始的图腾崇拜,我所推崇的正是这种荒蛮,或者说完全自发的生命力。”阿尔托这样说,他像创造的是超现实主义的神话剧场,虽然也是一种创造,但创造的本质是在反叛中激发否定的力量,他把戏剧看成是酒神狂欢,甚至看成是瘟疫,“我提倡残酷戏剧……我们是不自由的,天是会塌的,戏剧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件事。”让·热内在这种残酷戏剧中把犯罪看成是生命的典范,把神圣性确定为自己的目标,但却是在反叛意义上的,““我要歌颂谋杀,因为我爱杀人犯””在某种程度上,在存在主义反叛中,反叛指向了救世主,只不过这不是大写的神,也不是英雄,而是原始的张力、自我意识、本能的反叛者,用阿尔托的话来说,就是让我们看上去“像是那些被活活烧死的殉道者,在火柴堆中发出求救的信号”。
反叛或者仅仅是反叛的态度,反叛的宣言,反叛的精神,它并不指向对社会在实践意义上的建构,更不是不予真正反叛的参与和行动——社会性反叛充其量就是在批判中拨开社会的问题和道德的虚伪。所以反叛的本质是打破既成的规则,解构现有的秩序,否定行动主义和道德力量,反叛就是一种辩证法,“它最终将会带来难以调和的紧张对立和不作为,以及从美好、纯粹的真相中产生的形而上的愉悦。”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