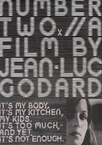2025-07-15《第二号》:“后进式”的身体叙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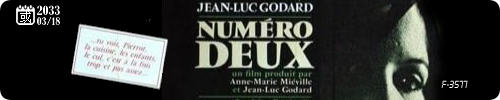
在观影了让-吕克·戈达尔的“75面体”之后,依然会发现被潜藏在那里属于戈达尔的影像序列:1975年的《第二号》就是其中之一,一种以为的完成却是在未完成中打开更大的世界,而当在50年后再次返回到戈达尔的影像文本,这种“再发现”是不是构成了观影的“第二号”?无疑,“第二号”总是相对于“第一号”而言的,甚至“第二号”的前面是永远被标注为唯一的文本,它不具有“第一号”而和“第二号”的区分,也正是有“第二号”的存在,唯一的文本成为了这个序列中的“第一号”。
“第一号”是唯一的,是源初的,相对于“第一号”的“第二号”则是次生的,当“第二号”成为又一个文本,“第一号”必然进入到被分化的行列,当“第二号”无可避免地出现,“第一号”唯一的、源初的地位再无存在的可能。“从前有一个图像,从前有两个图像,从前有两个声音,从前的从前只有一个声音……”这可以看做是对第一号和第二号关系的阐述,“从前”是第一号的时间标签,它只有一个图像,但是“第二号”让从前不再只有一个图像,于是第一号就变成了“从前的从前”,它以无限后退的方式保持着“从前”的原始时间,但是这种无限后退已经再无法回到“第一号”的情景中,“我们说曾经有那么一次,为什么不说曾经有那么两次?”
曾经两次是对曾经一次的篡改,从前的从前又是对从前的维护,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曾经还是从前,都发生了一种变异,“从前有两个声音:第一号和第二号。”那么当第二号像一个幽灵缠绕着第一号并分化和解构了第一号,“那么一次”还会像它应有和必然的样子那样,指向了一个真实的、确切的、只发生一次的“那”?实际上,在“第二号”里,一切都变成了不可更改且在场的“这”:这里是现实,这里是生活,这里是电影,这里是戈达尔的“第二号”。作为戈达尔结束维尔托夫小组之后的第一部电影,也是和安娜-玛丽·米埃维尔的首次合作电影,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第二号”的存在?纪录片和剧情片的混杂结构是戈达尔叙事的一次实验,不妨从这种混杂结构切入,从后半段的剧情来展开对“第二号”属性的分析:这是一个关于“这”的怎样故事?
| 导演: 让-吕克·戈达尔 |
“这”是一个家庭的故事,三代人组成的家庭:女儿瓦妮莎和儿子尼古拉,他们或者在黑板上写着板书,或者阅读大笨狼的故事,这是一种童年的生活,甚至是不受污染的纯真时代,但是在“这”样的家庭里,他们所见所闻构成了理论构想之外的“第二号”生活;“他爱她,她没去监狱看他,反而为了赏金,她向他的腿部开了五枪,可是他还爱着他……”尼古拉阅读的故事不再是大笨狼,而是一个他和她变异的爱情故事,“这”样的生活已经开始了分化,而瓦妮莎甚至开始询问母亲一个隐秘的问题:“长大后双腿间会有血吗?”尼古拉和瓦妮莎正在成长,孩童的成人化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尼古拉和瓦妮莎的父亲皮埃尔在工厂里上班,母亲桑德琳大部分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在孩子面前,母亲的身体总是处在半隐半现的“半裸露”状态,甚至在给瓦妮莎洗澡时,镜头完全呈现了小女孩的隐私部位,这是一种无遮的纯洁?还是对道德的挑衅?这个问题似乎在桑德琳和皮埃尔的性关系中得到了解答。
卫生间被堵了,皮埃尔非常生气,他直接掏出阳具将小便撒在盥洗器具上,桑德琳站在一旁,然后伸出手去抚摸他,但是皮埃尔说了一句:“我有时硬不起来了。”本来这是一个夫妻表达欲望的动作,但是在皮埃尔硬不起来的现状面前,也许性生活就像被堵的卫生间,也许阳具就只是小便的工具一样,它们在功能意义上都变成了取消“第一号”的“第二号”,而在被取消了“第一号”的性爱之后,“第二号”就演变为一种复杂的行为:一方面他们还是在做爱,皮埃尔用后进的方式插入了桑德琳的身体,是一种夫妻间的性行为,但是后进便表现为一种机械式的运动,在功能不健全的男性世界里,它甚至只是一种习惯;而另一个方面才是最关键的,皮埃尔说从后面插入,他看到的就只有桑德琳的屁股,“我喜欢看不见的部分”,看不见的部分在别处,它就是第一号之外的“第二号”,是遮蔽,是分化,是不可见,甚至是对夫妻面对面性爱抚的取消,但是皮埃尔说“喜欢”,这似乎构成了一种悖论:正因为看不见而喜欢,家庭生活的“第二号”就构成了爱之外的性,而这种性在不可见的地方发生,在硬不起来的状态中插入,它构成的不是愉悦,而是暴力,“像河流,暴力淹没了土地。”
这是关于男人和女人性叙事的隐喻,它在一种被称为看不见的“身后”发生,它在取消了爱抚的暴力中上演,“我想强奸她。”皮埃尔这样说,这种“第二号”的后进式性生活其实就构成了一种暴力,但是男性成为暴力的施事者,那么作为同样看不见身后的女性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桑德琳总是在抱怨,两个人总是在争吵,甚至面对这样的性生活,她也总是避开,她被皮埃尔看见的是自己的屁股,这是身体局部和性生活异化的隐喻,所以她坐在那里抱怨说自己已经好多天拉不出屎了,甚至直接说“我就是屎”,和屁股有关,和病态的功能有关,而这种抱怨、愤懑甚至讽刺就变成了和男性的暴力相抗衡的堕落,而在孩子面前无遮拦地呈现身体的一部分,甚至让孩子在场的方式传授性知识,是不是也是一种教育意义上的“第二号”?后面和前面,可见和不可见,硬不起来和要完成的插入,以及暴力和堕落,构成了“第二号”对第一号完全的分化和解构,它以必然发生的发生成为了“这样”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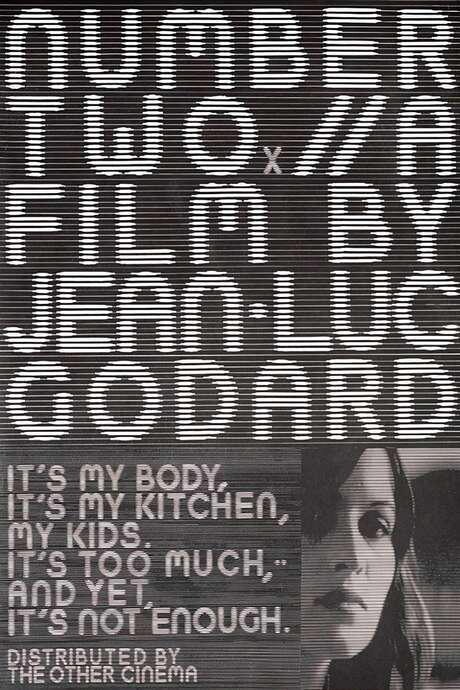
《第二号》电影海报
也从这个关于家庭的故事为出发点,戈达尔构建了他的政治叙事:皮埃尔在工厂上班,工作对于他来说就是为了赚钱,它取消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属性而变成赚钱的机器,与其说皮埃尔在性生活中丧失了功能,不如是他失去了工人阶级的地位,所以他只有通过暴力的方式“插入”,这种后进式的插入对桑德琳来说就变成了屁股式的堕落,“当我们和一个男人合不来的时候,可以离开他,但是当国家和社会制度强奸我们时,该怎么做?”而这个关于暴力和堕落的政治隐喻在上一代中更为明显体现出来,老父亲回忆自己作为革命者的经历,在墨西哥举行了婚礼,夫妻都是激进分子,后来回到了法国,经历了战争,加入了共产党,在工厂工会当了30年领导,但是现在老父亲也是呈现出和皮埃尔一样“硬不起来”的现实,他的这种革命命运也和暴力和堕落有关:当工厂生产武器,武器是大炮、坦克,却也可能用来对付妇女和孩子;当工人阶级通过罢工争取自己的权益,现在则变成了一种沉默……“看看我的老二……”在正襟危坐回忆自己的革命生涯时,老父亲的下身却裸露着,还不停摆弄着。
父亲和皮埃尔作为男性,已经在革命和后革命时代丧失了功能,而身为女性的桑德琳和母亲,则在暴力施予中变成了堕落,当暴力和堕落成为在场的“第二号”,真正的“第一号”永远在身后,永远不可见。而回到剧情之外的记录世界,戈达尔呈现出一个更为丰富样本的影像世界,但是这样的影像世界是电影,是现实,是故事?在形式意义上,戈达尔采用了黑屏中字母的变化来书写“标题”,用不同的分屏来演绎画面,这个三代人相关的故事被讲述,这就是一种嵌套式的屏幕,或者是一个关于“画框的画框”的形式表达:当电影本身构筑了一种封闭着的画框,当画框被分屏而呈现出不同位置的画框,“画框的画框”便不再是被看见,而是一种分化、变异的存在,它就是一种衍生的“第二号”,它就是不被看见的“第二号”,它就是充满暴力和堕落的“第二号”。而在本质上,戈达尔也解构了“电影”:他先是用廉价的录像带拍摄了剧情,然后用35mm的胶片拍摄监视器里的画面,在技术上这是“电影的电影”,在形式上这是“画框中的画框”,它不再让电影和画框保持它的源初性和唯一性,于是这个“第二号”就成为了对第一号进行解构的镜头。
电影变成镜头,“第二号”就变成了关于身体的一个游戏:“这不是左派右派的电影,这是身前与身后的电影。”身前站着一个孩子,身前是对孩子的教育;身前也站着自己的妻子,身前是面对面的爱;身前是工人阶级,是革命,是革命的电影。而身后呢?身后是屁股,是机械式插入,是暴力的政府,是赚钱的工厂,是资本。身前和身后就这样构成了“第一号”和“第二号”的隐喻,“第二号”是被遮蔽的,是看不见的,是物化的,更是一部机器。于是,不再有图书馆里的图书,它在身后就是印刷厂;不再有文件,只有被朗读的他人话语,只有被发号施令的那张纸;不再有五一游行、罢工、工会,它们都是工厂的一部分;不再有电影,“影像”闪烁在屏幕上最后熄灭,监视器里的画面最后变成了雪花;也不再有熟悉的“那谁”,“他现在应该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工作,我想他最后会成为驻雅加达的领事,我们上次见到他时还是在图卢兹的示威活动中……”一切都过去了,在第二号的世界里,不再有“那谁”,只有成为物的机器,一部变成机器的电影,一部只为了钱的电影。
“我的手是操纵机器的机器,或者相反。”戈达尔站在监视器前自言自语,电影是机器,言说是机器,甚至身前和身后都变成了机器的一部分,而最后戈达尔竟靠在桌子上入睡了,监视器里的影像已经消失了,他也停止了言说,在完全呈现为机器的世界里,电影也不复存在,“《第二号》的特殊性在于:它是由电视构思、由电影包装的影片,它的独特性也是它的困境:衣服不适合孩子……严格来说,这甚至不是一部电影,而是被电影包装过的一些镜头……”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882]
思前:《福利》:非福利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