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7-18《化石》:悲观的“内在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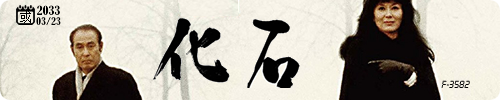
1975年之后,小林正树拍摄的电影包括1978年的《燃烧的秋天》、1983年的《东京审判》和1985年的《无餐桌之家》,《无餐桌之家》之后小林正树再没有拍过电影,也就是说,1975年的电影可以看作是小林正树“后期”的一次影像表达,在生命的最后30年,小林正树为什么对拍电影丧失了热情?当然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会有多长的长度,但是对电影的冷落和疏远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感受到了一种江郎才尽的无奈?无从知道答案,但是《化石》似乎提供了对小林正树解读的一个窗口,电影中的主角一鬼太治平正是在面对死亡时最后选择了成为“化石”。
“感觉自己变成了化石,铺满了不可思议的东西,就像面临黑暗却无法溶解。”这是电影在最后时一鬼的心理活动,当癌症手术顺利完成,医生木花告诉他可以活动八九十岁;当公司的债务危机逐渐化解,新提拔的下属也进入了正常轨道;当心念念的玛努斯夫人写信说从巴黎回到日本,要和他一起去看樱花……一切似乎都向好的方向发展,对于死亡似乎也开始变得通透,但是一鬼还是拒绝了陪伴玛努斯夫人,面对死亡他选择成为化石,而化石意味着放弃对生活的美好期望,意味着独自承受生活的变故,像化石一般被不可思议的东西占据,无声无息,像装饰墙壁的大理石,它走向一种不变的古老,宛如“妖精”的存在。
在得知自己患病而逐渐走向死亡的过程中,一鬼经历了许多,也感知了许多,死亡带来的生命感悟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内心体验”,但是为什么小林正树要让一鬼选择一种悲观的生活?悲观而压抑,这是整部电影的基调,在长达200分钟的电影里,小林正树采用了旁白的方式“讲述”一鬼的遭遇,这个他者的存在是一种故事叙述者的角色,其实对于这部电影来说,这个旁白基本上是多余,它制造的叙述和画面所呈现的故事不具有补充功能,和这部冗长的电影一样,旁白在很大程度上甚至破坏了一鬼对死亡的“内在体验”。如果说旁白是一种不需要介入而被言说的浪费,那么一鬼向往以及最后被构想的玛努斯夫人,则变成了另一个他者:她是一鬼陷入孤独、压抑和悲观时的抚慰者,是代表着一种和现实不同的美好存在,但是最后一鬼还是以拒绝的方式让她消失——这是不是他对那个“超我”的否定而回归到自我的一种努力?
| 导演: 小林正树 |
作为一家拥有2000名员工的建筑公司社长,一鬼的生活似乎都和工作有关,妻子去世之后两个女儿长大,终于有一天一鬼选择了欧洲之行,暂时放下工作意味着他要寻找属于自己的东西。因为寻找,正表达了一鬼内心的虚无,年轻的妻子早就去世,在飞机上他想起了她,但是越发感到孤独,到达巴黎之后,他似乎也对这里的异域风情无动于衷,后来去了意大利和西班牙,在西班牙女郎热情奔放的舞蹈面前,他甚至昏昏欲睡。但是这不是他心理上出现了问题,而是身体患病了,在商会举行的招待宴上,平时喜欢喝酒的一鬼却无欲望,身体总感觉到劳累,回房间想要休息竟然因为身体不适倒在了地板上。同行的下属部松给他安排去医院检查,在一鬼一再拒绝中终于上了检查台,而检查的结果是:他患上了胃癌,日本当地的一员对检查报告进行解读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即使手术成功,他的生命也只有一年的时间。
这无疑于晴天霹雳,宣布绝症就是宣布死亡,所以一鬼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陷入了常人的恐惧心态,因为死神在一步步走近,他开始感到绝望,甚至想到了自杀。这可以视为他对死亡的第一重态度,在这个严酷的现实面前,他没有办法逃避,但是一鬼却找到了安慰自己的一个人,她就是曾经出现过的玛努斯夫人:他和部松在散步时曾看见过她,玛努斯夫人看见他们也停下了脚步,一鬼感觉她就是一个日本女人,而且被她的眼神所捕获;后来在公园里再次看到了正在编织毛衣的玛努斯夫人,一鬼感觉到在这样的寒冬世界顾自做事“很美好”,所以他念念不忘;也许第一次相遇和第二次看见都是真实发生的事,后来在商会的宴会上,大家说起了玛努斯夫人,很巧合就是一鬼两次遇见的女人,这便像是一种幻觉了;后来玛努斯夫人在他感到不安时竟然来到了房间,这就完全变成了他自己的想象,而玛努斯夫人对他说的话也是:“我就是你的本身,我们是同路人。”
一鬼想象了另一个自己,这个自己是作为超我而存在的,尤其是在一鬼陷入死亡的绝望时:他受木史夫妇的邀请开启意大利之旅,而同行的人竟然又是玛努斯夫人,这就完全变成了被想象的存在,而这个被想象的自我就对死亡进行了“内在体验”:在一鬼把癌症的英语看成是“螃蟹”而吃掉了蟹肉,这是一种自我欺骗式的行动,它甚至不是对死亡的消除,而是强化,玛努斯夫人站在他面前,告诉他的是:“人的一生都会经历老死,这是自然规律,而且有人死去,也会有人出生。”玛努斯夫人的手上拿着一只小虫,她把小虫看做是赚钱的虫子,“即使它死了,也还会有新的生命降临。”把死亡看做是一种自然现象,这是一鬼创造的玛努斯对死亡的解读,而当他和木史夫妇参观了意大利的教堂,看见了教堂里的那些雕像,玛努斯问他有没有信仰,一鬼说:“只有痛苦是没有信仰的,不如通过喝酒忘掉痛苦。”而在面对曾经发生战争的布努哥平原,一鬼对木史说起了那些英雄之死,在这里,死亡成为了一种传奇,“他们的灵魂一直活着。”只有有信仰,有灵魂,死亡反而是一种活着的状态,这是他对死亡的第二种理解,比起自然规律的死亡来说,这又是一次超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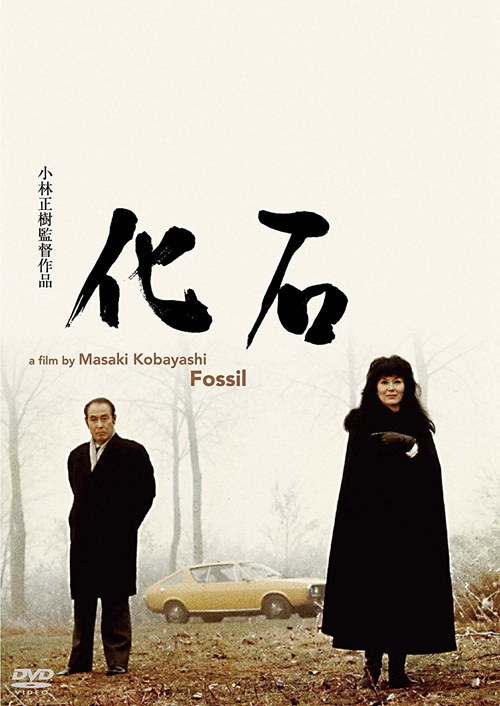
《化石》电影海报
在从欧洲回到日本之后,一鬼还是在公司里奔波,但是比起以前的忙碌状态,他也抽出时间安排自己的生活,他去了老家,和好久不见的继母一起聊天,这让他的弟弟大为惊讶,因为以前他和继母之间矛盾不断,为此他几乎不回家,这次一切都冰释前嫌,也许只有在面对自己的死亡时才会放下怨恨;他还去看望了同样身患癌症的朋友砂实,他没有告诉砂实自己的病情,而是从砂实对人生态度的转变中体会到了生命的意义,砂实说自己曾经吊儿郎当,没有做一个合格的夫妻,如果有来生的话,他一定要好好活着,努力做好自己。这是砂实的感悟,在一鬼伸出手深情握手时,砂实的这些话也是一鬼想对自己说的。日常生活矛盾的消融,自我的某种忏悔,都构成了一鬼对于生命的新感受,它们也成为了关于死亡却超越死亡的内在体验。死亡是一种自然现象,有灵魂的死亡是不灭的,生活中应该消除矛盾,要做真实的自己……这些都是一鬼在死亡面前获得的体验,是对人生和生命的一次深刻的感悟,如此,那个超我的玛努斯应该引领一鬼走向更富有意义的生命历程。
但是他最后选择的却是成为“化石”,不是像小虫子一样生死的轮回,不是像石雕一样拥有灵魂,也不是如砂实一样透彻了生命的意义——为什么化石是对死亡的唯一态度?化石是时间的沉淀,化石是固化的生命,化石是不生亦不灭的“妖精”,也许对于化石来说,生就是生,死也是生,这是一种不被衍化的存在,无法溶解的黑暗,而这不正是生命的本我状态?小林正树以一种莫名的方式转向了对死亡的另一种终极思考,像是放弃又像是坚持,像是否定又像是肯定,像是消极又像是积极,也许生命中“不可思议的事情”只有一鬼才能理解,也只有小林正树才能体会。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29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