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9-25《审美教育书简》:人只应同美游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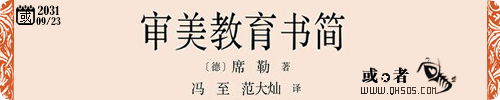
因此,人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或阶段:人在他的物质状态中只承受自然的支配,在审美状态中他摆脱了这种支配,在道德状态中他控制了这种支配。
——《第二十四封信》
席勒写给曾经在困难时期慷慨资助自己的丹麦奥古斯滕堡公爵一共写了27封信,除了对公爵的感激之外,作为收件人,席勒也将他看成是一种美的象征,他称公爵为“一个感到并且实施着美的全部权力的慧心人”,和他的通信自然变成了共同对“美的事物”的探讨——但实际上公爵没有回信,或者说回信部分并没有成为“审美教育书简”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创作审美教育书简更多成为席勒发表自己对美的看法的一种单向性的行为,而这种单向行为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在面对“必须根据感觉又必须根据原则的地方”,席勒将其作为自己工作中最艰难的部分,所以在第二封信里,席勒坦言:“我要是能同一个既是多才多智的思想家同时又是有自由思想的世界公民在一起来探讨这样一个对象,我要是能同一个怀着美好的热情献身于人类幸福的有感情的人一起做出判决,那对于我将会有多么大的吸引力!”
作为浪漫主义的旗手,作为狂飙突进运动的主将,席勒在面对古典主义的滥觞,也面对德国社会利己主义盛行的时代,勇敢站出来探寻美以及艺术的起源、艺术的本质问题,而他探讨美的重要理论依据则是康德的思想,“诚然,我不愿向您隐瞒,下边的看法大多是以康德的原则为依据”,尤其是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在他看来,实践理性所谈到的伦理学是“一般理性的至理名言与道德本能的事实”,席勒认为,道德本能就是“智慧的自然为监护人类而设置的”,它的目的就是让人类拥有明澈的认识,就是康德所认为的,人类发展的道路就是从被感性支配的自然状态过渡到走向精神能控制物质的理性状态。实际上在第二十四封信中,席勒就总结了人类的这条认识之路:从最初受到自然的支配,到逐步摆脱支配,并最后控制这种支配,这就是席勒所说从自然的物质形态走向理性的自由状态的必由之路,但是为什么从被支配到控制支配,人类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审美教育必然是第二阶段,也就是从自然到自由本质性改变的阶段?
在席勒的论述中 ,伦理意义上的道德也是精神,道德经验所适用的一切,在更高的程度上适用于美的现象,只不过道德世界的事务更多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而最完美的作品意味着道德世界抵达了“真正的政治自由”,在这里席勒其实已经指出了审美教育的最终目的,那就是自由,理想的艺术必须脱离现实,必须大胆超越,“因为,艺术是自由的女儿,她只能从精神的必然,而不能从物质的最低需求接受规条。”要达到这样的政治自由,就必须“借道美学问题”,也就是通过美才可以走向自由。自由的含义就是从物质的必然走向道德的必然,这是从人类之为人类发展的两端:自然是起点,自由是最高目标。但是从自然到自由并不是一条直线,理性也并不能完全脱离自然对人的支配和束缚,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理性还要从人身上夺走他实际占有的,仅仅是给他指出了“可能和应该占有的”,甚至为了人性,理性还会夺走“人获得兽性的手段”,而兽性又是人性的条件,“这样,人还没有来得及用自己意志握紧法则,理性就已经从人的脚下把自然的梯子撤走。”
这实际上反而变成了双重困难,一方面,理性如果把它的道德一体性带入物质社会,那么它就不可损伤自然的多样性,如果自然要在社会的道德结构中保持自己的多样性,也不可以破坏道德的一体性,那么这种完整性是不是就永远无法建立了?席勒认为,一个人的天禀和规定都是让自己成为一个纯粹的人、理想的人,他生活的任务就是在各种各样的变换之中同理想的人保持一致,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依靠“国家”,“这个在任何一个主体中都能或明或暗地看得到的纯粹的人,是由国家所代表,而国家竭力以客观的、可以说是标准的形式把各个主体的多样性统一成一体。”但是如果在民族性格里主观的人和客观的人水火不相容,那么国家只能压服主观的人才能使客观的人获胜,只能对公民绳之以法,甚至只能践踏敌对的个体。这里就凸显了一种国家理性带来的困境,在第五封信里,席勒就描绘了批判了这样一种建立在理性上的国家道德。
理性让偏见的威望倒地,揭开了专制的假面具,但是当人从长期的麻木不仁和自我欺骗中醒来,他渴望恢复人不可丧失的权利,但是当他只能用暴力夺取这些权利的时候,他就成为粗野和堕落的人,“解脱了羁绊的社会,不是向上驰入有机的生活,而是又堕入原始王国。”而从整个社会来看,当文明阶级显出一幅懒散和性格败坏的景象,出自文明本身的毛病会让人更为生厌。席勒在这里把这种问题归结为利己主义,“我们受到了社会的一切传染和一切疾苦,却没有同时产生一颗向着社会的心。我们使我们的自由判断屈从于社会上专断的偏见,使我们的情感服从社会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习俗,使我们的意志受社会的各种诱惑;我们坚持的只是我们的任性,以此来对抗社会的神圣权利。”席勒认为这是文明本身的问题,文明并没有将人类带入一个真正有道德、有信仰的世界,反而在偏见、诱惑和人性中失落,这就是席勒所说的自私,它当然丧失了人的天性。
自然以物质化的形态束缚了人,当人挣脱了自然却又陷入了文明带来的自私之中,从自然到自私,这就是理性战胜自然的一条错误之路,更不是我们需要的时代精神,所以在这里席勒指出了真正的时代命题:“一方面使它脱离自然的盲目暴力,一方面又使它回到自然的单纯、真实和丰富——这是一项要用一个多世纪时间的任务。”在这里,席勒提出了完成这一时代命题所需要的东西,那就是力,而且是一种冲动,“真理要想在同各种力的斗争中取胜,它本身必须先变成力,并在现象世界设置一种冲动作为它的代理人,因为冲动是感觉世界中惟一的动力。”这就是给理性提出的法则,而实行法则更需要勇敢的意志和生动的感觉来担当。在这里,理性的法则和感觉联系起来,而这就是席勒思辨中的重要思想,“培育感觉功能是时代更为紧迫的需要,不仅因为它们是一种手段,可以使已经得到改善的审视力对生活发生作用,而且还因为它本身就唤起审视力的改善。”
| 编号:H44·2240621·2146 |
这就是美的纯理性概念,它不是来自现实的事件,但它可以纠正并引导我们对现实事件的判断,它是从“感性理性兼而有之的天性的可能性”中推论出来的,这种感性和理性合而为一的天性就是美的天性,“一言以蔽之,美必须表现出它是人的一个必要的条件。”而审美修养的高度就是政治的自由和公民的美德、美的习俗和善的习俗、举止的文雅和举止的真实携手并进。那么,感性和理性如何结合而表现为一种美的天性?席勒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引出了人格和人的状态,在有限存在那里,它们永远是两个,人格是不变的,它有一个绝对的、以自自身为根据的存在观念,这个观念就是自由,保持不变的人格不可能来自变化;人的状态是变化的,它是由因果关系而产生的,不是绝对的存在的人的状态在变化时所需要的条件,就是时间,所以人只有在变化时,他才存在,人只有保持不变时,他才存在。
这是不是人的存在的一种悖论?在席勒看来,人要尽善尽美地表现出来就需要在变化中永远保持不变的一体,这就对人的这种一体提出要求:人必须把形式的东西转化为世界,是一切的天禀表现为现象,这就是要求绝对的实在性的法则;人必须把他仅仅是世界的东西消除掉,把一切带入他的变化之中,也就是说把内在的东西外化,把外在的东西加上形式,这就是要求绝对的形式性的法则,而两种法则的结合就是感性和理性兼而有之的天性法则。所以美的纯理性概念在冲动的力中表现为两种冲动,一种是感性冲动,它是由人的感性天性而产生的,职责就是把人放在时间的限制之中,使人变成物质,成为实在,实在充实了时间,时间也具有了内容;另一种是形式冲动,它来自人的理性天性,也就是绝对存在,它使人得以自由,在千变万化中保持住人的人格,它扬弃了时间,扬弃了变化,他让永恒的和必然的事物变成现实的。
看起来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在变化和不变中是对立的,但在席勒看来,因为它们误解了自己、违背了天性才成为对立的,而在本质上,它们具有融合的可能,文明的任务就是给两者同样的合理性,“它不仅面对感性冲动维护理性冲动,而且也面对理性冲动维护感性冲动。”而作为文明的人,他的人格性使物质冲动保持在自己的范围里,感性则使形式冲动保持在自己的范围里。各自保持在自己的世界里,这只不过是让文明不再成为自私自利的工具,或者说只是解决了人类自私的问题,但是并没有由此完成真正的融合,并没有走向真正的自由。席勒在这里便提出了两种冲动之外的第三种冲动,他命名为“游戏冲动”,游戏冲动的目标是:“在时间中扬弃时间,使演变与绝对存在,使变与不变合而为一。”它所要求的规定和感受就像自己制造的一样,它把形式送入物质之中,把实在送入形式之中,它夺去了感觉和热情强有力的影响,使它们和理性的观念一致,它又消除了理性的精神强制,使它和感官的兴趣相调和。
当游戏冲动将感性冲动的对象即最广义的生活和形式冲动的对象即本义和转义的形象结合在一起,它的对象就是“活的形象”,而这就是美的本质所在,“美是两个冲动的共同对象,也就是游戏冲动的对象。”在席勒看来,美的事物不是纯粹的生活,也不是纯粹的形象,而是活的形象,所以游戏冲动体现的是天性,体现的是人的自由,“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也因此,理性摆脱了文明本身的问题,它作出的断言就是:“人同美只应是游戏,人只应同美游戏。”但是游戏冲动仅仅是冲动,它还没有最终完成美的建构,而席勒看来,美是一种整体性,它需要的是抵达最后的自由,在这里就需要审美教育,即把多种美变成一种美,“从美的各种种类提高到美的总体概念。”从这里开始,席勒开始了真正的审美教育,它把美分为适用于紧张心情的“熔解性的美”,和适用于松弛心情的“振奋性的美”,“自由只有在人的两种天性共同作用时才会有。”
“熔解性的美”有两种不同的形体,一种是作为宁静的形式和缓粗野的生活,它是为感觉过渡到思想开辟道路,另一种是以活生生的形象给抽象的形式配上感性的力,它把概念带回到观照,把法则带回到情感,两种形式适合不同的人,而不管是谁,都在感觉的状态到思维和意愿的主动转移中完成了审美自由,而这也是真正文明的体现,“文明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使人在他纯粹的物质生活中也受形式的支配,使人在美的王国能够达到的范围内成为审美的人,因为道德状态只能从审美状态中发展而来,而不能从物质状态中发展而来。”而对于“振奋性的美”,席勒并未在《审美教育书简》中进行阐释,但是很多人认为他之后的《论崇高》是关于振奋性的美,但实际上,席勒在这里论及的并不是振奋性的美,而是崇高,也就是说,在席勒看来,美并不包含着崇高,两者是同属于人的天禀。
席勒把人的天禀分为两种,一种是美感,美结合了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美挣脱了自然的束缚,所以美带来的是自由。另一种是崇高感,崇高的事物那里我们同样感到自由,但是崇高感的自由并不是两者的结合,而纯粹是因为感性冲动对理性的立法毫无影响,“仿佛除了它自身的规律以外不受任何其他规律的支配。”崇高的自由混杂着痛苦和快活两种感觉,它们是感性冲动的表现,但是却不依赖于一切感性的触动而独立存在,也就是说,崇高感自身有一项自主的原则,它甚至和感性、理性也不一致,它所表现出来的就是矛盾——如果说美将我们禁锢在感性世界之中,那么崇高则让我们走出感性世界,它是震动,是混乱,是斗争,是搏斗,它释放天性,它体现意志,它表现尊严,“美仅仅是为人服务,崇高是为了人身上的纯粹的精灵服务。”在这个意义上,崇高的意义甚至更符合浪漫主义、狂飙突进运动的本质:
谁不是这样,宁肯欣赏一个乱杂无章但意味无穷的自然的景色,也不愿欣赏一座整齐划一但毫无生气的法国式林园?谁不这样,宁肯赞叹西西里岛上的洪水带来的肥沃与破坏之间的奇异斗争,宁肯在苏格兰的瀑布和云雾缭绕的山峰——即莪相式的宏伟自然——的面前饱享眼福,也不愿赞赏在笔直的荷兰耐心战胜最顽强的自然威力而取得的辛酸的胜利?谁会否认,在巴他维草原,物质的人得到的照应要比在危险的维苏威火山口好得多?谁会否认,一个正规的种植园,远比一个原始的自然景物,更能满足知性要理解和归类的要求?但是,人除了活命和安康以外还有一种需要,除了理解他周围的现象以外还有另外的天职。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0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