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5-09《鹳鸟踟蹰》:用来攀登的一双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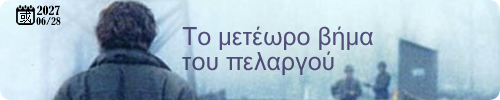
上映于1991年,距离新世纪的到来还有近10年的时间,在这个逐步走向世纪的末端而呈现出“世纪末”征象的时代,人类是不是会向鹳鸟一样活在踟蹰中:一只鸟站在土地上,另一只脚抬起,是要勇敢地跨过去告别这分离而忧郁的过去?还是缩回来继续以观望的方式甚至在拒绝中回到习惯性的生存世界里?一种是告别,一种是回望,“鹳鸟踟蹰”于前进还是后退?未来还是现在?面对这一问题,在1991年的西奥·安哲罗普洛斯似乎也用一个假设让这个问题变成了关于人类命运的悬疑命题:“假如现在刚好是1999年12月31日……”
这一个假设来自那个希腊政治家写就的一本书:《世纪末的忧郁》,在题辞上写道:“假如在1999年12月31日之前读到……”不管现在刚好是这个世纪的最后一天,还是在走向新世纪之前阅读,其实阅读者依然会保持“鹳鸟踟蹰”的状态,时间还未来临,故事还没有结束,一只脚是如何也无法安然选择最后的命运,而告别和回望的二元性带来的是对于世纪末的整体性忧郁,而这种二元性直接进入的是一个未知命运的乌托邦——不是虚构式的乌托邦,不是理想性的乌托邦,而是被现实完全包围的异域世界,种种的选择,种种的方向,其实都是现实的投影——“鹳鸟踟蹰”便是在这个异托邦里构建起以为能超越现实的希望,但它其实比现实更逼仄,更绝望,如《世纪末的忧郁》的作者在写给法国妻子的信中所言:“一无所有就是一无所有……”
安哲罗普洛斯用“鹳鸟踟蹰”这个具象性的动作演绎世界末的人类境遇,而实际上在这个异托邦里,并不仅仅是踟蹰这样一种悬置的状态。一开始是记者的旁白:“在边境做报道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比雷埃夫斯港事件,那些亚洲偷渡者的尸体漂浮在海水中,当他们得知希腊政府拒绝给他们提供政治避难后,他们决定以死抗争,最后选择集体投海……”亚洲偷渡者跳海自杀,他们偷渡的那艘轮船就是被命名为“海鸟号”的希腊海轮,海鸟没有让他们学会飞翔,没有使他们跨越了希腊的边境,这不是一种踟蹰的状态,而是抗争的结果,所以在这个不能跨越的边境线上,偷渡者和希腊构成了异的世界,而这种异带来的是死亡,记者对于无法忘记的这一触目惊心的事件,发出质问的是三个问题:人是如何离去的?为何会离去?他们去往了何方?
异之死,其实连异托邦都没有被构建起来,记者的三个问题指向了事件最核心的部分,却也是对于异的一种发问,因为他们不属于这片土地,因为他们无法实现政治避难,所以他们无法成为那些飞翔的海鸟,他们的尸体被海水浸泡。没有构建起异托邦,却指向了异带来的普遍悲剧:异就是缺少同一性,异就是矛盾和冲突,异就是被悬置在踟蹰的状态中,在无法趋向于同一性的构建中,不断走向世纪末的人类只能在相互隔阂、相互猜忌、相互放逐的异世界里生活。异可以是异国,可以是异见,可以是异教——上校带着记者来到了边境线,就是展开了所谓异的地理性对立,“你知道什么是边境吗?”他走到那座两国作为国界标志的桥,在那条边界线之前,他抬起了脚,但是没有在那一边放下,这就是一种“鹳鸟踟蹰”的鲜活示范,“你只要迈出一步,就是过界了。”过界意味着私闯,意味着侵犯,当然更意味着被击毙:对面的守卫在抬起脚的一刹那就已经端起了枪做好了瞄准的动作,过界的唯一结局就是死亡。
这就叫边境,这就叫异。上校带着记者来到了那条界河,那里正有人用自作的设备将播放着音乐的磁带送到河对岸,或者还有人通过这种方式秘密进行烟草交易;上校又带记者来到了瞭望塔,从高处瞭望,是那个边境的小镇,这个被称为“候车室”的地方就是希腊政府设立的难民营,那些来自库尔德、伊朗、阿尔巴尼亚的难民暂时生活在这里,他们等待批文,只有拿到批文他们才有机会去“别处”,所以一条河隔开了两个世界,一个属于阿尔巴尼亚,另一个则属于希腊的“候车室”,这是另一种异,和那座桥上的边境线相比,这里没有赤裸裸的死亡威胁,但是这里所体现的异比那条线的范围更广。不仅这里就是一个被圈起来的异托邦,他们是难民,还不是正式被希腊政府接纳的难民,他们无法跨越出一步;而且这里的难民来自不同的国家,属于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生活习惯,所以在这个“候车室”里,也常常发生矛盾和冲突:在一家小酒馆里,几个男人找到一个人,并把他叫“叛徒”,但是那人却声明自己不是叛徒,他大吼,他哭泣,他甚至用刀片在手上割开以此证明自己的清白,但是不久之后,这里发现有人被一辆吊车吊死,尸体在上面晃动着,不知道谁是凶手,但这样的死亡就和关于叛徒的冲突有关,而这样一种冲突带来的死亡,是对于宗教和民族的异见和异教的诠释。
| 导演: 西奥·安哲罗普洛斯 |
异国之间隔着细细的边境线,异教和异见会带来暗处的杀戮,而在人类生活的现实里,异更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更表现为没有家的漂泊。写作《世纪末的忧郁》的希腊政治家有一个漂亮的法国妻子,在希腊内阁中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那次在议会大厦举行的会议上,他本来想作演讲,但是当他走向演讲台,犹豫之中把文稿放进了口袋里,然后只说了一句话:“有些时候,个体需要沉默,为了听到雨幕后面的乐曲。”一句话就是他的沉默,之后他离开了会场,消失在那些政治家的目光中,也消失在妻子的世界里。他失踪了,即使四十天之后他再次回到妻子身边,但是二次出走之后妻子再也没有见过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言说了沉默,写作了关于世界末忧郁的书,选择了失踪,是因为他看到了世界的异化,一方面,个体在政治生活中已经没有了说话的意义,唯有沉默是对于“雨幕后面的乐曲”生活的坚守;另一方面,他也离开了妻子离开了家离开了婚姻,四十天后他回来,他和妻子做了爱,但是这种回来依然是异带来的缺失,就像妻子所说:“我们像是两个陌生人,在一起只是一段露水情缘——他完全蜕变成另一个人。”这是妻子的感受,那个丈夫已经不再了,而政治家写给妻子的信中些表达了这样的想法:“我不能与你携手,我注定是过客,一无所有就是一无所有……”所以在过客的生存状态下,回来的他再次选择了失踪,从此音讯全无,这是异制造的无。而那个上校呢,他在小酒馆对记者说,自己接到了去边境驻守的任务,妻子在雅典,女儿准备去英国留学,“这仿佛就是人生的悲剧,我变成了吉普赛人……”
国与国之间的边境线,难民与难民之间的矛盾,男人和女人之间的隔阂,这些都是异呈现的人类状态,有人选择逃避,有人选择沉默,有人选择消失,有人则走向了死亡。但是,对于这个异托邦的观察者来说,记者进入其中感受不断异化的绝望,发出“人是如何离去”的质问,亲见死亡、沉默和消失,他的存在其实是承载了某种使命,那就是在异中寻找同一性。在拍摄新闻类节目中,他发现了那个抽烟的男人很像失踪的政治家,这一种想象扩展开了他构建同一性的基础,他找来政治家的妻子挖掘那些线索,他甚至登门拜访他,“我不知道是对这个小镇感兴趣还是对他感兴趣?”但是法国妻子说:“那个人不是他。”在否定这种同一性的时候,她还不断地强调:“他已经死了,肯定死了。”男人或者就是一个阿尔及利亚难民,当他面对记者时说:“我们跨越了边界,然而我们仍在那里,我们需要跨越多少边界才能重返家园?”而他对那个孩子讲述的关于风筝的故事却永远没有结局:当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人们开始迁徙,他们以撒哈拉沙漠为目的地,那时一个小孩扯起了风筝,大人也和他一样,不断拉着线,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东西,开始了漫长的旅行……故事没有讲完,因为那些人永远走不到最后的终点,或者这个世界本没有成为归宿的终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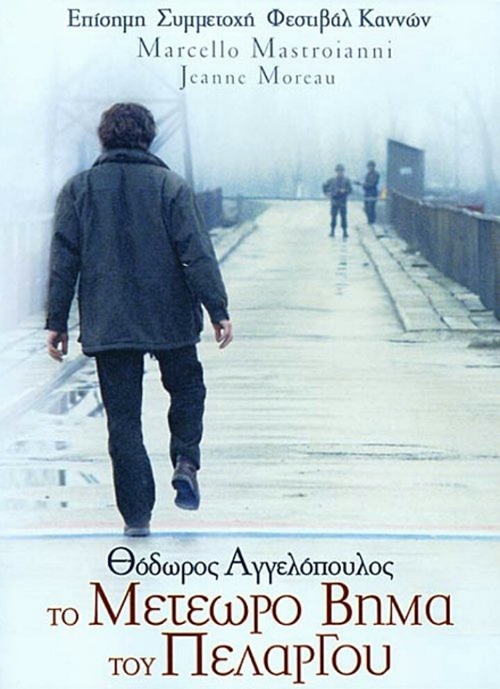
《鹳鸟踟蹰》电影海报
这是另一种“鹳鸟踟蹰”的状态,男人在记者面前走下河滩,然后去捉水里的小鱼,他像极了那只鹳鸟,但是他并不是踟蹰,而是一步一步朝着目标前进,最后瞄准时机——尽管两只手没有捉到那条鱼,“它逃掉了……”但是这是不是对于命运改变的一种努力?而男人的女儿对于爱情的渴望也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在小餐馆里,记者坐在桌旁,四周的人载歌载舞,这时邻座的女孩盯着他看,长久地注视,不曾变换位置;终于记者发现了她,他也朝女孩望去,也凝视着她;等他站起身,走过女子的身边,女孩的目光孩在他的身上;记者走到酒馆门口,回过身来看见女孩还在看他,他也再次保持观望的姿态——在这个几分钟的长镜头里,看和被看完成了一种呼应,在这种呼应里,同一性取代了陌生感颠覆了相异性,终于女孩走过来和记者一起走进了旅馆。
但是,女孩或者把记者当成了另一个人,“你为什么要喊着另一个男人的名字?”这是记者的疑惑,疑惑的背后似乎又返回到了相异性的世界里,而且按照同事的说法,明天河滩上的那场聚会就是女孩的婚礼。婚礼,隔着一条河,这里的是穿着白婚纱的新娘,那边是穿着黑礼服的新郎,这边和那边,白色和黑色,男人和女人,以及阿尔巴尼亚人和在希腊“候车室”的阿尔巴尼亚难民,他们构成了一个异的世界,但是这场婚礼却是在创造同一性:骑着自行车而来的牧师为他们主持婚礼,新郎在河那边将花抛向了水里,新娘也将头上的花环抛到和河里,他们相望,他们呼应,他们隔空结合在一起。婚礼之后,成为新娘的女孩对记者说的是:“我和丈夫青梅竹马,我们来自同一个民族,终会有一个夜晚他会渡河过来接我走。”来自同一个民族,完成同一场仪式,进入同一个婚姻,隔开的河流不是将他们推向异的世界,是爱让他们拥有同一个世界。
鹳鸟踟蹰,是如不能飞翔的“海鸟”一样,在抗争中成为一种悲剧;鹳鸟踟蹰,是抬起脚在可能越界中面临死亡的威胁;鹳鸟踟蹰,是坚定地朝着目标前进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活在异托邦,面向世纪末,苦难、冲突、隔阂构成了异,但是在异的世界里一样可以发现同一性,它是抗争,它是超越,它是抉择,即使现在已经是1999年12月31日,已经看见了“世纪末的忧郁”,鹳鸟也可以不以踟蹰的方式活着:最后的长镜头里,雪后的夕阳现出美丽的色彩,穿着黄衣服的修理工爬上了电线杆,他们步调一致,然后拉直了那些电线,在一步一步往上攀登的过程中,每一个人都是一只鹳鸟,不再踟蹰地爬向高处,望向远方,世纪末的到来是旧的结束,更是新的开始。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2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