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5-09《陈东东的诗》:重又把死还给了不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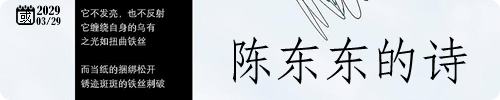
五月,在一间茶室的木窗格下,他将读到另一位诗人——
——《五月》
五月,里尔克在《布里格笔记》中写到了一位“快乐的诗人”,“他对他的窗子与书橱的玻璃门说话,它们的沉思也反映出一种可爱而寂寞的距离”;五月,陈东东在这间茶室的木窗格下,读到了里尔克的文字,读到了里尔克将要读到的另一位诗人,甚至陈东东认为里尔克会接下去写道:“这就是我希望成为的诗人。”五月,一个在五月的晴和五月的朗中独坐书房的读者,翻开《陈东东的诗》,时而会从椅子上起身,从玻璃窗向外望去,时而踟蹰在木制的书橱前,透过玻璃门看见自己五月的模样。
五月,是“一位快乐的诗人”的五月;五月,是里尔克希望成为那样的诗人的五月;五月,是陈东东在茶室木窗格下读到另一位诗人的五月;五月,是读者从不同的玻璃窗望见晴和朗的五月。读诗,从最里面的诗人开始,依次在里尔克的希望、陈东东的诗歌和一个读者的目光中成为关于诗歌的“四个四重奏”:是谁望见了谁?是谁又被谁读到?读与被读,看见与被看见,构成了五月绵延、层叠,甚至镜像的故事,这实在是一个奇特的互文现象,在窗子和玻璃中“反映出一种可爱而寂寞的距离”,诗人和读者仿佛如群山连接在一起,最后,所有人都变成了那个希望成为的诗人:“他的声音像澄明的空气里响着的铃。”
诗人的声音是五月澄明空气里响着的铃,《五月》来自陈东东的《二十七章》,五月之外还有七月,还有九月,还有另外读与被读的诗,另外看与被看的诗人,还有另外的群山另外的铃声另外的玻璃,但不同的诗人、另外的故事都在同一个五月变成了归一的存在:《二十七章》里是“他瞥见一个追求永远的流浪歌手依然故我”的《日子》,站在旧居的露台上,“面对石头拱门接石头拱门接石头拱门的单调街景”,反复的阴影里拨弄着烧焦的老木头琴;是“他下楼领取牛奶时总能碰到夜半梦见的同一个女子”的《早晨》,即使天亮了,“松散的发辫里残留着纯真色情的诗”;是“他终于会是他自己的信使”的那封《信》,寄出去、送达、然后将回信寄出,收信与回信都从和他有关的那个“黑暗城堡主人的信箱”有关;是“除了另一面镜子,不必另有他物”的《镜像》,即使镜子不再是对称于此生的一种有限,在乌托邦词语的增殖、省略、收缩和追忆中,镜子之外再无他物,和五月看见一个诗人的另一个诗人的看见,以及一个诗人被看见和被另一个诗人看见一样,“行进在纯粹由玻璃钢幕墙筑起的街头,他发现他写下过他从来未曾设想的句子。”
《二十七章》里他依然故我,梦见同一个女子,自己是自己的信使,一面镜子之外再无他物,对称甚至变成了同一,那么诗人和诗歌是不是也在这五月、这《二十七章》里成为“另一个,同一个”?但是当陈东东在镜子里构造了增殖、省略、收缩、追忆的乌托邦,当“不必另有他物”的镜像完成了对此生有限的取消,那由玻璃幕墙筑起的街头,为什么还会发现他从未设想的句子?玻璃和他、他和句子构成了镜像乌托邦之外的存在,也许依然故我的他不再是同一个我,梦见的同一个女子早就在醒来中消失,在收信和寄信中那个信箱已经有人偷偷打开了,所以陈东东在《西区》里说:“而繁复的楼道间,或纠结了黑暗的陌生的弄堂里,那递送晚报的绿衣人晕眩。”晕眩让他在落日里生锈;所以在《奇观》里一段铜线、一片薄膜、一句捕捉不住的呓语,终究在最新版本的只能手机里变成了一种不确定,“一心想要在人之境写诗,却难免写入某种妖魔境地的诗人,其实很早就发现了这一时间的奇观。”
晕眩是时间的晕眩,奇观是时间的奇观,镜像是时间的镜像,一定是时间越过了五月的晴和朗,一定是时间制造了足够的阴影,让那些透过玻璃的词语变成了另一个句子,让那些“依然故我”的同一个自我变成了他者,“它终于变成了一个暗影,从回忆的深底浮起的意象,传说中一匹秘密的走兽。”而写于1985年至2015年的《二十七章》,何尝不是在三十年“他将读到另一位诗人”中变成了关于诗歌的“暗影”。但是,很具有对称意义的是,陈东东在推出《二十七章》的“奇观”和“暗影”时,却又构筑了《七十二名》。写于1989至1996年,《七十二名》在七年里完成,在创作时间上似乎就是对三十年的一次背离,而“七十二”之于“二十七”的倒置,“章”之于“名”的变动,是不是从大幅的“暗影”回到了个体的“词语”?从讽喻的“奇观”回到了归一的自我?陈东东对此的回答是:“每个词独立、完满,却又是种子、元素、春天和马赛克,是无限宇宙里有限的命运。”
《二十七名》是独立的词,是完满的词,是无限和有限的词,是被命名的词,也一定是五月里那个“我希望成为的诗人”写下的词——因为词语就是诗歌,引用狄兰·托马斯的诗句,“我知道这邪恶的点滴时间”,词语在里面可能被一张纸裹住,可能被锈迹斑斑的铁丝刺破,但是,邪恶的点滴时间之外,“它仍是一个奇异的词”,一个“指向它那不变的所指”的词,一个“置身于更薄的词典”却仍是奇异的词——邪恶的点滴时间和奇异的词,对应于“二十七章”的暗影和“七十二名”的词语,对应于不确定的奇观和独立、完满的词,构成了陈东东破和立的诗意线索,那么,“将读到另一位诗人”的陈东东如何在词语的名中发现“无限宇宙里有限的命运”?如何子去除暗影中发现独立和完满?又如何在真正的镜像里发现从未设想的句子?
| 编号:S29·2230205·1914 |
从发生的现实开始,从对命运的解读开始:端点不是生却是死。“他被装进木盒子里/他的无视又得以穿越冬季的墙/他甚至看见了消失的风景”,写于1985年的《骨灰匣》无疑就是在关注一种死亡:一个十几年前就老了的人现在变成了“一根腐朽的羽毛”,听到孩子们在秋天里喧闹,他便知道“他成了自己的荒地”,之后是蒿草没顶,是“潮湿的石头又冷又硬”,是左边的一束纸花,是面前的三只塑料橘子,是纤瘦苍白的烛火——但是这一切都不是在他者意义上的送行和祭奠,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的看见,一个人的听说,一个人的知道,一个人的想象,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将走向死亡就是一种不死,“他重又把死还给了不死”。把死还给不死,而且重新把死还给不死,在死与不死之间,陈东东构筑了一种看似循环实则否定的关系,看见、听说、知道和想象的死,是常人之死,是俗世之死,是普通之死,而看见、听说、知道和想象之行动却是不死——但是,这不死之死和死之不死还没有完全进入陈东东的诗意世界,但是“重又把死还给了不死”却已经是词语命名的开始。
死亡在发生,1986年《秋雨夜过墓地》中见过的是“在空旷的尽头会面”又哑然失笑的死者,“我推门进入厅堂的时候/说话声戛然,音乐凝冻,弗朗茨/卡夫卡伸手过来,想不起是否曾跟我相识”;《病中》里有忧郁的护士,有呻吟的老人,有得病的妇女,最后是降临的死亡,“正当你视线自花园移开/第一滴雨/落进了第一个死者的掌心”;诗歌皇帝当然也没有逃离亡国的命运,“接近完成的多米诺帝国”终于变成了窒息的大业,这是另一种死亡,铺张的万千重关山只剩下“虚空里最为虚空的啁啾”;连《奈良》里那樱花、那花鹿,那法隆寺殿,也都构筑了如梦之境,“走马观花一过/即为葬身之地”;面对死《读一部写于劫后的自传》,有时候会有诱人的“第二生”开始的意愿,会有“死者/才是真正的幸存者”的想法,只是,“死亡营有一个虚妄的结构”;甚至,陈东东自己也感觉到了从出生开始就是一个混杂着记忆与感情纹理的梦境,“我生于荒凉的一九六一”,这是“偶然说起”?却是必然,未知于死的生,也是未知于生的死。
看见死,听说死,知道死,想象死,从生到死,死亡就这样成为唯一的结局,这是有限的命运,所以在死亡的解读里,陈东东一定是要从反面进入到无限之宇宙中,一定是为用词语书写一部“来世之书”,“一本来世之书,仿佛星期天上午的金星。它被书写,继续被书写。以七月为心脏的冬之歌手仅能在死亡里将它触摸。”从有限到无限,从此生到来世,从虚妄到必然,在陈东东的命名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被凸显出来,那就是“否定者”,1992年写就的这首诗将“否定者”作为了从现实中出生却超越现实的存在:否定者从火中出生,否定者是“蜜/和涂上了蜜汁的细小的刺”,否定者是“刺带给咽喉的那份尖锐”,否定者是在尖锐中制造了“一点疼痛的血”——是火,是蜜,是刺,是尖锐,是血,这就是否定者的全部意义。而陈东东之所以命名这个否定者,就是在否定与肯定之间建立一种对立的关系学。
|
| 陈东东:它仍是一个奇异的词 |
肯定的是蝴蝶图谱和大海小腹上的纯洁性,却变成了色情和盐,最后,“火车正靠向你素馨的床沿”;肯定的是那个古老的梦,但是“冲凉的水龙头/代替这场雨洗去梦想(《在汽车上》)”;肯定的是“吴淞江岸北/片面的诗意”的邮局,却在旧物质慢慢褪尽中变成陡坡上自行车俯冲的意象……纯洁性和床沿,梦想和醒来,诗意和衰老,对立的关系学在陈冬冬那里充满了某种感伤,但是命名了否定者,就是要从现实中用针刺出那疼痛的血,而“上海”也成为了陈东东笔下的否定者面对的视域:外滩旁边的花园变迁,虎皮被人造革替换,水泥成为想象的石头,“它漂离堤坝到达另一侧”,以及外白渡桥浑浊的阴影、泛白的城市三角洲、石头长成了纪念塔,它当然制造了暗影,“从桥上下来的双层大巴士/避开瞬间夺目的暗夜/在银行大厦的玻璃光芒里缓缓刹住车(《外滩》)”时代广场未能阻止一座桥的冒险一跃,“从旧城区斑斓的/历史时代,奋力落向正午//新岸,到一条直抵/传奇时代的滨海大道(《时代广场》)”也有玻璃,也有暗影,“玻璃钢女神的燕式发型/被一队翅膀依次拂掠”;甪直的“甪”是独角,“甪直”便成为了麒麟,在周末告别键盘,甩脱大城市难看的水泥花边,但是那里没有田园风光,“它的神是一个邋遏女人/浑身散发泥土的芳馨/比花朵柔软,那些胸脯/像一座座坟”,新世界为它编码,房地产销售的一刀代替了一瞥,马戏团预告的新潮脱衣舞正在上演……
这是存在的上海,这是现实的上海,这是暗影的上海,这也是否定者面对的上海——一直生活在上海的陈东东将“上海”放入了“七十二名”中,在他看来,上海“朝着感性、肉体、神经和骨髓漫无节制的癫痫症黑暗疾驰”,上海是一个漩涡,“不仅令人眩晕,而且令每一个进入其中者最终成为漩涡本身,无限地运转,在惯性中为避免被高速抛出而努力向心,无限地沉沦”,当否定者站在上海的对面,其实是要发现带着疼痛的血的上海,“对它无法言说之时,它又已经以对语言的否定扩大了数倍;梦见它坍塌和深陷之时,它又似乎正山岳般耸起。”上海是生活和生存着的上海,是否定者面对的上海,也是在“七十二名”中的上海,是无法言说而言说的上海,是坍塌又耸起的上海,所以上海是两面的,更是多面的,是在否定与肯定之间建立对立关系学的那面词语的镜子。
透过玻璃的反射、折射,透过镜子的镜像,甚至透过透明之存在,陈东东所构筑的是否定者看见的那个世界,词语在那里说话,词语在那里书写,词语在那里抵达无限宇宙的有限命运——“七十二名”无疑是陈东东命名的词语世界,不妨从那些名里找寻真正站立着的否定者。“当云层突然四散,鱼群被引向/临海的塔楼/华灯会瞬息燃上所有枝头/照耀你的和我的语言”,这是1983年的《语言》,陈东东在语言里发生,在语言里面命名,这其中就有海,就有灯,鱼群被引向临海的塔楼,“海”是什么?“海被我置于当前。海不是背景,而是我诗的心脏。活着的心脏优先于灵魂。”海是没有阴影的海,是“平静的房顶”的海,是父性的海,是容纳一切名的海,当然更是否定者的海,“被海的环状闹市区围拢,逆死亡旋转的海盆体育场里巨人们骑着虎鲸争先。”灯在熄灭中点燃语言,“灯”是什么?“灯——自明,并且把其余的也都照亮;正如诗歌自在,并且证明人的存在。”灯自明而且照耀他人而他明,所以灯点燃词语,灯照亮诗歌……
还有“莲女和渔夫、渡叟和钓翁、志士、隐者、琴师、高手、墨客、僧侣、看风景的和饮花酒的”所在的“湖”,它也是江湖,“名之湖,书面的湖,泛黄纸张之间的湖,汉字围拢的绝对的湖”;还有“被无数次复制、毁坏、放大、缩小、节选、加注、精装、简装、携带、丢失、赠送、转让、抵押和遗忘”的书,它成为复数的存在,它也可能出自一个抄写员之手;还有“是命运之车的钢轨,是写作之河的闸门”的梦,还有“张扬自我中心的人之命运”的火,还有“万有人性和神性显露于感性洁净的表面”的水,还有“成为眩晕的根本原因”的光……“七十二名”是七十二个词语,是七十二首诗,是七十二个否定者,但是词语从来都不是经久不变的,陈东东的命名也并非是为了固定一种永恒的价值,也正是这种变让否定者的诗人永远可以在五月“将读到另一位诗人”,所以有了“广播在广播/广播体操反复的广播(《莫名镇》)”的繁复,有了“现在/只有寒/只有寒凝冻一切皆寒(《写给娜菲的冬之喀纳斯序》)”的循环,有了《为题作石榴的本子而写并题写石榴》的强调,有了“被象征的意愿先于象征”和“被象征的乌有先于象征”的晕眩……
但是词语不是游戏,词语是否定者的言说,词语是诗人自明的灯,词语是流动于血脉的火,词语是毁灭和再造的水,无限之宇宙,有限之命运,“在名之下,有了期待、成长和老去,有了回忆、悔悟和死难,有了四季、轮回、重临和不复返,有了旧梦,新雪,有了生活和妄想拥抱虚无的生命……”还是在山中,还是有铃声,还是诗人和诗人,陈东东和柏桦,“两个诗人,倾听和指点”,五月的晴和朗,五月的沉与思,五月的暗和影,五月的“七十二章”和“二十七名”,在窗子和玻璃门的词语中,“反映出一种可爱而寂寞的距离……”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5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