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2-28《瞧,这个人》:我是卓越的毁灭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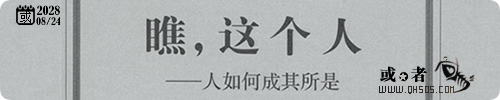
现在我要叫你们丢掉我,去寻找你们自己;唯当你们把我全部否弃时,我才意愿回到你们身边……
——《序言》
“瞧,这个人”,睁大眼睛,竖起手指,或者怒目圆睁,握紧拳头,口中发出的是愤懑和谩骂之声。一个标题是一种态度,想象那个叫尼采的人正投入一场战斗,而他面前的敌人就是被瞧见、被指明,也必须被毁灭的“这个人”。
在瞧见和被瞧见之间,在毁灭和被毁灭之间,在尼采和“这个人”之间,对立无可避免,但是,尼采是谁,“这个人”又是谁?在《序言》里,尼采定义了“我”以及站在“我”对面的“这个人”:“不过,我的使命之伟大与我的同时代人之渺小,两者是大不相称的,这种不相称表现在,人们既不听我的话,也未曾哪怕仅仅看一看我。”我是拥有伟大使命的人,他们是渺小的人,我是靠自己的信誉活下来的人,我成了他们眼中的一个偏见——伟大和渺小,信誉和偏见,甚至活着和死去,构成了这种关系。很明显,当我以“瞧,这个人”的态度和方式来定义自己的时候,渺小者、偏见者和死去的“这个人”必定构成了我只反对个抗拒的目标。
“我是哲学家狄奥尼索斯的一个门徒,我更喜欢成为一个萨蒂尔而不是成为一个圣徒。”他们为什么是“圣徒”?因为他们活在偶像的世界里,偶像是什么?陶土做的双脚能站立吗?偶像不正是捏造的陶土?所以偶像指向的理想世界实际上是虚假的世界,它是真实世界的反面,人们正式通过树立偶像活在那个虚假的世界里,并由此获得了价值、意义和所谓的信仰,“理想的谎言一直都是实在头上的咒语,人类本身则通过这种谎言而在其最深层的本能当中变得虚假和虚伪了一一直至去膜拜那些相反的价值,或许正是这些相反的价值才保证了人类的繁荣、未来以及对于未来的崇高权利。”用谎言建造的权利世界里,信仰和道德也便是虚无的存在,哲学当然更是一种谎言,在这个意义上,尼采认为这就是谬误的产生:它不是盲目而是怯懦。
当指出了那些圣徒以树立偶像的方式膜拜价值以及获得权利,尼采也完成了“我”的定义:我是圣徒之外的狄奥尼索斯的门徒,我把哲学当成是“寒冰和高山上的自愿生活”,我要拆除偶像之陶泥,我在被禁止中寻找真理,“以此为标志,我的哲学终将获胜,因为一直以来,人们所禁止的根本上始终只是真理。”而这个我有一个代言人,那就是查拉图斯特拉,查拉图斯特拉是诱惑者,“而当查拉图斯特拉第一次重返寂寞时,他自己到底说了些什么呢?”诱惑者说出的是与“智者”、“圣徒”、“救世主”以及其他颓废者相反的话,甚至就说出了那句“瞧,这个人”,所以我是伟大的,我是偏见的,我不与这个人混为一谈。
但是,在我和这个人之间成为对立存在的时候,“人如何成其所是”的命题并没有最终完成,“这个人”是战斗的目标,我是狄奥尼索斯的门徒,是查拉图斯特拉,但是一切的战斗都是为了寻找真理,所以最后是建立“你们”的世界:你们最终要丢掉我,你们最终要寻找你们自己。丢掉和寻找才是“你们”的终极生活,才是人如何成其所是的最终答案:在“这个人”、我和你的三者关系里,尼采构筑了关于人的本质命题——副标题“人如何成其所是”,“人”是生命的本质命题,这个命题的目标是成其所“是”,它的过程则是如何“成”。
按照《序言》里的关系命题,尼采无疑要“叙述我的生活”,我这样一个和渺小者站在对面的伟大者,如何会变得伟大?“我威慑么如此智慧”“我为什么如此聪明”“我为什么能写出如此好书”,如此智慧,如此聪明,以及写出如此好书的我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在《我为什么如此智慧》中,尼采回顾了自己的人生,他把“厄运”看成是让自己拥有独一无二生命的一个原因:“在我父亲生命衰落的那同一个年纪里,我的生命也开始衰落了:36岁时,我的生命力降到了最低点,——我还活着,但却看不到离我三步远的东西。”这是一种痛苦的遭遇,这是一种病态的身体,生命力降到最低点,是颓废者的人生。但是尼采认为,正是这种厄运反而让精神变得明亮和喜悦,反而拥有了健康的意志,反而懂得了生命的哲学,“一个典型的病态人是不会康复的,更不能自我康复了;相反,对一个典型的健康人来说,患病甚至可能是一种有力的兴奋剂,一种促使更丰富地生活的兴奋剂。”漫长的疾病让自己重新发现了生命发现了自己,它成为意志的一部分,成为哲学的一个内容,“作为surn -ma summarum[顶峰之顶峰、至高无上者],我是健康的,作为隐僻一隅,作为特性,我是颓废者。”
| 编号:B82·2221105·1895 |
从疾病、痛苦、厄运和颓废,尼采在我的世界里发现了生命、意志和哲学,这就是“如此智慧”的人生,而这一切在尼采看来就是“重估一切价值”:“从病人的透镜出发去看比较健康的概念和价值,又反过来根据丰富生命的充盈和自信来探视颓废本能的隐秘工作——”颓废而健康,痛苦而智慧,厄运而意志,重估一切价值中尼采也命名了“我”的父亲,“伟大的个体乃是最老的个体:我理解不了,但恺撒可能是我的父亲——或者亚历山大,这个真正的狄奥尼索斯……”如何重估一切价值,如何变成智慧者?尼采否定乐于助人的“博爱”,他认为这是一种虚弱,是无能于抵抗刺激的个案,“唯有在颓废者那里,同情才意味着一种德性。”否定理性,理性只是把自身当做一种天命而不愿意“改变”自己。在否定博爱、同情和理性之后,尼采也终于变成了“重估一切价值”的战斗者,“按我的本性来讲,我是好战的。攻击乃是我的本能之一。能够成为敌人、成为敌人——这也许是以一种强壮的天性为前提的,无论如何,它都取决于每一种强壮的天性。”他把自己的战斗实践归结为四个定律:只攻击那些胜利的东西;只在找不到盟友、孤立无援的时候才攻击;从不进行人身攻击;只攻击“那些排除了任何个人差异、没有任何恶劣经验之背景的事物”。
四种攻击成为战斗的实践,但是正如《序言》所指出的,在我对这个人的战斗之后,最后面对的既不是我个人,也不是这个人,而是你们,是丢掉我、寻找自己的你们,所以尼采说:“攻击在我这里乃是善意的证明,或许也是感恩的证明。”在《我为什么如此聪明》中,攻击和战斗当然没有停歇,只是尼采在这里将“这一个人”更具体化了:这个人和宗教有关,将我定义为“有罪的”,而打开了一个上帝、灵魂不朽、拯救和彼岸的世界,尼采认为这一且都是“纯属我不予关注、也没有为之消耗过时间的概念”;尼采攻击了德国文化,“我从来没有原谅瓦格纳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屈尊俯就德国人,——就是他成了德意志王国的了……德国所及之处,它就败坏了文化。”目标如此明确,所以只有战争才能“拯救”:战争是树立对立面,“我根本就不把这些所谓的‘一流人物’算作人,——对我来说,他们是人类的渣滓,是病态和复仇本能的怪胎:他们纯属灾难性的、不可救药的、对生命进行报复的非人……我要成为他们的对立面:我的优先权在于拥有对健康本能之全部征兆的至高敏感。”战争更是一种建构,“我表示人类之伟大的公式是[热爱命运]:人们别无所愿,不愿前行,不愿后退,永远不。不要一味忍受必然性,更不要隐瞒之——所有理想主义在面对必然性时都不外乎是谎言——,而是要热爱之……”
从颓废中热爱,从非人中为人,尼采就是在这样一种对立中为人找到正确的战斗之路,“人成其所是,前提是人压根儿就不知道人是什么。基于这个观点,即使是生命中的失误也有其本身的意义和价值,诸如暂时的歧途和邪路、迟疑不决、‘谦逊’、在远离那唯一使命的各种任务上面挥霍掉的严肃认真。”而人成其所是的过程对于尼采来说,就在于“我为什么能写出如此好书”的答案里:一方面,身为作家也依然是被他们定义的作家,著作当然也会“败坏”趣味和鉴赏力;另一方面,在抛弃“纯粹的愚蠢”中打开的书册是伟大的韵律,是伟大的风格,是大起大落的超人激情,这就是尼采所说的“酒神颂歌”,如《查拉特斯图拉如是说》中的“七个印记”,“我就飞越以往所谓的诗歌千里之外了。”
那些书里到底有怎样败坏趣味和鉴赏力的东西存在,又如何在酒神颂歌中演绎伟大的风格?如何以攻击的方式完成战斗,又如何表示热爱生命之伟大?尼采对自己的著作进行了点评,而贯穿其中的便是在我、这个人和你们中完成“人如何成其所是”的命题。《悲剧的诞生》完成于1872年,尼采开宗明义:“让这本著作产生效果,甚至于产生魔力的,正是它的错误——那就是它对瓦格纳主义的利用,仿佛瓦格纳主义是一种上升的征兆。恰恰因此,这本著作就成了瓦格纳生活中的一个大事件:从那时起,瓦格纳这个名字才有了大希望。”瓦格纳主义包含在“瓦格纳事件”中,《瓦格纳事件》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一个音乐家的问题”,一个音乐家的问题当然是瓦格纳主义的问题,尼采为什么要忍受音乐?那“就是忍受音乐已经丧失了它那美化世界、肯定世界的特征,——音乐成了颓废音乐,不再是狄奥尼索斯的笛声了……”所以回到《悲剧的诞生》,在悲剧诞生之前,理性让音乐丧失了美化和肯定世界的意义,理性让音乐变得颓废——在尼采这里,“理性”是加了引号的理性,“‘理性’反对本能。‘理性’无论如何都是危险的,都是埋葬生命的暴力!”所以悲剧必须诞生,它是“狄奥尼索斯现象的第一门心理学”,从这个现象中可以看到整个希腊艺术的唯一根源;它指出了苏格拉底主义对希腊艺术的消解,因为苏格拉斯就是一个典型的颓废者;它反对否定一切审美价值的基督教,“基督教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是虚无主义的,而狄奥尼索斯象征却达到了肯定的极端界限。”
悲剧必须诞生,是因为悲剧是狄奥尼索斯的本质,因为悲剧肯定着生命本身,因为悲剧是对存在的最高肯定,它就是“生成”,“对消逝和毁灭的肯定,一种狄奥尼索斯哲学中决定性的东西,对对立和战争的肯定,生成,甚至于对“存在”(Sein)概念的彻底拒绝——”在这里,“悲剧的诞生”便成为了尼采关于“人成其所是”命题的一个答案,诞生就是生成,悲剧就是“是”,所以尼采说:“我期望着一个悲剧时代:当人类有了关于最艰难但却最必然的战争的意识,而又没有因此而痛苦,这时候,肯定生命的最高艺术,也即悲剧,就将再生了……”《悲剧的诞生》是尼采战斗吹响的一个号角,而回到《不合时宜的考察》,则是投入到另一场战斗中:在四篇《不合时宜的考察》中尼采揭示了德国教育的恶毒、科学活动的危险性、重建文化的两个极端形象,“我是喜欢剑拔弩张的,——也许也证明了,我的手腕是危险而自由的。”《人性的,太任性的》则是尼采建立的危机纪念碑,“在这里举例说,‘天才’冻僵了;另一个角落里‘圣徒’冻僵了;在一根粗大的冰柱下‘英雄’冻僵了;最后,‘信仰’冻僵了,所谓的‘信念’,连‘同情’也完全冷却了——‘自在之物’几乎在所有的地方都冻僵了……”当然,人性也在所谓的理想主义光环中“冻僵”了。《曙光》一书,尼采说自己“打响了反对道德的战役”,他所反对的是这样一种必然的洞识:“人类不会自发地走上正确的道路,也根本没有受到神性的统治,相反地,恰恰是在其最神圣的价值概念的影响下,否定之本能、腐败之本能、颓废之本能起着诱惑和支配作用。”这样的道德是“无自身性”的,它最终指向的是无生命……
战斗在进行,攻击在继续,《善恶的彼岸》是“一种未来哲学的序曲”,尼采对现代性进行了批判;《论道德的谱系》给出了基督教的心理学、良心的心理学,回答了禁欲主义理想、教士理想的巨大权力来自哪里,“也许是我迄今为止的著作中最阴森可怕的”;《偶像的黄昏》中,尼采则抡起了锤子,在“怎样用锤子进行哲思”中尼采以“最富于实质内容,最卓然独立,最具颠覆性”的方式打碎了偶像,让旧真理濒于灭亡……锤子哲思,战斗精神,生命意志,对于尼采来说,每一本书都是攻击的武器,而一切的攻击和战斗,都是为了重新回到“人成其所是”的命题和实践中来,《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便是对人之命题的阐述,尼采甚至人为其中的永恒轮回思想是我们“所能获得的最高的肯定方式”,它在1881年8月的纸条上写上的一句话是:“高出于人类和时间6000英尺”。这是尼采的高度,这是尼采思想的高度,这是尼采之“我”的高度,正是在这个高度上,尼采以查拉图斯特拉的方式俯瞰,“查拉图斯特拉甚至也主宰了对人的大厌恶:对他来说,人是一种怪物,是一种材料,是一块需要雕琢的丑陋石头。”查拉图斯特拉站在高处,他说出的是“不”,他代表的是精神,他获取的是健康,而他的另一面则是带着锤子的坚强乐于毁灭的狄奥尼索斯。
查拉图斯特拉在说,狄奥尼索斯在说,尼采在说,他们都是“我”:“我不是人,我是甘油炸药。”我在战斗,我在毁灭,我在创造,“我是第一个非道德论者:因此我是卓越的毁灭者。”当查拉图斯特拉把从不讲真话的善人称为末人称为最有害的人,当狄奥尼索斯反对被钉十字架的人,尼采在“我为什么是命运”中定义了道德,“道德——颓废者的特异反应性,其隐含的意图是报复生命——而且成功了。”但是毁灭有时也是一种自我毁灭式的牺牲,“我为什么是命运”的尼采还是没能逃过命运:1888年10月底,已经精神失常的尼采开始写作此书,12月初完稿,随着本书的完成,尼采的精神开始加速崩溃,这本书也便成为了尼采的遗著。“瞧,这个人”终于成为了尼采之“我”的终极态度,疯狂终于成为了尼采之“我”走向深渊的终极命运,但是在“这个人”之外,在“我”之外,“你们”也正在从战斗和毁灭中看见了生命的意义:“现在我要叫你们丢掉我,去寻找你们自己……”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461]
顾后:《蛹梦》:我们等待着裂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