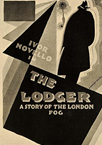2024-05-13《房客》:“麦格芬”敲响了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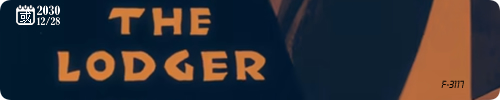
果断给了四星!并不是因为这是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心目中第一部真正的“希区柯克式电影”,也不是因为这是他第一部在商业上获得成功的电影,更不是因为在这部电影中希区柯克第一次客串出境——这诸多的第一次或者只是一种表象,在希区柯克早期的默片时代,这部根据Belloc Lowndes小说改编的电影具有突出地位,关键就在于希区柯克明确表达了那种独创性存在并成功被标注为个人经典。
一是在题材选择和主题上,希区柯克明显偏离了庸常,1927年希区柯克上映的电影有三部《房客》《拳击场》和《下坡路》,《拳击场》和《下坡路》的女性基本上是道德败坏的典型,再加上两年前的第一部电影《欢乐园》,都带有明显的希区柯克的“厌女”风格,而且故事的模式都是男女之间理不清的关系,或者两男和一女,或者两女和两男,情感的纠葛最后也总是以道德胜利论为结局。《房客》虽然也有两男和一女之间的矛盾,但希区柯克的重点显然没有放在这种俗套的道德故事里。而且,不仅没有表现出对女性鄙弃的“厌女”情绪,剧中几乎所有人物都是善的代表,黛西是友善的,黛西的父母是和蔼的,被怀疑是“复仇者”的“房客”也是对家人情深义重的人,而且充满嫉妒心的警官乔伊,虽然在情感上受到了一些伤害,但是最后还是救下了被自己误解的房客,还他一个清白——当然,电影中存在坏人,杀害女法女郎的真正“复仇者”当然是十恶不赦的坏人,对“房客”施以死刑的群众也是坏的代表,但是他们的形象都处在一种模糊性的状态中,“复仇者”甚至从来没有出场,而群众的坏都是一种劣根性的表现,坏只是一种概念,在没有被具化指称中,它们也只是为希区柯克的悬念服务。
第二是在拍摄手法上的惊艳,在《房客》拍摄之前,希区柯克去了德国学习,德国表现主义对他产生了影响,尤其是茂瑙的电影风格对希区柯克来说,变成了对固定叙事套路和风格的一种突破。《房客》片头被打出,另一个名字则是《伦敦雾夜奇案》,当字幕播放完毕,第一个镜头就是惊恐的女人张大嘴巴的尖叫,她的表情是扭曲的,她的头发是散乱的,她的目光是恐惧的——据说希区柯克利用玻璃的效果,她让女演员的头放在玻璃上,然后将头发散开,从下方照亮,就是一张扭曲变形的脸;之后是闪烁的霓虹灯出现的字:今晚节目,金发女郎,它既在灯红酒绿中消解了谋杀案带来的惊恐,又在都市生活的迷离中加深了系列谋杀案的惊悚感;之后是案发现场的画面,是目击者的采访片段,是被发现的“复仇者”纸条,上面是一个神秘的三角标志;然后是目击者说出了凶手的特征:高大,蒙着半张脸,而此时电话亭里给报社打电话的记者就蒙着半张脸;之后是新闻社里打字机对案件的报道:“第七名金发女郎被复仇者杀死”“被害人尸体与铁路沿线被发现”“目击者描述所见情形”“凶手遮住了半张脸”……之后则是新闻社加印报纸的场面,所有印刷机器都被启动;之后则是街上的人争抢购买这张“号外”,而报童还在四处叫卖,“复仇者”“第七件命案”……
| 导演: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
短短十几分钟,希区柯克利用视听语言编织了一个沉浸式地惊悚现场,他不断组织视听元素,又让每一个元素都传递惊悚的信息,闪烁的霓虹灯,正在书写的打字机,人群争抢报纸,所强调的信息最后所要表达的是:这是一个连环杀人案件,这是一个只杀金发女郎的凶杀案,这是一个只在星期二发生的谋杀案……它在反复,它在强调,在案件线索变成一种规律的时候,仿佛凶手就在眼前,无处不在却又找不到踪迹,所以这才是最令人害怕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凶手,每一个金发女郎都可能是下一个受害者——尤其在晚上,希区柯克利用玻璃、霓虹灯制造了光影,颇具德国表现主义的叙事风格。而在剧情推动中,这种表现主义风格也被不断运用:黛西家的13号房门在深夜被人敲响,房客的那只手就落在门上;在房客入住之后,邦达太太总觉得这个房客行为怪异,当她将这个情况告知乔伊的时候,几个人便听到了楼上房客的脚步声,此时希区柯克利用水晶吊灯的叠印效果,将楼上行走的身影和吊灯组合在一起,让人感觉到一种窒息;之后,这个吊灯叠印的效果几次出现,黛西看见了,乔伊看见了,它是对人们不安心理的具象化摹写;还有当房客在深夜出门,警惕的邦达太太起身去查看,画面中出现的则是房客沿着楼梯扶手下滑的那只手,它具有极强的视觉效果,快速滑动的纯粹动作带来的是一种无声的窒息感:他会去哪里?他为什么要偷偷出门?
当然,这一切都为了电影内在的叙事服务,希区柯克在这部电影中第一次使用了之后成为他标签的一种叙事风格:麦格芬。麦格芬,MacGuffin,它来源于希区柯克所讲述的一个故事:一列苏格兰火车上有个爱追根问底的人,他见隔壁的乘客带着一个形状很奇特的包裹,就问那是什么,乘客答:“麦格芬。”“什么是麦格芬?”“是在苏格兰高地捉狮子用的。”“可是苏格兰高地没有狮子啊。”“啊,这么说,也就没有麦格芬了。”“麦格芬”是一种不存在,但是它却在被说出被表达时成为一种存在,这种存在可以是一种虚构,可以是一种误读,但是在希区柯克的叙事中,就变成了一种线索,一种悬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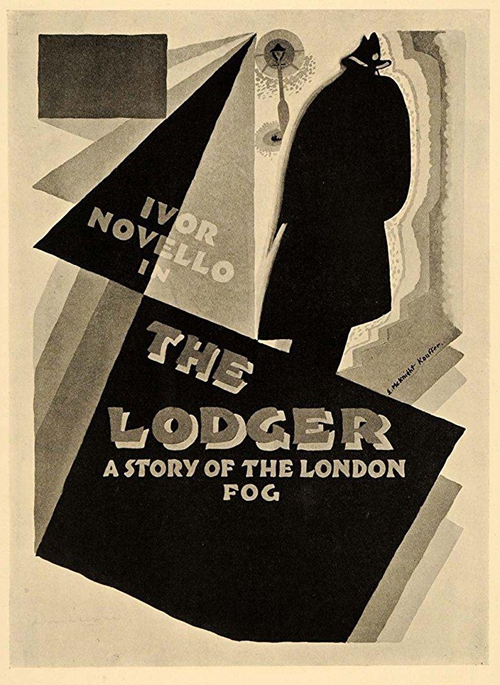
《房客》电影海报
《房客》中的“房客”就是一个“麦格芬”式的存在,在杀人案中它像极了一个纯粹的概念,是电影构筑的惊悚效果和恐怖氛围,赋予了它一种实存的可能,而希区柯克在最后几分钟的揭秘之前都在营造这个“麦格芬”。13号的房门被敲响,邦达太太小心翼翼打开门,夜雾中出现在门口的就是一个半遮着脸的男人;当他走进楼上的房间,看到了墙上那些金发女郎的画像,便要求将它们全部取下,说自己看不得这些;在房客一个人的时候,他将自己带来的一个黑色长条包放进了柜子里,然后锁上了柜门;在和黛西下象棋的时候,他对着金发的黛西说:“小心,我会抓住你的。”说的是下棋的事情,但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和杀人有关的计划……如此,夜雾中敲响门的手,半遮着的脸,对金发女郎画像的敏感,对黛西说“会抓住你”的“警告”,这些构筑了“房客”是复仇者的第一重可能。
之后邦达太太发现他深夜偷偷出门,走进他的房间防线柜子的门锁住了,而那天正是星期二,晚上凶杀案再次发生,另一个金发女郎丧命,那么,房客是不是就是“复仇者”?房客和黛西越走越近,他们甚至一起在夜晚出门,这引起了邦达太太的不安,乔伊犹豫嫉妒在街上找到了他们,在被黛西数落之后,乔伊从房客留下的脚印响起那盏吊灯,想起复仇者,于是他带人来到了房客的房间,搜出了那个被锁住的柜子,从长条包里找到了一把手枪,一张地图,一些和凶杀案有关的简报以及一张金发女郎的照片,这更是成为了直接的“证据”:手枪是作案工具,地图上标着的三角区域正是命案发生地,简报更是让他和案件脱不了干系,最重要的是金发女郎,它就是第一个被害者。在这些证据面前,乔伊当然将他当成了犯罪嫌疑人,给他戴上了手铐,但是房客却乘机逃脱,相信他的黛西和他一起来到了酒馆,在喝了白兰地之后群众认为他是凶手,于是在铁栏外面狠狠走了他,幸亏乔伊赶到,房客才被救下。
因为乔伊接到上面的指令:“啊,真凶已经抓到了!”因为房客对黛西说起自己的故事,那张照片上的女孩是自己的妹妹,她在那个夜晚被谋杀,之后母亲因悲伤过度而死去,所以他开始了对案件的跟踪,希望自己找到杀害妹妹的凶手为她报仇。所以“房客”不是嫌疑人而是受害者,是“复仇者”但是为了追杀凶手的复仇者——据说希区柯克还想在最后设置一个开放的结局:无法真正认定房客是不是凶手,他既可以是受害者,所有这些都是为妹妹复仇,但是他也可以是嫌疑人,他所说的只不过是谎言,两方面都可以自圆其说——但是希区柯克还是选择了一种明确的结局,房客不是凶手,房客得到了照顾,房客还以了清白,甚至房客获得了爱情,“所有的故事都有一个结局”,最后的结局是:房客和黛西走到了一起,他们相拥,而外面的霓虹灯依然在闪烁,“今晚节目:金发女郎。”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