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1-18《血的婚礼》:我是一个燃烧着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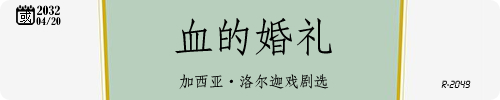
安古斯蒂娅(拉住她)你不能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开!强盗!丢我们家的脸!
马格达莱娜 放开她!让她走!到我们永远看不见她的地方去!
——《贝纳尔达·阿尔瓦之家》
一个叫嚣着“拉住她”,是不想让阿黛拉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只有“拉住她”才能制止她目的的达成;一个拼命要“放开她”,是因为让阿黛拉消失才会少一种对自己的威胁,才会不丢全家的脸。看上去“拉住她”和“放开她”是完全相异的态度,是完全对立的方式,但是对于最小的妹妹阿黛拉来说,两位姐姐的做法却是奇异的一致:她是家族的不幸,她是家庭的祸水,因为她竟然想获得自己的爱情。
安古斯蒂娅没有将她拉住,马格达莱娜也没有将她放开,在日趋紧张的争斗前,响起的是“一声枪响”,是母亲贝纳尔达让人拿来了枪,是母亲贝纳尔达要赶走被阿黛拉迷住的“罗马人”贝贝,但是枪声并不是贝纳尔达杀死了贝贝,“女人不会瞄准。”搅乱“贝纳尔达·阿尔瓦之家”秩序的贝贝已经骑马离去,枪声只是一声警告。但是贝贝之后,枪声之后,却传来了撞击声,它比枪声更响,也比枪声更具毁灭性:阿黛拉死了,她以自杀的方式反抗家族对她爱情的扼杀,只有在面对阿黛拉的死亡时,贝纳尔达这个被称为“暴君”的母亲才“哀其不幸”,“我的女儿死了,她是贞洁的!”但是用“贞洁”来形容女儿的死亡,不正是像安古斯蒂娅一样,认为她丢了家族的脸?不也正像马格达莱娜一样,是她去了永远看不见她的地方去?
作为贝纳尔达最小的女儿,年仅20岁的阿黛拉为什么要选择以这样的方式自死?“阴暗的寂静笼罩着舞台。”这是加西亚·洛尔迦在第一幕开场时的描写,阴暗和寂静的舞台就是“贝纳尔达·阿尔瓦之家”的象征,而且丈夫死去的时候这里正在举办丧礼,“她们围着巨大的头巾,身穿黑裙,手拿黑扇。”这更是整个家庭中女人的集体象征。但是在女仆蓬西娅看来这个家族真正的统治者是“周围所有人的暴君”的贝纳尔达,“她,最干净;最体面;最高贵。”对待女儿的婚姻和爱情,她也是至高无上的象征:她认为,“女人在教堂里,除了司仪神甫之外,不应看任何男人,可以看司仪神甫,因为他是穿裙子的。左顾右盼无非是在找汉子。”安古斯蒂娅是最年长的女儿,已经39岁的她是贝纳尔达第一任丈夫的女儿,她在丧礼上对她的指责是:“像你这样身份的女子,在为你父亲做弥撒的日子,跟在一个男人后面卖弄风骚,这正经吗?”而对于30岁的马格达莱娜,她提出了做女人的本份,就是整天要坐在这黑屋子里;27岁的女儿阿梅里娅则感慨:“出生为女人就是最大的惩罚。”
虽然如此,安古斯蒂娅却要马上结婚了,结婚的人就是“罗马人”贝贝,而这桩婚姻在阿黛拉看来,就是因为安古斯蒂娅有钱,“ 看上了你的钱!”在这里阿黛拉这样对姐姐说,实际上就显示出了她的反抗精神:因为她爱着贝贝,她知道贝贝也爱着她,“我的身体将属于我喜欢的人。”这就是阿黛拉爱情的宣言,但是正是这样的爱情,偷偷摸摸不算,还被几个姐姐所监视,或者在另一个意义上,她们也成为了贝纳尔达的帮凶,女人和女人组成的联盟变成了对自由爱情的扼杀。但是越是在这样的暴君面前,阿黛拉越是不肯屈就于命运,越是要争取自己的幸福。在丧礼的时候,她就喊出了“我要出去”的呼声,“我不能关在家里。我不想像你们那样,变得人老珠黄。我不想在这些房间里失去自己的洁白;明天我就穿上绿色套装到街上散步去。”当蓬西娅让她死了和贝贝在一起的那份心,阿黛拉告诉她:“要扑灭从我的双腿和口中升起的这股烈火,不仅你无能为力,因为你是个佣人,就连我母亲也是无能为力的。”
| 编号:X38·2241107·2201 |
火就成为洛尔迦笔下爱情的象征,爱情在女人心里是一种力量,这既是彰显自我的力量,更是摧毁旧势力的力量。而在火之外,血就成为悲剧性的象征,鲜血也有火一样的颜色,但是血往往指向了最后的死亡——火也是悲剧性的,它激发为一种摧毁一切的力量,但是火也会燃烧自己——血与火便成为洛尔迦的母题。面对自己内心熊熊燃烧的爱情之后,阿黛拉对蓬西娅说的是:“我一看见他的眼睛,就好像在慢慢地喝着他的血似的。”其实五个女儿都想要属于自己的爱情,她们也都在酝酿这一场风暴,但是唯独阿黛拉抵达了血与火的世界,她不害怕死亡,“我见过这屋顶下面的死神,我要追求本来就该属于我的东西。”她敢于反抗权威,贝纳尔达说:“那是天生的坏女人的床!”并愤怒地走向她,阿黛拉竟然夺过母亲的拐杖并将其撅为两段,拐杖就是权杖,是权力的象征,阿黛拉摧毁了权力的象征之物时就说:“这监狱的训斥已经结束了!我就这样对付统治者的棍棒。”而她最后的自死无疑就是反抗最极端的表现,在那一刻她死了,但是如血一样祭奠了宗法家庭,如火一样烧毁了女人自设的权力世界,正如马蒂里奥最后的感慨:“她比活着要幸福千万倍。”
以血与火的勇气,通过血与火毁灭权力,这就是阿黛拉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而在洛尔迦反映安达卢西亚妇女悲惨命运的“乡村三部曲”中,《血的婚礼》和《贝纳尔达·阿尔瓦之家》同样燃烧着火,同样流淌着血,同样用一种死亡换来了自由。新娘即将和新郎结婚,这个曾经在十五岁时爱过莱昂纳多的女人现在也要走进婚姻殿堂,而莱昂纳多也早已经和妻子结婚,但是多少年过去了,这一段感情却始终在莱昂纳多和新娘心里,即使新娘对新郎说自己爱着他。但是对于新娘来说,结婚的意味却是对自由本身的毁灭,新郎的母亲说:“一个男人,几个孩子和一堵宽不足两米的墙,这就是一切。”女佣对婚姻的解读是:“是一张闪光的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几个数字就注解了婚姻的本质,这是不是毫无希望的生活?这是不是像曾经居住的窑洞一样的囚禁?当莱昂纳多的马匹响起,它搅乱了新娘的一切计划,尤其当他对新娘说:“沉默和煎熬是我们对自己最大的惩罚。”而对于新娘来说,真正悲剧的不是平淡和束缚,而是男权思想的渗透,就像母亲对新郎所说:“别让她不高兴,但要让她感到你是个男子汉,是主人,是指挥者。”
在这样的婚姻面前,在这样的规则里面,新娘终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她跟随着莱昂纳多逃离了婚礼,以血与火的激情进入到了自由世界,但是血与火对于她来说也意味着悲剧的开始。在现实主义构筑之后,第三幕中洛尔迦完全以超现实主义的方式推进了最后的悲剧:在夜晚的树林里初夏了三个砍柴的人,他们预言了流血的结局,一个说:“—个早就在欺骗另一个,归根到底,血更厉害。”另一个则是:“要走血的道路。”第三个说:“宁可流着鲜血死去也不带着腐烂的血活着。”第四个说:“但是那时他们的血液已经混在一起了,就像是两个空坛子,两条干涸的小溪似的。”砍柴人对血的注解既包含了他们的抗争,也注解了他们的死亡;之后是月亮,它在舞台上就是一个年轻的樵夫,“然而今夜我的面颊/将染上鲜红的血”;之后出场的是老妇人,她是“叫花婆”,就是死神,“他们过不了此地。树干的细语与河水的流淌,将扼杀叫喊声放荡地飞翔。就在此处,顷刻之间。我已经疲倦。”
莱昂纳多骑着马,他的逃离也是对于婚姻的背叛,这是戏剧中唯一有名字的人,“莱昂纳多”就是“狮子”,是力量的象征;新娘跟随着莱昂纳多,她甚至比莱昂纳多更具勇气和力量,“我爱你!我爱你!走开吧!如果他将你杀死,我会用带紫罗兰花边的裹尸布将你包裹。”当月亮出来,当叫花婆现身,就像《贝纳尔达·阿尔瓦之家》中枪声和爆破声制造的声音效果一样,“两把小提琴奏响。突然有两声长长的让人心碎的叫声,提琴声中断。”然后便是寂静,之后就是叫花婆的喊声:“丧命,是的,丧命。”声音的跌宕预示着情节的快速转换,更是印证着命运的变化,最后出场的是披一条黑纱巾的新娘,“我是一个燃烧着的女人”,她对新郎的母亲说,新郎就是一个像水的小孩,冰冷,自己也不想让他成为自己的归宿,她需要的是大海,“那另一个男人的手臂就像大海的冲击,就像骡子甩头一样地拖着我,他会永远地拖着我,永远地,永远地,即使你儿子的所有的子孙都抓住我的头发!”
|
| 加西亚·洛尔迦:我就是自由! |
同样是爱情所燃烧的火焰,同样是反抗汇聚的血河,同样是走向毁灭的火和血,也同样在死亡中获得的自由,《贝纳尔达·阿尔瓦之家》和《血的婚礼》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同样是关于女人的自我解放,只不过在《贝纳尔达·阿尔瓦之家》中,这种反抗是在家庭内部展开的,《血的婚礼》则是对“新郎”和母亲的反抗,而从女人的身份来说,阿黛拉是追求自己幸福的未婚女性,新娘则是即将嫁做人妇、踏入婚姻世界的女性,她们的状态不同、身份不同,面对死亡的方式不同,但是洛尔迦却给了“女人”相同的命运和对待命运相同的方式,未婚自死和走向婚姻殿堂时的逃离,共同构筑了关于“女人”对家庭最决然的反抗:她们没有真正让自己成为规则、道德的牺牲品。但是作为“三部曲”的《叶尔玛》,叶尔玛的身份却是踏进了婚姻世界的女性,面对婚姻,面对丈夫,面对这个家,她又如何唤醒她内心的火?又如何制造最后的流血悲剧?
第一幕开始的时候,叶尔玛和丈夫胡安结婚已经二十四个月,之后他们的婚姻进入了第三年,到了第二幕的时候他们已经是五年的夫妻了。时间在流逝,对于叶尔玛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她始终怀不上孩子:她独自一人的时候,面对着针线笸箩问自己:“你的第一个摇篮用它做成!你的肌体几时散发茉莉的幽香孩子呀,你几时才能降生?”她对邻居马丽亚说,生儿育女对于女人来说就是受苦也在所不辞,“为了看着他们长大,我们就得受苦。我想我们要费掉一半的心血。但这是高尚的、健康的、美好的。”当三年了还没有任何反应,叶尔玛也只能自我发问:“您知道。我为什么不生育呢?难道我全部的生命力就只是为照管家禽和给我的小窗户装上熨好的窗帘吗?不。您一定要告诉我该做什么,我什么事情都肯做,哪怕是让我把针扎进眼睛里最娇嫩的地方。”洛尔迦之所以将她取名叶尔玛,是因为“叶尔玛”的原意是“不生长树木的、无法耕种或未经开垦的土地”,这暗示着叶尔玛无法生育的命运。但是,这是叶尔玛本身的宿命吗?
她回忆起了十四岁时的维克托,“他抱着我,跳过一条水渠,我颤得直打牙。可那是因为我害羞。”那是关于爱情的第一次甜蜜回忆,正因为这个爱情的回忆揭示了叶尔玛的命运,她和胡安结婚,婚姻是冰冷的,“难道就是为了找男人而找男人吗?他把你放在床上,让你用悲伤的眼睛望着天花板,然后转过身就睡,那么这时候,你会怎么想呢?”在和胡安的对话中,胡安强调的是家庭的名誉,强调的是共同的职责,而叶尔玛却想要孩子,而孩子并不只是孩子,而是爱,“我想喝水,可是既没有杯子也没有水,我想上山,可是没有脚,我想绣自己的裙子,可是找不到线。”在胡安只要名誉和职责的世界里,叶尔玛何来真正的水?她去神婆多洛雷斯家求子,多洛雷斯说胡安是个好人,叶尔玛知道他不坏,但是生活完全没有激情,“他沿路放羊,晚上数钱。当他跟我睡的时候,他尽了自己的义务,可我觉得他的腰是凉的,好像是个死人的尸体。”而自己呢?渴望水的滋润,更渴望火的燃烧,“而我呢,尽管我一向讨厌狂热的女人,可在那个时候也愿意像座火山似的。”
《贝纳尔达·阿尔瓦之家》里的阿黛拉说自己拥有“我的双腿和口中升起的这股烈火”,《血的婚礼》中的新娘“是一个燃烧着的女人”,《叶尔玛》里的叶尔玛内心像座火山一样,三个女人都有火的激情,它们是爱情的象征,更是驾驭自己命运的力量,如果说未婚的阿黛拉和新婚的新娘组成了婚姻外反抗的力量,那么叶尔玛则成为了婚姻内部的更具革命性的反抗者,在最后的神庙里,洛尔迦设计了雌面具和雄面具上场,“雄性的拿着一只牛角。一点儿也不粗野,相反却很优美,并具有纯朴的乡土气息。雌性的挥舞一串大铃铛。”雄和雌象征着男人和女人,但是他们都戴着面具,而这也成为压抑个性的象征,于是洛尔迦笔下关于安达卢西亚妇女悲惨命运被更强大、更颠覆性的力所破坏,当老妇只是劝叶尔玛“可以离开你的家”,叶尔玛没有选择像“新娘”一样逃亡,也没有如阿黛拉一样自死,“住嘴!住嘴!没那回事!我绝不会那么做!我不会去的。你以为我会去找另一个男人吗?我的名誉往哪儿摆?水不会倒流,月亮也不会在中午出来。去你的吧!”她自己没有离开,而且她掐住了丈夫的喉咙,“她掐住他的喉咙直至将他掐死。响起庙会的歌声。”
为什么叶尔玛最后会以这样的方式对抗命运?她曾经问胡安:“你寻求的是房子、平静和一个女人。然而仅此而已。我说的是真的吗?”胡安的回答是:“是真的。像所有的男人一样。”在这一刻,叶尔玛的反抗不是对自我命运的反抗,而是对代表着女性整体对工具论的反抗,女性之所以被束缚住了,是因为她们是权力的统治物,是因为她们自己没有自由,所以掐死胡安不是掐死丈夫,而是掐死权力、男人,掐死规则、秩序,“你们别靠近,因为我杀死了自己的儿子,我亲手杀死了我的儿子!”自己的身体不会生育了,即使会生育不也是生出了制造悲剧命运的“儿子”,他也会成为男人,成为丈夫,成为父亲,成为胡安,“像所有的男人一样。”
掐死丈夫,而且彻底掐死男人,就是叶尔玛比阿黛拉和新娘更彻底的地方,洛尔迦的“三部曲”构筑了不同身份女人所组成的“女人的一生”,从未婚到即将结婚到已经结婚,也完成了血与火的对抗三部曲,从自死到他死再到杀死男人。洛尔迦的“三部曲”虽然书写的是女人的反抗,但其实是所有弱势群体的反抗,“这三幕的场景应具有纪实性。”《贝纳尔达·阿尔瓦之家》的这一“作者提示”不只是对戏剧布景的要求,“纪实性”更是指向了戏剧具有的现实意义,1925年1月8日于格拉纳达首演的《马里亚娜·皮内达》就是洛尔迦的一次“政治宣言”,马里亚娜在家里缝制自由的旗帜,是为了自己的爱人堂佩德罗,而堂佩罗所在的共济会同盟就高举反抗国王的旗帜,最后马里亚娜被抓住,然后送上了绞刑架。马里亚娜为什么冒死缝制那面自由的旗帜,表面上是为了爱情,但是所谓的爱,在洛尔迦那里并不是单一的爱情,也是对自由之爱:既是用爱来争取自由,也是以“爱自由”的方式反抗专制,所以马里亚娜便成为了“自由女神”,“我就是自由,人们令我痛苦!爱情,爱情,爱情,和永恒的孤独!”
马里亚娜的选择已经超出了单一女性的态度,它是对现实的反抗,这是“格拉纳达的日子多么悲痛”的不公,这是“连石头也会发出哭声”的压抑,这是“西班牙的河流已变成长长的锁链”的暴力,所以洛尔迦呼唤“自由女神”,于是真正的火焰在燃烧,“自由!为了你永不熄灭的高尚的火光,我愿奉献全部生命。”这一片火光也照亮了洛尔迦,在创作完《贝纳尔达·阿尔瓦之家》两个月之后,洛尔迦就被法西斯杀害了,但是他留下了诗歌和戏剧,留下了自由之声,“我就是自由,因为这是爱的心愿!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9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