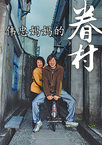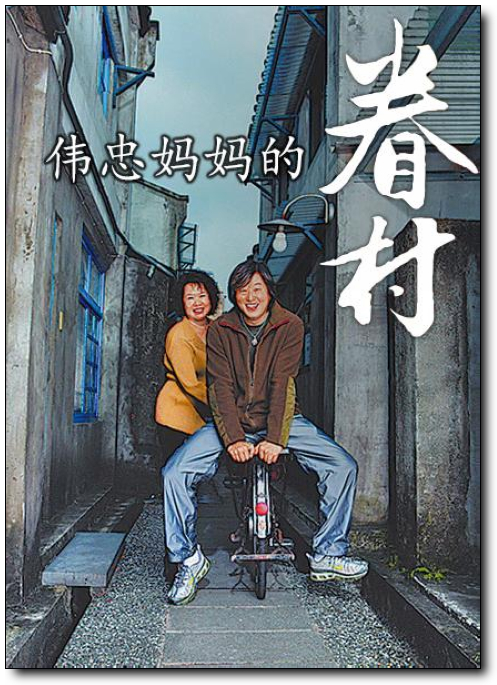2015-06-17 《伟忠妈妈的眷村》:从游子变居民的集合

对于眷村这个大集合来说,“伟忠妈妈”是个形容词,不是伟忠一个人的妈妈,是所有眷村第二代的妈妈,也是眷村第二代的所有妈妈,他们叫女大大,叫吴妈妈,叫周妈妈,或者也叫颜爷爷、陈爷爷、任伯伯,他们居住在台湾嘉义的建国二村这个眷村里,54年前,他们从官兵变成游子,54年来,他们从游子变成居民,当这个生活了54年的村子被拆迁的时候,对于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伟忠妈妈”来说,意味着漫长的生活集合被打破,意味着点滴的故事将变成记忆,也意味着眷村最终被定格成一条街路、一块门牌以及一幅油画。
对于建国二村这个普通的眷村来说,54年前的那次事件成为他们集合在一起的起点,民国38年在眷村妈妈的记忆中,总是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离开故乡离开大陆,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岛屿,陌生的村子里,对于每一个妈妈、伯伯来说,都是一种偶然而成的必然。那时这里只有单薄的竹篱笆,只有破旧的空房子,只有日据时代留下的痕迹,临时搭建的简易房分给地勤人员,而地勤人员似乎羡慕空勤人员在对街的另一个眷村待遇,但是却庆幸自己不会在空战中被战死。54年前的记忆里原本是青春,却变成了战火,原本是爱情,却变成了撤退,伟忠的妈妈孙绍琴因为怕王爸爸被“抓小车”而回去受罚,只好和王爸爸的母亲、妹妹来到了这里;19岁的女大大刚刚订婚,就和王大大一起离开了北京南苑的家;在军中乐队唱戏的吴妈妈订婚不久,也从塘沽坐船一直到了这个陌生的地方。
|
| 导演: 王伟忠 |
 |
他们来自大陆的各个省市,各个民族,一道简单的竹篱笆其实不是永远的隔绝,当被拆除,便是通融的开始。不同的习惯,不同的风俗,其实带来的是一种多元的融合。“一开门就像个大院一样,没有吵闹过,没有不愉快。”吴妈妈在54年后还是充满了感恩。由于生活清苦,很多眷村的妈妈开始开铺子卖包子、米糕、萝卜干,以补贴家用,有的甚至是自己家窗户一开,便吆喝起来。周妈妈似乎是最勤手的人,她是台湾媳妇,嫁给了眷村的士兵,她向眷村的妈妈学习包粽子、水饺、馄饨、汤圆,也把这些东西分给眷村妈妈和孩子们吃。周妈妈的身份似乎是最具有融合意义的,而在她生孩子难产的时候,也得到了这里妈妈们的帮助和关心,大家把她送到医院,然后剖腹产的时候,浦妈妈一刻也没有离开,而等到大出血被治好母子平安出院的时候,王伯伯又拿出自己的钱给她度过难关。
|
|
| 《伟忠妈妈的眷村》海报 |
剖腹产、大出血毕竟是一件大事故,而对于眷村的妈妈来说,他们像一家人更在各种细微的小事上。孩子奶不够了,就找有奶的妈妈喝上几口;小孩子回家没人带,就交到邻居的手上,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大家没事的时候坐在一起聊聊天,各家有什么东西也拿出来大家分享,谁家的孩子有对象了,从巷子里走过,妈妈们看着不说话,直到他们走过去了便张家长李家短地议论,但是这种议论从来不讲坏话,言语之间是深深的情谊。而被称为“女匪干”的女大大,当初和王大大一起做包子的时候,就是吵架,在王伟忠的记忆中,他们没有一天不吵架的,吵架的时候甚至忘了收包子的钱,他们卖了一辈子包子,也就吵了一辈子的架,但是这种吵架也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永远的人生风景,而对于街坊邻居,总是充满着微笑,充满着快乐,而在这个眷村里,也每天弥漫着包子铺里飘出的浓郁香味。
54年来永远的风景是女大大和王大大的争吵,是阿婆米糕店那一辆从来没有换过的小推车,是巷子里那一排排的破椅子,是村口那一颗渐渐长大的榕树,而54年来的眷村,在妈妈伯伯之后的第二代第三代,也都成为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融入了这个大家庭。在王伟忠的记忆里,建国二村的菜市场成为他们游乐的最佳场所,下午的摊位基本上都空了,他们便在那里用手抓一大把的苍蝇,或者在巷子里躲猫猫,玩官兵捉贼的游戏,女大大的二儿子王新民出生在这里,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眷村,每天也都随着女大大一起推车做包子,所以在这里,有太深太深的感情。而同为出生在这里的第一代,王伟忠的姐姐也深刻感受到了眷村妈妈的那种胜似亲人的亲情。
但是,这54年的风景却面临着被拆迁,由于城市改造的需要,建国新村将被完全拆除,这对于在一直居住在这里的妈妈们来说,变成了一件难过的事。孙绍琴说,虽然这里又破又烂,那些搭建的东西也不安全,但是真的要搬走还是很舍不得,四个孩子在这里出生,自己的大半辈子在这里,虽然过得并不富有,但是这里总有回忆,“总是住了50多年的家。”点滴的回忆总是渗透在每一个妈妈的心里,其实也影响着这里的每一个老人,虽然颜爷爷一家26口人23人在美国,但是为了过不习惯美国生活的妻子,还是留在这里陪伴终老,那院子里50多年的树其实是这里生活的见证,“拆了还是要陪着她。”而陈爷爷说,一辈子没有一定的住处,搬哪里也都一样,但是看着舍不得离开的陈奶奶,陈爷爷也说出了在这里积聚的感情:他们邻居比亲姐妹还好,比妯娌还好,她不想搬啊。而任爷爷虽然说不再回大陆了,但是一提起自己分别几十年的兄弟姐妹,还是很想他们,而这种想念在这个住了50多年的眷村里得到了一丝慰藉。
过了这个春节,建国二村就要拆了,拆掉竹篱笆,拆掉深深的巷子,拆掉破旧的房子,甚至拆掉这里的点滴记忆,是的,当这里的阳春面、褪色国旗、小时候的奖状、豆棚瓜架、路边盆栽、破旧的藤椅,狗屋都被拆除的时候,54年的记忆也将变成老人最后的交谈,变成离开时的寂寞影子,变成那一幢幢在没有分别的新家园。拆除眷村之后,他们都将搬到经国新城里,这是现代化的小区,44幢大楼,每一幢高12-14层,2000多户的眷村人口,这是新的集合,但是这崭新的房子没有记忆,没有故事,甚至每一幢每一户都是相同的,都容易迷路,都紧关着门。
所以当眷村的记忆被整体拆除之前,伟忠和妈妈策划了最后一次除夕联欢晚会,将所有眷村的妈妈、伯伯、爷爷以及第二代都请了过来,大家又唱又跳,大家欢聚一堂,叙说着故事,讲述着生活,但是有欢笑也有悲伤,有相聚终有离别,那璀璨的烟花照亮又冷又雨的夜空的时候,其实生活在这个大集合里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意味着不舍,意味着离开。抽签、装修、搬家,当新家迎来自己的主人的时候,也是眷村完全变成记忆的时候。而对于这一份维持了54年的记忆,任何人都不会轻易抹去,而伟忠妈妈将眷村的那一块门牌钉在了自己房间的门上,民国路,四巷25号,蓝色门牌上的这些白色地址似乎是伟忠妈妈一生的记忆,和房间里那张54年前的北平大地图一样,希望的是孩子们能永远记得陪伴大家的眷村记忆,房子可以被拆除,而只有记忆是永恒的。
2006年的中秋,伟忠妈妈和伟忠,以及伟忠的孩子一起来到曾经的眷村时,这里的房子已经被拆除,而曾经自己居住了54年的家却变成了一条马路,站在马路的中间,伟忠妈妈说,我家就在这里,就在这里,那一刻是留恋,是无奈,是心酸,好像那破败的墙上残留着笑声哭声,那再也找不到家的旧址里还有浓得化不开的回忆和故事,“感情可以世世代代留下来”,那一块门牌,一张地图,一幅油画,似乎都是寄托着不变感情的载体,可是54年,当从政治的集合变成生活的集合,当士兵变成游子又从游子变成居民,对于眷村的妈妈来说,他们不是失去了什么,而是得到了许多,那是一种无法忘怀的感激,是留在内心的记忆,是融合的亲情,而最终成为了永不褪色的眷村文化,成为共生共存的时代符号。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850]
思前: 《拔一条河》:天灾面前如何抬头?
顾后: 看不见的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