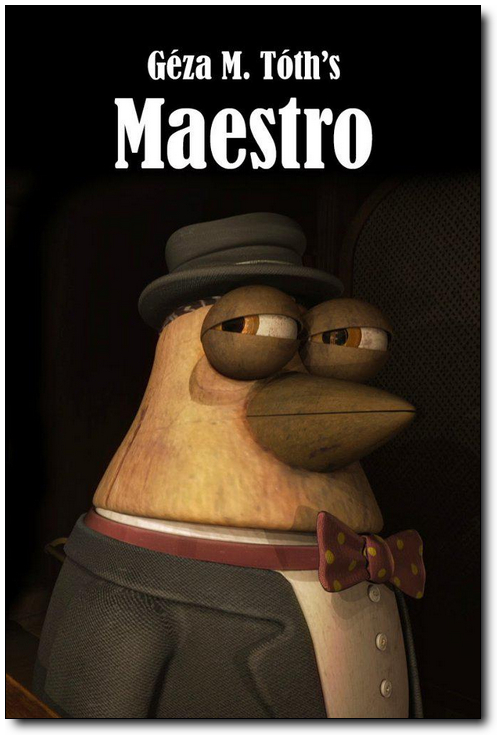2016-10-27 《大歌唱家》:并不只为他人鸣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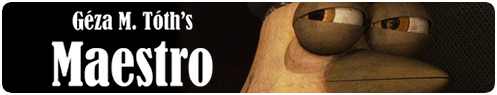
五分钟之前,一杯舒润咽喉的饮料已经被精心调制好;四分钟之前,黑暗的空间里亮起了灯;三分钟之间,穿着礼服的小鸟开始被从头到脚被打扮;两分之前,坐在那里的小鸟已经被事无巨细地打扮一新;一分钟之前,准备工作已经做完;10秒之前,空间里的灯被熄灭,小鸟最后被系上了紫色的领结——我们的大歌唱家终于要迎来一场重要的演出,那扇门被打开,刺眼的光亮照进来,小鸟被推出去,然后是两声短暂的报时。
出乎意料的结局,在字幕开始的时候,背景是嘈杂的人声,是依稀的歌声,是耀眼的追光,似乎置身在一个豪华热闹的剧院里,底下坐着无数聆听大歌唱家美妙歌声的观众,而这个空间便是小鸟准备登场的幕后。从调制饮料到涂脂抹粉,从刷净衣服到更换领结,一切的准备工作都事无巨细,都为了最后两秒的精彩表演,可是,充满期待的歌唱家演出最后却只是维持两秒的报时,似乎是颠覆,似乎是反转,底下或者根本没有座无虚席的观众,但这鸣叫,却都为了服务他人,为了提醒他人。
|
| 导演: Géza M. Tóth |
 |
|
|
| 《大歌唱家》电影海报 |
在系统里,控制一切的就是这收放自如的机器手臂,而在没有人的空间里,机器手臂背后必然站着另一个控制者,他没有现身,却掌控者一切,而幕后的指挥者其实就是设置好的程序,当程序、机器完美无差地将整个过程按照计划演绎,其实对于小鸟来说,他只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他的出现,他的鸣叫,他的报时,是不可或缺的,他面向他人,却完成了最后一个任务。但是在系统里,他却只是一个没有自我、没有主动性的零件,所以这一场重要的演出,从来不会有错误,从来不会出问题,在被控制的世界里,一切都是准时的,一切都是单一的,一切都没有悬念。
但是在被控制的过程中,为什么会产生一种意外的感觉?为什么会想象一场精彩的演出?为什么被置换成一次简单的报时会有失落感?为什么有一种从系统控制论中挣脱的欲望?其实,从这一只早已经成为某一个零件的小鸟身上,我们却能够发现一些系统外的可能,一些不被完全控制的意念。那面镜子,那盏灯,似乎就是系统外的道具,如果这是一个完全机器化的空间,完全被机器手臂控制,那么放置一块大大的镜子,点亮那些灯,根本没有任何意义,这个空间不需要被照亮,不需要被反射,不需要被看见。但是,镜子和灯光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营造一种舞台幕后的效果,让人有一种进入其间窥视的欲望。不仅于此,镜子立在小鸟前面,镜子前又亮起了灯,所以在更深的意义上,是为了让小鸟有限地看见自己,不致在黑暗中迷失。镜子是一个存在的世界,一个活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光亮,有影子,有反射,也有一模一样的自己,所以,镜子的存在意义就是为了找到那一个不曾完全失去的自我。
当小鸟被机器手臂控制着进行打扮,虽然他自己不用动手,自己对一切无能为力,但是他可以看见,可以观察,可以记住,所有这一切的动作和影像都进入了小鸟自己的世界,它们和演出无关,和报时无关,当然也和系统无关。这是小鸟自我存在的一个标志,而另外,小鸟也在想方设法寻找属于自己的一切,当机器手臂正在忙碌的时候,小鸟开始发声,那是抒情的歌声,和短暂而单一的报时声音不同,从内心发出,从喉咙深处传递,完全是一个大歌唱家必备的嗓音,最后在这个空间里回荡,所以这个声音是属于他自己的,它不受机器手臂的控制,也不再系统之内,当然更不是整个程序的组成部分。
而同时,当机器手臂按照程序设定从小鸟身边拿走饮料的时候,小鸟似乎还没有完全喝完那一杯饮料,甚至还不肯马上让嘴巴离开那根管子,顺着机器手臂的方向,几乎开始倾斜了身体,而目的就是为了喝到最后一口饮料。小鸟变形的动作,不舍的心情,也正是一种凸显自我欲望的表现。而其实,在机器手臂有条不紊进行准备的过程中,小鸟的脸上显出的是一系列的微表情,他有时是茫然,有时是不解,有时是思考,有时却是责怪,这丰富的微表情出现在小鸟真实的脸上,也出现他面前的镜子里,所以在双重的变化中,折射出小鸟不甘于成为系统一部分的心理,不甘于被机器控制的想法,甚至不甘于成为一个为他人服务而失去自我的零件。
从镜子里看到自我,在歌声中保留自我,在微表情里展现自我,小鸟不是彻底的零件,小鸟还有小小的自我意识,这是难能可贵的,这在系统社会里的制造活力,在被控制社会里表现自我,所以,这样一种反讽的方式使得被机械化的“大歌唱家”世界里,存在着一点光,一点照亮自己的光,一点温暖观者的光。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2674]
思前: 历史演义与法的精神
顾后: 《某个旅人的日记》:奇遇一如未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