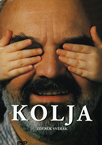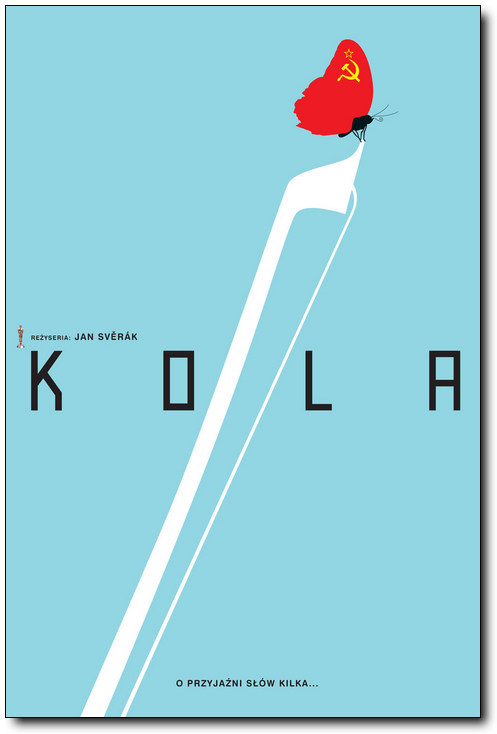2017-03-06 《给我一个爸》:政治错位下的温情回归

他回到了布拉格,在那一间自己租住的房子里,1986年乐队合影的旁边多出了一张孩子手拿玩具的照片;他和妈妈坐上了飞往苏联的客机,望着窗外的云层,他用稚嫩的小手抚摸着舷窗,仿佛是在和底下的这片土地告别——一个是捷克的父亲,一个是苏联的孩子,当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故乡,并不是一种永远的分离,照片和小手,在相隔的距离中仿佛又走向了一起,就像他们在机场分开时他深情地叫了一声:“再见,爸爸。”
“爸爸”,不再是一个虚构的身份,不再是一种欺骗的称呼,对于5岁的孩子柯利亚来说,他已经找到了缺失的父爱,照顾他,关爱他,虽然讲着不同的语言,虽然分属不同的国家,但是在“给我一个爸”的孤寂中满足了最后的心愿;而对于卢卡来说,那一声“爸爸”又把他拉进了一个充满亲情的世界,甚至让他告别了曾经的疏离,曾经的自我——重新回到交响乐团,重新投入爱着的女人怀抱,也重新开始了成为一个父亲的准备。
爸爸,一种缺失的状态,其实也是1988年捷克的现实隐喻,在东欧发生巨变的政治生活中,苏联的影子却无处不在,他们开着军车穿行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乡间,他们的国旗必须挂在每一户普通市民的加重,他们的新闻总是在欧洲之声的电台里播出,在社会主义的阵营里,苏联总是扮演着解放者和控制者的角色,而这样的政治生活也渗透在普通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日常生活中,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多变的政治环境,让他们找不到属于自己真正的父亲,找不到可以喊出一声“爸爸”的父爱。
|
| 导演: 扬·斯维拉克 |
 |
对于卢卡来说,选择这样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拒绝成为一个社会人和政治人,在音乐、女人的世界里,在独处、自由的生活里,他似乎远离了被赋予的那个“父亲”的称呼。而其实,这种避世主义难以逃脱现实的困境,他在葬礼上拉大提琴,收入不多,却欠下了太多的债,为了能买一辆二手车,他几乎想方设法要去赚钱,自己在空闲的时候去修整墓碑,金字5克朗一字,银字3克朗一字,在和墓地家属讨价还价之后,便一个人坐在空寂的墓地里,一笔一划地修整墓碑。葬礼、墓碑,卢卡面对着那些逝者,仿佛自己的生活也困在这样一种死寂的世界里。
当掘墓人布罗兹介绍他一笔交易时,卢卡的生活才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布罗兹告诉他有一个苏联女人娜杰兹达想要通过和捷克人假结婚的方式获得捷克身份,所以要卢卡成为她的“丈夫”,交易的条件是举办婚礼,然后在六个月后离婚,而假结婚的报酬是四万克朗。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拥有了它完全可以不必去目墓地,完全可以买一辆二手车,所以卢卡答应了。而其实,假结婚看起来是一次简单的交易,但是却完全在卢卡控制之外,一个苏联女人通过非法的手段获得捷克身份,本身就有着某种政治上的“阴谋”,而更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他们举办婚礼不久,娜杰兹达在拥有了捷克身份之后,又去了西德,和自己朝思暮想的情人汇合。
|
|
| 《给我一个爸》电影海报 |
忽然就变成了一个政治事件,苏联人到西德,就是一种叛逃行为,而接受了这个交易的卢卡自然被警察调查。到这里为止,似乎还不足以颠覆卢卡的生活,因为他毕竟只是参与了假结婚这一单纯的事件,但是社会形势的复杂性,最后把他整个卷了进去。而真正改变他的,不是一种和政治有关的交易,而是娜杰兹达留下的那个五岁孩子柯利亚,成为他颠覆生活的开始。娜杰兹达去往西德,把孩子留给了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姑妈,而姑妈却身患重病,最后把孩子托付给了卢卡,本来期望着两个星期姑妈的病情好起来,却不想竟然在医院里逝世,卢卡最终成为柯利亚这个苏联孩子唯一的亲人,也最终使他变成了“爸爸”。
似乎是一步一步走向了无可奈何的反面,其实作为一个独身主义、避世主义、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卢卡来说,他的生活并不能真正脱离现实,他失去交响乐团的工作是政治原因,因为当局让他报告出国演出接触过的所有人,他因为不合作而被乐团解雇;他的兄弟早就移民到西方世界,而他的母亲住在捷克斯洛伐克乡下,面对每天在家门口来往的苏联军车,母亲总是抱怨甚至愤怒地对他讲:“当初苏联进攻时,他们连水也不给,而现在却狼狈为奸。”所以她敌视着这些穿着军装的苏联人,她以关门关窗的方式拒绝看见他们,甚至不理会他们讨要水洗手的要求。
所以在1988年的政治大背景下,卢卡的生活其实是错位的,母亲对于苏联是抱怨、反对,甚至是敌视的,而自己成为“爸爸”之后,却带着一个苏联的孩子,这种错位在他带柯利亚回到母亲的乡下时,便将他推向了尴尬地境地。柯利亚看见窗外的苏联军车和军人,在一声“这是我们的”之后便兴奋地跑出去,用俄语和他们打招呼,戴上苏联军帽,然后学着军人迈步。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种在异乡获得的归宿感,就像他在卢卡的房间里看到贴着的苏联国旗,对他说:“还是我们的好看。”
“我们的”是柯利亚的身份认同,但是对于卢卡的母亲来说,却加深了那种仇视感,“我不喜欢俄国人。”不仅是针对外面的那些苏联人,也针对面前这个需要他照顾的孩子,她用了一个比喻说:“捷克母鸡生了一个俄国的蛋,却还不知道。”这是对于政治有关的序列关系的一种嘲讽。在这样的境况中,希望躲在音乐和女人世界里的卢卡,第一次在错位中面临一种抉择,他离开母亲,他照顾柯利亚,他成为他的“爸爸”。
让他成为“爸爸”,一开始是被动的,无奈的,那个所谓的姑妈逝世了,自己的母亲痛恨苏联人,作为假结婚的“丈夫”,他自然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他给柯利亚换上了鞋子,他给柯利亚吃东西,他是冷漠的,柯利亚则是沉默的。对于柯利亚来说,感兴趣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垫着凳子看窗外磨喙的鸽子,甚至有时候他还打开窗,让他们进来,给它们喂食,和自己在一起。鸽子是一种寄托,似乎也成为一种渴望和平的象征,或者在与鸽子相处一室的隐喻中,卢卡发现了在孩子身上的那种童真,那种去除了政治、国家和语言隔离之外的现实。
他带着柯利亚去葬礼演奏现场,给他洗澡在澡盆里放上“汽船”,他从老家的箱子里找出提线木偶让他玩,就像捷克语和俄语发音相同的“茶”一样,卢卡渐渐在柯利亚身上找到了两个人的共同点,即使在柯利亚洗澡的时候和前来学习大提琴的女学生调情,但是对于卢卡来说,再不是只有自己了,他开始牵挂这个特殊的儿子,他开始审视自己作为“爸爸”的特殊身份。为了不让柯利亚伤心,他包场让他在电影院看苏联动画片;为了亲近柯利亚,他带着他去野外的河滩边,在晒着太阳的大石头上给他讲水獭的故事;为了让柯利亚安然入睡,他深夜打电话给曾经的女友让她在电话里讲故事;为了救护发高烧的柯利亚,卢卡叫来了克拉娜给他吃药,整夜守护着他,让克拉娜第一次感觉一个做父亲的责任感:“没想到你这么关心别人的孩子,我觉得你根本不自私……”
这种感情的交流其实是相互的,柯利亚在卢卡的关心关爱中体会了一种亲情,从陌生的熟悉,甚至开始离不开他,在用喷头哭着叫“奶奶不要睡了”呼喊中,是卢卡拥抱他;在坐地铁走失的惶恐中,是卢卡想方设法寻找他;在从未有过的生日庆祝上,是卢卡给了他礼物——在那一列火车上,疲倦却并不孤单的柯利亚终于叫了他一声“晚安,爸爸。”这是一种认同,这是一种寄托,这是一种归宿,这是一种超越了国家的温情。
生活中的错位感消除了,他是爸爸他是儿子,似乎正以一种和谐的方式回归到生活本身,而投射到当时的大背景,柯利亚骑在卢卡的头上,两个人在人群中参与了反对当局的大游行,这是1988年的“天鹅绒革命”,似乎个体的生活完全和大政治结合在一起,也正是这种对于错位政治的消除,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完成了政权和平转接,随着柏林墙的倒塌,随着东欧的巨变,娜杰兹达回来接走了柯利亚,卢卡也重新进入了交响乐团,开始了克拉娜等待新生命的降临。
从假结婚开始的那个交易式的“爸爸”,到被抛下而无奈接手的冷漠的“爸爸”,再到不依不舍融入感情的爱心“爸爸”,最后是用温情让自己成为真正的爸爸,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角色转变,也见证政治生活的风云变幻,最终在“给我一个爸爸”的期待和付出中,回归到个体命运最温情的那一刻。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600]
思前: 被隐藏的直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