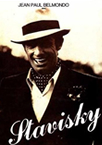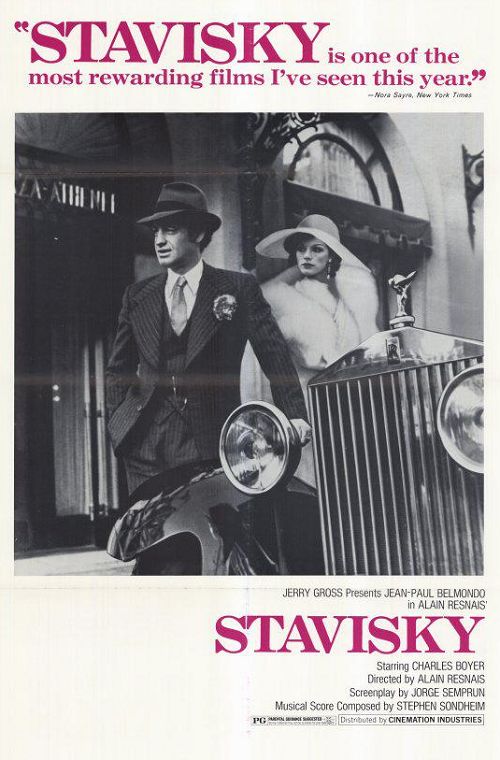2019-10-21《史塔维斯基》:从历史的内部虚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西班牙内战,德国犹太人,法国“正义之战”,以及托洛茨基,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当种种的历史元素汇聚而来,无疑这是对于过去的一种解读,“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加入了自己的想象,人名也都是虚构的。”电影一开场的注释,明白地表露了阿伦·雷乃的用意:当历史的框架摆放在那里,用虚构的人名解读历史,就会一种“非历史”,而这个非历史的影像到底指向什么?
1974年,阿伦·雷乃似乎已经开始转向,从“夜与雾”构筑的在场,转变到真实事件的记录,但是这种转型似乎只是影像讲述方式上的,以前的反战是对记忆的一种延伸,而当“在”的在场复活于记忆,那种“作家电影”对于历史的反思依然是片段的,但是当《史塔维斯基》变成一个历史真实事件的主角,当时间和地点都变成唯一,记忆是不是被取消了?片段的反思是不是成为了传记式的整体?“加入了自己的想象”,以及虚构的人名,似乎又回到了雷乃固有的叙事手法中:似是而非的人物关系还在,确定的情节只是外壳,而深入其中的依然是关于战争、关于存在、关于人性的阐述,就像“史塔维斯基”这个名字一样,从来不指向历史的具体存在。
“这样,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十月革命的胜利者,列宁的战友,红军的指挥者,开始走上末路了。”当托洛茨基流亡到法国寻求庇护的时候,这句话似乎也终结了一种历史的终结,曾经的革命者变成了流亡者,末日来临,一段历史结束——而且作为法国政府庇护的对象,法国内政部提出的要求是:不得干预法国内部事务。历史不仅终结,而且被隔离了。但是托洛茨基或者只是雷乃对于历史叙述的一个引子,当那个叫亚历山大·萨奇的男人出现,当这个苏联犹太人活跃在法国政坛,当真实名字叫“史塔维斯基”的他从事非法的投机活动,法国政府又如何对他进行限制、调查和惩罚?当他的罪恶暴露又饮弹自杀,谁能又说自己是清白的?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有无数个“史塔维斯基”组成的网络,这就是有无数个“史塔维斯基”制造的谎言,这当然也成为无数个“史塔维斯基”应有的下场。史塔维斯基曾经因为诈骗罪被捕入狱,当他出狱之后便改名换姓为亚历山大,对于他来说,名字似乎只是一个被用来改变的符号,而对法国政坛来说,政治也成为一个和名字一样可以虚构的东西。亚历山大行骗是为了什么?作为一个犹太人,他的首要目的是为了钱,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无所不用其极:他伪造证券,控制了银行业;他巴结官员,获得了独立银行的股份;他开设了赌场,控制了全巴黎的新闻出版界,帝国大剧院几乎成了他私人表演的舞台,当他的触手伸向法国政坛要界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丧失了自我的人。
甚至将自己的妻子阿雷特都拱手让给了别人,西班牙军火商蒙塔沃被阿雷特吸引,不断邀请她接近她,最终向她表白,当在高尔夫球场想要吻她的时候,阿雷特却避开了他:“我只属于一个人,我最害怕的是他离开我。”这一幕却被拿着望远镜的亚历山大看到,心中的一个计划似乎就此成型。他对于阿雷特的感情从来不是“只属于一个人”的那种纯粹,即使他将阿雷特的房间放满了花像是一个天堂,但是对于他来说,阿雷特无疑也是自己手中的砝码:他就是要利用蒙塔沃的资源,在军火生意中得到好处。所以他反而极力促成蒙塔沃和阿雷特的关系,而当蒙塔沃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他告诉亚历山大的是:100英镑已经打到了你瑞士银行的账户上。
| 导演: 阿伦·雷乃 |
爱情被金钱取代,亚历山大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利益,他又可以用这些钱解决账户上实际的亏空,而相反,那个说出“我只属于一个人”的阿雷特,似乎也并非在爱情世界里拥有满屋的浪漫。亚历山大在酒店里看见了旁边一个女人,于是在他的安排下给女人送去了鲜花,之后他上了她的床,她的那根项链送给了亚历山大,而亚历山大又把项链给了阿雷特,当阿雷特拿着项链,也知道是从那个女人那里得到的,却丝毫没有吃醋,仿佛这知道这和爱情无关;当亚历山大被调查,阿雷特无疑也成为了重点目标,贝荣说:“亚历山大的所有秘密就是她。”其实不是说她掌握了亚历山大的秘密,而是说他利用了她的所有资源, 而最后,阿雷特甚至不知道亚历山大到底做了什么,她只是问了一句:“他会自杀吗?”而当阿雷特入狱,贝荣似乎是礼节性地送了一只花篮,最后那只花篮却被放到了监狱门口,无用的隐喻,就像亚历山大曾经送的那些鲜花一样,关于爱情,都会在交易中枯萎。
一切为了钱,一切都是欺骗,银行、赌场、新闻出版,这些要害部门被亚历山大所控制,但是在这一种投机中,危险也慢慢在扩大,即使到了边缘,亚历山大也不忘为此一搏,当助手艾伯特提醒他:“我们已经亏损了,这是在浪费钱。”亚历山大说:“这是投资,不是浪费。”一个发明了子宫探测仪的男人找到他希望得到投资,只要一万法郎的投资,对于亚历山大来说几乎成了反讽,他拍了拍年轻人的肩膀说:“我来教你做生意。”在他眼里,只有西班牙军火生意,只有伪造证券,只有让官员为他让路,才是真正的生意。但是这样一个一掷千金的人,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却也是孤独,也是苦闷,甚至是折磨——当警察终于敲响他在霞慕尼的那扇门,他做的两件事是:把阿雷特在报纸上的照片减下来;拿出自己准备好的手枪。
|
《史塔维斯基》电影海报 |
他害怕失去阿雷特,害怕自己进监狱,因为害怕,所以要保持自己不害怕的状态,因为在公众场合不害怕,所以他越来越害怕,麦泽医生说:“他是个双重人格的人。他想人们谈论他,可以做任何事,可实际上他真正想要的是人们忘记他。”为什么要人们忘记他?也许是两年前被捕入狱的经历,“我宁可死也不要进监狱。”这是他曾经表达的害怕,监狱意味着仅仅失去自由?其实是失去一切,所以出狱之后,他改名换姓将过去的一切都埋葬了,就是让过去的一切都死去。但是这种性格并非仅仅是被捕过,而是来自家族的某种遗传,七年前他的父亲自杀,那把手枪结束一个人的生命,不是勇敢,而是无法摆脱存在的现实,所以他要人们忘记他,而唯一可以让人忘记的不仅仅是改名,而是将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埋葬,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是要用足够的钱,有足够的的关系,有足够的的骗术。
但这并非是被忘记,甚至有一天真相被暴露的时候,便是永远被记住,所以当越来越陷入难以自拔的关系网里的时候,亚历山大渐渐看见了某种宿命,“我老了,最好做一名乡村推销员。”那是他在帝国大剧院举行生日宴会那天说的话,无上的荣耀,生命的仪式,却想到了微小的愿望,但是亚历山大显然不可能完成这个心愿,那只被踩死的小白鼠似乎是他命运的写照,在树林里,他没有听到老鼠的尖叫,也没有感觉到它的挣扎,却赤裸裸变成了死亡。生日那天,他去了那间被铁门锁住的老房子,那里有着他的记忆,但是最后都变成了废墟,而自己的生命是不是也会在真相暴露之后成为一间废墟?
想要被人遗忘,却又害怕直面如老屋一样的命运,双重人格永远在寻找一种平衡点,却永远在病态中被自己否定,妻子阿雷特是一个工具,那些财富只不过是骗局,甚至犹太人的身份也变成了一个仇视被人又被人仇视的符号,那个在剧院里前来试演的爱玛,是一个犹太人,当亚历山大问他为什么要让所有人知道自己是一个犹太人的时候,爱玛说:“因为我蔑视所有其他种族文化的无知。”蔑视其他文化而成为一种唯一,是不是也是一种无知?当30年代的犹太人已经成为一个危险的身份,爱玛却用她的无知论构建种族的优势,是不是就是身份带来的悖论?
是的,一切都在双重人格中成为了自己:他是史塔维斯基,他是从苏联犹太人,他是投机分子,于是在一切真相被揭露之后,他拿出了那把枪,朝着自己的胸口开枪——一个戴着红花的千面骗子变成了时代的悲剧,“一个时代结束了。”阿伦·雷乃说,这不是三十年代的结束,这也不是1974年影像的结束,而是在虚构的人名之外,在加入了想象之外,一种法国式的人文时代结束了,就像亚历山大视为好友的贝荣在面对法国外交部官员时说:“他不是一个好人,他也不是一个法国公民。”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291]
思前:影,非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