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4-21【“百人千影”笔记】赛尔乔·莱昂内:英雄往事,已随风而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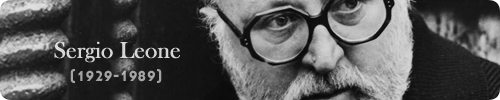
意大利只是一个意大利,法国只是一个法国。而美国却是整个世界。美国的问题也是全世界共同的问题:矛盾、幻想、诗意。
——赛尔乔·莱昂内
一个意大利是单数的意大利,是国家主义的意大利,当美国以“整个世界”的方式制造了一种整体性,对单数的意大利是取代还是融合?当意大利导演赛尔乔·莱昂内在镜头前展示西部镖客、纽约黑帮的往事,他是在向美国文化致敬,还是在由内而外的进入过程中制造另一个美国神话?一切的问题都归结为他言说的后半句:当美国成为整个世界,这是一种“美国神话”,这种神话所承载的是整体性的问题,它是矛盾的结合体,它是幻想的异托邦,它是诗意的理想国,一切的矛盾、幻想和诗意不是一种静态的观望和展现,是在动态的过程中,需要修订之后的重写,需要解构之后的建构,而神话的重写者和建构者,从来都只需要人,他的名字叫“英雄”。
从1961年的《罗德岛巨像》到1984年的《美国往事》,莱昂内在23年的时间里只拍摄了九部电影,而真正属于莱昂内的电影只有七部——三部“镖客三部曲”和三部“往事三部曲”,加上处女作《罗德岛巨像》,七部电影对于莱昂内来说,的确在数量上太少了,但是在矛盾、幻想和诗意的世界里,莱昂内却制造了电影的神话,就像《黄金三镖客》中的“好人”所说:“每支枪都有他们自己的声音。”这些电影构成了莱昂内独特的声音,而其中的英雄主义、异托邦的诗意,成为解读莱昂内电影叙事的关键,而这个从“一个意大利”从突围而创造了整体性世界的导演,无疑也让自己成为了英雄,他在矛盾中寻找出口,在幻想中制造虚幻,在诗意中构筑理想。
这到底是怎样一个神话?这需要怎样的英雄?两个三部曲之外,处女作《罗德岛巨像》其实正是通往莱昂内电影神话的钥匙。当最后象征权力统治的巨像在巨大的震动中倒塌,罗德岛的灾难便开始了,在狂风、骤雨、地震中,岛上的王宫、民居,以及所有的建筑毁于一旦,这个“地中海上最强大的港口”在这场劫难中几乎被夷为平地。这一切的灾难缘何发生?因为那些卑鄙、残忍的统治者触犯了天神,罗德岛便成为神对人的惩罚,但是在统治者和无辜居民死于浩劫,英雄却从来不死——英雄因为受到了神的庇护,英雄是因为超越了人的存在,或者说,英雄是神的化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神话之发生,必须要英雄来支撑,甚至只有英雄存在才能命名为神话。但是在英雄不死的神话里,当他们只是作为神的附属而存在,是不是这个神话反而成为了一个空泛的符号?是不是神话和英雄都无法真正关照人类?迪亚拉曾经开玩笑地对达里奥说:“普通人对我来说没有意义,而英雄又太过了。”这一种尴尬是不是也是莱昂内无法走出的英雄宿命?
对于莱昂内来说,“美国却是整个世界”的确带有离开意大利寻找新世界神话的某种膜拜情感,这是莱昂内构筑的第一重神话。“在我的童年时代,美国就像一种宗教信仰……”美国成为一种宗教,在莱昂内的内心成长为一种信仰,来源于两种情结:“在法西斯统治下,历史教材都不真实。我们知道那都是假的。在独裁时期,谎言成为教育的内容,但媒体也从不说真话。我们读报纸就是为了寻开心,因为我们知道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没有一丁点儿是真的。我呢,经常给我的历史老师出难题,经常向他问一些根本不可能回答的问题。”在《莱昂内往事》一书中,莱昂内用虚无主义的态度否定了“一个意大利”在国家主义体制下的历史真实;而1963年开始,随着意大利电影的急剧衰退,随着好莱坞公司的撤退,莱昂内内心的美国梦开始萌芽,当黑泽明的武士电影《用心棒》在罗马上映,莱昂内开始意识到拍摄西部片的潜力——1964年的《荒野大镖客》是对《用心棒》的西化改造,但也陷入了官司纠纷中,而最后的败诉以及赔偿无疑使得外界将其只是视作一个拙劣的抄袭者。
这或者只是结构意义上的“抄袭”,其实莱昂内在片头就已经设计了一种完全不同于美国西部片的风格:血红色的银幕上出现了一个模糊的白点,创造出一种近乎迷幻的效果,片名浮现的片段回荡着枪声和恩尼奥·莫里康内独特的音乐,这些都标志了莱昂内“去美国化”的西部片基调:一脚踏进历史洪流,另一脚踏进好莱坞之梦。“我在中间,枪响了。”当荒野大镖客转身离开,莱昂内的英雄时代才真正拉开帷幕,《黄昏双镖客》和《黄金三镖客》无疑完全变成了莱昂内自己创造的神话代表,尤其在电影结构中,完全去除了简单的对立性,从一个人到两个人再到三个人,不确定在增加,可能性在增多,也正是不确定性和可能性带来的多义性,所以才能让故事变得扣人心弦。《黄昏双镖客》中,看上去是两个人在善与恶的对决中,在生与死的较量中,但是作为第三者的莫科已经成为他们之间决定胜负的关键,在这样的格局中,三个人也成为无法分隔的整体,就如他们最后站立的那个地方,是被石子围起来的圆形区域,圆形而包围,圆形而变化,正像这个故事本身一样,三个人之间的纠葛,三个人产生的变量,完全超越了善与恶、生与死、输与赢的简单对立状态。而在《黄金三镖客》中,三个镖客,三把手枪,六双眼睛,以及20万金币,在最后象征死亡的墓地里,空气仿佛凝固了,他们的命运只有两种:生或者死;拿到金币或者葬身墓地:好人的嘴里永远叼着半根雪茄,他看着坏人和小人;坏人的右手中指少了一截,他看着好人和小人;小人的脸上有着新的旧的伤痕,他看着好人和坏人。
三个镖客,各怀鬼胎,他们眼神游移,他们汗珠滴落,他们沉着冷静,他们站在生死边缘。谁会用最快的速度扣动扳机打出子弹?谁会在别人的枪声中轰然倒下?谁又会在这场游戏中最终取胜拿到金灿灿的金币?没有人知道,但他们都想知道。这种宛如衔尾蛇的环形结构,正是具有了“自我吞食”的不确定和可能性,使得电影张力得到了扩展,而对于莱昂内来说,“每支枪都有他们自己的声音”也成为英雄驰骋的舞台,他们都身怀绝技,他们例不虚发他们百发百中,他们眼疾手快他们杀人不眨眼,如果行走在空旷、遥远的西部,荒漠、高山都是他们活动的场所,三个人制造的不确定性也是人性可能性的隐喻,“但使我感兴趣的,一是把善/恶/丑这几个形容词非神秘化,一是展现战争的荒谬。善,恶,丑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点罪恶,一点丑陋,一点善良。”
可能性意味着矛盾性,当镖客作为英雄驰骋在西部这个舞台,它便成为莱昂内童年的那个美国梦的一部分?成为美国整体问题的一种表达?实际上当美国在童年时代成为莱昂内的一种情结,它并不只是一种信仰,更多是一种“世界问题”的凸显,“现实生活中的美国人突然进入我的生活——坐着吉普车,打乱了我所有的梦想……我发现他们很有活力,但也很有欺骗性。他们不再是西部的美国人了。他们和其他人一样都是军人……唯物主义者,占有欲强,热衷于享乐和世俗商品。”这是美国整体性中“矛盾”的体现,在生命即将走向镜头的时候,莱昂内曾经对这种矛盾性做过阐述,“很明显,我不能用除欧洲人的眼光以外的任何方式来看待美国;它让我着迷,同时也让我感到恐惧。”
着迷和恐惧,就是美国神话在莱昂内心中的矛盾性表现,当莱昂内那一代的欧洲人,在战后这片以美元重建、以美国外交政策参与政治决定的大陆上成长,他们一边做着美国梦,一边怨恨美国统治的现实,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莱昂内在“镖客三部曲”中的“去美国化”就在于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国神话:莫里康内音效实验是一种外化的神话表现,在枪声、炮火、鞭裂、吟唱、口哨和手表的鸣响中,西部片的原声传递着巴洛克式的意象;横行其中独行侠、残暴匪徒和赏金猎人,他们充满了暴力,也充满传奇,更具有人性,他们在谎言、暴力、背叛、残酷现实中追求着普通人内心对正义、和平、友谊的渴望;在一个靠武力决斗、复仇而不依赖法律的“前文明”时代,英雄成为这个“江湖”正义的象征……
其实,从《荒野大镖客》开始,莱昂内的美国神话早就告别了童年的宗教信仰,告别了战争期间的唯物主义特性,它在刺激、暴力、极端、令人厌恶以及荒诞可笑中,成为一种莱昂内的异托邦:在异质的世界里,它是美国之外的存在,它是超现实主义的王国,是剥去了华丽而尽显欲望的世界,而需要重建这个世界的秩序只能靠英雄的横空出世。在《西部往事》中,水滴在不断落下,苍蝇在嗡嗡鸣叫的声音,在凝固的空气中,甚至连呼吸也不存在了,那一张张黝黑的脸,那一个个漠然的表情,以及一把把满含杀机的枪,似乎都在延续“镖客三部曲”的风格,但是莱昂内的突破在于,他把神话放置在更真实可感的历史场景中:“in the west”,不是表示地理位置的标记,所指的仅仅是时间。在这个和时间相关的标记里,有着时代最后的伪装,它是压抑而窒息的声音,它是取代名字和说话的口琴,它是5000美元身价的抢夺战,它是一个美艳寡妇的身体欲望,世界过去的方式正在这种伪装中消失,水井在消失,运送行李的马车在消失,沙漠也在消失。
一望无垠的大漠黄沙、骑士一样的抢手、冷酷而窒息的枪声,以及仿如呜咽的口琴声,这一切都已远去,取而代之的是铁路、汽笛、水和女人,一个多元的时代将西部变成了“Once upon a time in the west”的记忆。当一切都在时代中消失,英雄似乎正走向没落,但拯救英雄时代的却是另一种英雄,三个男人,或者死亡或者消失,而见证这个火车轰鸣的时代似乎只属于唯一的女人吉儿,这个从新奥尔良来带着文明印记的女人,寻找到了这个时代的水,她最终走出自己的小屋,为外面那些铺设铁轨的男人们送上水,需求和满足,在这个象征文明进程的水的故事里,女人变成了最后的主角,她面带微笑被男人们注目,就像被历史注目的这个有火车的新时代。而在《革命往事》里,当胡安完成暴力,看到受伤的约翰,问他:“如果你离开了我,我该怎么办?”约翰说:“你会当上将军。”然后将一枚皇家十字架勋章送给了他,约翰是英雄,当他用一次爆炸完成了自我革命,他把更高的革命使命交给了胡安,而胡安从劫匪到英雄,再到被命名的“将军”,将在浓烟散尽之后投入更激烈的暴力推翻的历程中。
时代变了,但是英雄主义不变,无论是暴力还是革命,无论是野蛮还是文明,总有英雄支撑起神话,所以对于莱昂内来说,“往事”所勾起的不只是回忆,更是对于历史的续承,在美国这个异托邦里,莱昂内就是在从事一种革命,“是时候改变一下了”——改变在15年后就变成了真正阐述美国这个异托邦的“美国往事”。赤裸裸和隐蔽,情欲和艺术,以及蛋糕的交易和圣经的祈祷,佩吉和狄波拉,这些构筑起了“面条”的美国梦,一如少年人生中的莱昂内,但是当最后老去的他们再次面对面的时候,麦大祈求着“让我的心灵在平静中死去”,而面条却在叹息中把报复、仇杀和死亡的恩怨变成了注定的一场人生际遇。“上帝保佑美国,因为我热爱这片土地。”似乎是莱昂内的心声,但是这心声的背后却是悲伤的歌声,在这个城市“面条”几乎没有了兄弟,没有了爱情,没有了金钱,剩下的只有咿呀的皮影故事,只有萦绕不停的电话铃声,以及随便去哪里的单程火车票。
《美国往事》是一个关于美国的神话?黑帮是英雄?实际上,当莱昂内用这部电影在好莱坞抵达了一个高度,在电影史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记,这个创造神话的英雄不是别人,而是莱昂内自己。莱昂内带有极其明显的个人印记制造了英雄式的“作者电影”,他对西部边疆的异质化风味的描绘、戏剧性的华丽场面,以及长时间的停顿,已成为了西部片的样本,在好莱坞,从《回到未来3》到昆汀·塔伦蒂诺和他的伙伴罗伯特·罗德里格斯的作品,无不刻着莱昂内的烙印,而莱昂内式的意象和莫里康内的配乐也构成了美国无数电视广告的基础。这是一种新的美国神话,也是莱昂内通过“去美国化”而构建的神话,这无疑又成为美国问题的核心:当莱昂内在电影中创造了一个根植于美国历史细节的世界,他却只能通过好莱坞的镜面折射出来,也正是这种折射关系,使得他的这个英雄神话更添了一种幻觉的色彩:为了拍摄《美国往事》,他在欧洲各地取景,并在威尼斯建造了“纽约长岛酒店”,在巴黎建造了“纽约中央车站”,意大利餐厅被命名为“莫胖餐厅”,它们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但却只是一种对美国的移植;《美国往事》最初的粗剪版长达10小时,莱昂内亲自将其剪到249分钟,即使参加戛纳电影节电影被精剪至229分钟而博得了现场观众长达15分钟的掌声,但是在美国上映时,制片方却将电影缩剪至139分钟,使得它变成了一部有“美国”而没有“往事”的黑帮电影;“欧洲版”赢得了掌声,但是当莱昂内参加奥斯卡角逐,最后却没有货的任何一项提名。
一个意大利导演,既想在“美国”中找到内化于整个世界的矛盾、幻想和诗意,又想在“美国往事”里创造英雄主义的神话,既想构建“去美国化”的异托邦,又想融入好莱坞的主流,这无疑就是莱昂内的“美国问题”,而英雄或者正是在那座巨像倒塌时看见了宿命式的悲剧,1989年,莱昂内在《美国往事》五年之后,开始执导新的电影,开始构建另一个英雄神话:一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包围苏联列宁格勒900天的宏伟史诗战争片,但是在完成初步企划拍摄时,他却因为过于劳累去世,英雄轰然倒地,英雄没有完成神话历史,于是,在制造了美国神话、好莱坞神话,以及电影神话之后,莱昂内最终在自我神话里倒下,矛盾、幻想、诗意成为这一系列神话最后的绝唱。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