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9-10《虚构叙事中时间的塑形》:构成内在的超验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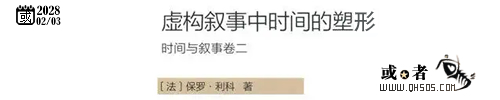
唯独虚构可以探索五花八门的时间经验,这些经验供人阅读,为通常的时间性再塑形。
——《第四章 虚构的时间经验》
叙事,虚构叙事,两种行为都趋向于一种时间的塑形:改变物理时间的线性结构,它成为了“时间的塑形”。但是当叙事在虚构中构建了一种时间经验,它便是虚构经验,便开始了时间的“再塑形”——从塑形到再塑形,从叙事到虚构叙事,保罗·利科完成了一个想象的世界,一个文本的世界,“当文本世界与读者生活的世界两相对照时,叙述塑形问题才会倒向叙事对时间再塑形问题一边。”但是再塑形之前必定是叙事意义的塑形,而塑形之前则是“预塑形”——这便是保罗·利科所提出的三重模仿理论,而这个理论的最终意义是在以虚构的方式探索丰富多元的时间经验中,将虚构经验变成文本投射于“世界居住的一种潜在方式”,从而建立起文本内在的超验性,最后完成读者和文本互动的阅读理论,只有时间完成了再塑形,只有读者参与了文本,才是真正的文学,“没有这后一个世界,文学作品的含义就是不完整的。”
预塑形、塑形、再塑形,不可或缺的元素便是时间,不可或缺的行动便是虚构,在这里,时间其实已经分化为三种图式:实际时间、情节编排时间和阅读时间,三种分化的时间也并非是彼此独立的,它们共同面对的一个行为就是模仿论,模仿论如何重建时间经验,如何完成虚构叙事,如何在再塑形中建立文本内在的超验性?保罗·利科在《时间与叙事》这部三卷集作品中就构筑了关于塑形的庞大体系,这个体系以两部著作作为出发点:一部是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对时间问题进行思考后提出了三重现在观:假如现在是一个没有广延的点,现在就是现在的现在,而过去的东西在记忆中留下了印记,它是过去的现在,将来的东西则在期待中显出征兆,这便是将来的现在——现在的现在,过去的现在和将来的现在,消弭了时间呈现为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分裂状态,它们构成的时间都是“现在”。但是奥古斯丁的三重现在观是在精神领域中建立的,甚至在他看来,精神的紧张体现了三个时间的特征:精神在回忆,在期待,即使现在的现在也使得将来转入过去,从而使得将来逐步缩小,过去逐步增大,一切变成了过去——现在,只是精神紧张的一种专注状态。
但是这种时间悖论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却变成了情节观,在他看来,时间和希腊悲剧情节编排行为遥相呼应:悲剧就是以戏剧形式模仿重大的严肃行为,悲剧的第一要素便是情节,情节就是对行动的模仿,情节的编排,是协调的、具有完备性、整体性和适当的广度,同时,悲剧又包含着命运的逆转、令人怜悯或恐惧的事变、悲剧性错误、不幸等等突变,所以它产生了不协调性——悲剧正是包容了不协调的协调。一方面是奥古斯丁提出的三重现在观,另一方面是亚里士多德的悲剧情节编排行为,保罗·利科就是在悲剧创作行为中看到了如何消弭精神紧张的办法,那就是协调对不协调的胜利:既在一个事件中包容了不协调的协调,更在一种循环中构建了时间经验:当受众在悲剧中发现不协调的协调的意义,把这种意义化成实际生命的体验,模仿论则又产生了全新的意象、主体和情节,在螺旋式的上升中,叙事的时间和生活的时间、叙事的经验和生活的经验联系起来,在读者和文本的层面完成了再塑形,从而开始了更多的可能性,按照利科的说法,“为时间的外显开创了无限的前程”。
情节对行动的模仿,叙事对时间的塑形,三度模仿论、三重塑形,利科直接将其和虚构等同起来,在他看来,塑形行为就是一种“生产性想象力的一种活动”,而且虚构叙事就直接指向文学创作活动,但是在再塑形之前的塑形阶段,虚构叙事显得更为重要,利科结合奥古斯丁的时间观和亚里士多德的情节编排概念,将虚构叙事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情节编排的扩展,通过革新、稳定和衰亡等概念,情节编排在形式上体现了多变中的同一性,这是不向任何本质主义让步的具体表现;第二个阶段则是情节编排的深化,它建立在对文学文本的阅读基础上,从而达到一种叙述智力,利科将其放在叙事学以及结构主义的背景下,使叙事更具合理性,在这个过程中,叙事的无时性更加突出;第三个阶段则是情节编排的充实,它发掘的是虚构叙事所特有的叙述塑形的资源;第四个阶段则是情节编排的开放阶段,在这个阶段,虚构经验开始出现,虽然它很不稳定,甚至看起来是一种悖论——经验如何被虚构,但实际上,虚构经验正是在想象中完成了文本的构建,一方面它只有在文本中存在,另一方面,通过文本的内在超验性,和读者世界的对照才能成为可能,再塑形才成为可能。
扩展、深化、充实和开放,是利科以亚里士多德的情节编排概念对虚构叙事做出的“解释”,其归旨仍在于从文本的内在超验性中、在时间的再塑形中建立和读者世界的互动:关键在于:叙事如何从实际时间变成情节编排时间,情节编排时间如何变成阅读时间?或者说如何从虚构情节变成虚构经验,从而和读者世界的生活经验相关照?《情节的变形》,当然只是在形式意义上具有了对情节编排的一种改变,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中,只有悲剧、喜剧和史诗才是情节编排的体裁,但是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传统之外的体裁:流浪汉小说、教育小说和意识流小说,这些体裁的一个共同点是情节开始变形,被简化,甚至性格损害了情节;而另一方面,产生了向经验回归的文学,“其意图是使文学作品尽可能准确地符合它模仿的现实”,它们把模仿变成了复制,这种复制看起来是虚构,但只不过是在技巧上的“信以为真”,“虚构艺术于是暴露为错觉艺术。从此,人为的意识将从内部破坏现实主义的动机,直至掉过头来反对它,把它毁掉。”
| 编号:B38·2220720·1852 |
这当然是情节编排上出现的危机,利科借用了诺思罗普·弗赖的《批评剖析》的观点,“诺思罗普·弗赖提出的叙述塑形体系属于叙述智力的跨历史模式论,而不属于叙述符号学的非历史合理性。”跨历史模式论,其实体现的是风格的同一性,不管情节编排如何变形,叙述模式中的虚构依然有着一个基本的标准,那就是:主人公的行为能力分配了虚构方式:叙述方式总是在情节编排层面进行操作;模式论的背后总是一种生产性想象力;不管想象的秩序如何改变,传统性的时间侧面总是不能缩减的。利科甚至认为,危机带来的不是终结,“它标志着迫近终结向内在终结的转化。”变形其实带来了革命,而这也正符合亚里士多德关于情节编排对行动的意义阐述:不协调的协调,利科说:“怀疑虚构在撒谎和弄虚作假,因为它给人以慰藉;坚信虚构不带随意性,因为它符合我们的一种无法控制的需要,即给混沌打上次序的标记,给无意义打上意义的标记,给不协调打上协调的标记这种需要。”
不协调的协调遭遇了危机,危机本身也是一种转向的开始,在深化的阶段,利科以结构主义的观点来阐述叙事智力问题,在他看来,“所谓深化,是指寻求一些深层结构,其具体的叙述塑形将在叙事的表层反映出来。”这里就进入到文本的虚构内部,利科提出的一个标准便是:必须弃历史而要结构。他把结构主义看做是情节编排的一场方法论革命,这个革命具有三大特点:一是在构建公理式模型的基础上要尽可能接近演绎程序,因为只有演绎这条路才能构建一个假定的描述模型,才可以衍化出不同的亚门类;第二要在语言学的不断运动中构建模型,最彻底的尝试是从小于句子的语言结构出发,得出比句子场的单位的结构价值;第三则是保持整体有机性的优先地位,只有在整体上保持有机性,部分遵从于整体,塑形才成为可操作性的行动。三个特点构筑了情节编排的一种革命,而这个结构主义的符号学革命在叙事中其实只有一个目的:使叙事非时序化和再逻辑化,非时序化和再逻辑化其实具有同一性,它打破的是叙事的历时性概念。在对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中提出的功能优于人物的观点进行否定之后,对克洛德·布雷蒙在《叙事的逻辑》中强调角色与情节的联系进行批评之后,利科从格雷马斯的叙述符号学中引出了“行动元”的概念,行动元不再是具体的人物,也不再简单的是角色,而是行动范围里的存在,它天然构成了行动,而行动带来的是情节编排,是时间经验,“我认为,从契约到斗争,从秩序的丧失到恢复的运动,构成寻觅的运动,它不仅包含一个连续的时间,一个时间顺序。”
面对情节编排的变形,利科强调危机的出现正体现了不协调的协调的编排原则,而在叙事符号学中对情节编排的深化,则强调了行动元的行动意义。在第三阶段的充实中,利科则直接带入了“与时间的游戏”中,“这些特点可以说靠塑形行为自反性产生的各时间层面间的游戏而释放出来。”游戏区分了陈述和被陈述的事,区分了陈述行为和陈述,“由于注意力从叙述语句转移到陈述行为上,叙述时间固有的虚构特点更加鲜明突出。”埃米尔·本韦尼斯特对故事和话语的区分、卡特·汉堡格和哈拉德·魏因里赫对动词时态问题的贡献,都是这种虚构的表现:被讲述不是叙事,它仅仅是被描述、被还原,没有赋予叙事的血和肉;被讲述的事情体现的仅仅是生活的时间性,而生活本身不被讲述只被体验;叙述是一种讲述时间,它既可以是托马斯·曼的“搁置一旁”,也可以是菲尔丁的“褶曲”——“被讲述时间在讲述时间中的不均匀分布”,被讲述的关于时间的实际经验,而讲述是在创造时间,成为“诗的时间”,显现为“有意义的创作”。
当然,虚构叙事的时间塑形还体现在视角和叙述语态上,视角分为第一人称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视角问题就是创作问题,形成了新的空间层面和时间层面,“因为采用可变视角的可能性——视角概念固有的属性——使艺术家有机会,艺术家也一贯利用该机会在同一部作品内变换视角,增加视角,并把其组合纳入作品的塑形。”视角概念是以陈述行为和陈述的关系为中心的研究的制高点,而语态则打破了叙述者的时间,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它改变了欧洲小说的独白原则,打破了叙述者和作者的一体性,在独白和对话中,小说进入了戏剧之列,利科认为,“复调小说的标新立异,是叙述者观念和叙述者语态观念的一场革命。”视角体出现了“从哪儿感知被讲述这件事所呈现的东西”这一问题,而语态则回答了“谁在这儿讲话”的问题,如果说视角仅仅是创作内部的方法问题,那么语态已经是一个交际问题,因为它面向的真实读者,“语态处于塑形和再塑形的转捩点,因为阅读表示文本世界与读者世界的交叉。”
无论是变形、深化,还是充实,利科阐述了叙事的同一性、叙事的符号学和在陈述中“与时间的游戏”,最后落脚点都在于让时间经验变成一种虚构经验,把塑形问题变成再塑形的读者互动问题,所以必须回到文本的分析中,寻找文本内在的超验性,而这便是一种想象力的超越运动——超越的是什么?虚构经验本身就是一种惊世骇俗的存在,经验怎么可能被虚构?虚构的东西怎么可能是现实意义上的经验?提出这个悖论式的改变,利科就是要发现文本中的内在超验性,以超验的方式形成“经验”,并将虚构的经验投射到作品中,从而为给读者让出位置的再塑形创造条件,“这里所说的时间虚构经验,不过是文本提出的在世界生存的一种潜在经验的时间外貌。”
利科在三个文本中发现潜在的时间外貌,那就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托马斯·曼的《魔山》和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达洛维夫人》体现的是个人时间和宏伟时间之间的塑形,在这里叙述者代表的是叙述的主体,而不是作者,他发出的是叙述的声音,他提供的是共享式的时间经验,当大本钟敲响了时间,它指向的是事件,更是叙述的一次塑形,“大本钟的钟声在不同人物对时间的鲜活经验中有其真正的位置,钟声属于时间的虚构经验,作品的塑形就从该经验开始。”塑形的意义就是以虚构的方式把行为世界和内省世界编织在一起,日常性的含义和内在性的含义交缠在一起:大本钟的时间是钟表时间,也是叙述的历史时间,更是权威形象时间,它们都成为了同一个时间,“时间塑形特有的这些手法促使叙述者和读者分享一个时间经验,或不如说一系列时间经验,从而在阅读中为时间再塑形。”所以小说中的时间经验不是克拉丽莎的时间,不是塞普蒂莫斯的时间,不是彼得的时间,不是任何小说人物的时间,“它是一个孤独的经验在另一个孤独的经验中的反响向读者暗示的经验。”
《达洛维夫人》的时间经验已经向读者开放,而读者建立的时间经验也开始在内在的超验性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再塑形便开始了。而在托马斯·曼的《魔山》中,它和《达洛维夫人》一样,将内心时间和顺序时间的冲突扩展到宏伟时间的范畴,但是《魔山》在开篇的前言中实质上提出的是讲述时间和被讲述时间的关系问题,它是一部时间小说,又是关于生命的疾病小说,当然它还是关于欧洲命运的文化小说,利科认为,“托马斯·曼决定把主人公对时间的探究当作他对疾病、死亡、爱情、生命和文化等其他一切探究的试金石。”时间经验体现在时间上,也体现在时间的永恒性问题上,它们共同构成了塑形的时间经验,“疾病和腐败的迷惑力揭示了死亡的永恒,它在时间上留下的印记是相同永远的重复。对星空的凝视向一种经验广布宁静的祝福。”也只有时间意义上发生重大历史事件才能破除无法超越永恒的着魔状态,而这便构成了魔法世界的虚构经验。
《追忆似水年华》的时间经验更为复杂,在利科看来,这部小说是关于时间的寓言,它既不是和不由自主的记忆所认同,也不是符号学意义上的时间,“它提出了这两个层面的经验与叙述者拖了近三千页才披露的独一无二的经验之间的关系问题。”利科把这部小说想象成一个椭圆形,第一个焦点是寻找,第二个焦点则是顿悟,而在寻找和顿悟的两个焦点中,最基本的时间经验则是失去。从玛德莱娜小点心的现实经验展开,进入到童年回忆中,但是这个回忆有两个声音,一个是主人公的声音,一个则是叙述者的声音,主人公的时间经验构成了回忆,它使得整部作品带有虚构的自传性,而叙述者的声音引起的是即时的幻觉,在《斯万之恋》中更是表现为受幻想、猜疑和失望折磨的爱情的恶性循环,“这种爱情注定要经受等待的焦虑,嫉妒的啮咬,淡化的忧伤和对本身消亡的冷漠。”所以叙述者讲述的是失去的时间,是被取消的时间,而这个失去和被取消的时间经验为的是寻回时间。寻回怎样的时间?不是一种失而复得的时间,而是关于时间的停顿,它指向的是永恒的时间经验,“超乎时间之外的存在”,所以在小说中,连接起重大场面和具有启蒙意义的叙事联结起来,插入的是关于艺术的长篇大论,艺术的背后就是永恒性问题,它超越了时间,超越了死亡,最后关于复活则变成了写作本身。
失去之后是寻回,这是时间的一个焦点,另一个焦点则是顿悟,从寻回的时间到失去的时间构筑的时间经验。利科分析认为,寻回的时间含义,一种是建立时间的隐喻意义,那就是永恒,另一种则是“视觉”,寻回就是对视觉的辨认,“隐喻和辨认的共同点,是把两种感觉上升到本质,又不抹杀二者的区别”,隐喻变成了辨认的逻辑对等物,而辨认又变成了隐喻的时间对等物,“隐喻之于文体范畴相当于辨认之于立体视觉范畴。”所以寻回的时间经验是隐喻上的永存,是辨认中的认出。当然利科认为还有第三种寻回,那就是寻回感受,它是一种和解,让文学和生活和解,利科的说法是:“寻回的时间表明失去的时间再现于超时间中,正如寻回的感受表明生活再现于艺术作品中。”
为什么要和解?和解便是同构,当失去的时间和寻回的时间同构,当叙事者和主人公同构,当生活和文学同构,虚构经验便在时间的塑形中完成了它的使命,接着再塑形便开始了,《追忆似水年华》的最后一句话似乎为利科的再塑形而准备,“我呢,我要写的是另一种东西,这更长,为了不止一个人。写起来很费时间。白天,我最多只能尽量睡个觉。我要工作也只会在晚上。但我会需要许多夜晚,或许一百个,或许一千个。我会提心吊胆地生活。早晨,当我暂且搁笔时,我不知道我命运的主宰,不如谢里阿苏丹宽容的主宰,是否乐意延缓我的死亡判决,允许我在下一个夜晚继续写下去……”
作家开始写作,但是叙事却戛然而止:写作在时间中,因为“允许我在下一个夜晚继续写下去”,叙事也在时间中,在“我暂且搁笔”时,于是时间为时间留下了位置,虚构为经验留出了一个出口,“小说的最后一句话要我和所有人在时间中各归其位呢?”对于利科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位置”,文本世界已经打开,读者世界已经打开,再塑形的世界已经打开,“这些方式构成某种内在的超验性,有了这种超验性,与读者世界进行对照才成为可能。”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6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