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4-09《新闻价值》:重新解释与受众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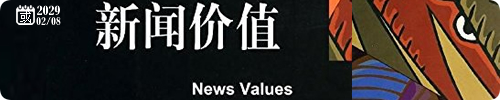
人们无数次地向我们这两位作者重申,对于“为什么这是新闻?”的问题,我们的回答仍然是:“它本来就是!”在此我们再重复一遍。
——《结论》
2014年2月第1版,保罗·布赖顿和丹尼斯·福伊的《新闻价值》在时间维度里,是一种新的存在:2014年,距离博客的诞生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各类社交媒体也犹如雨后春笋涌现,在如新闻价值的判断一样,高于或低于常规活动的“基准”,事件就变成了新闻,互动类的社交媒体也在高于或低于常规基准线中“制造”了新闻,但是在回答“为什么这是新闻”这样一个问题时,为什么保罗·布赖顿 丹尼斯·福伊坚持将“它本来就是”看成是唯一的答案?
产生新闻的时代变了吗?制造新闻的生态变了吗?或者说,关于新闻价值的理论和实践都发生了改变?种种变与不变,似乎都归结为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新闻价值?回答这个问题,保罗·布赖顿和丹尼斯·福伊引用的是挪威社会学家加尔通和鲁格提出的观点。在分析了挪威一组报纸内容之后,加尔通和鲁格找出了这些新闻的共同线索,然后创建了一个优先筛选新闻的体系,即关于新闻价值的理论,《构建和选择新闻》便是他们研究的成果:在这本书里,加尔通和鲁格确定了最符合他们所概括的新闻本质的标准,这些标准一共十条:相关性,即“对可能的或潜在的受众所产生的影响”;及时性,这是新闻之所以“新”在时间上的关键所在,在选取时思考的问题是:“它是最近发生的事件吗?这一事件的发展情况恰好是受众事先不知道的吗?”简要性,它可以简单地、直接地描述;预见性,选取新闻时的问题便是:“该事件可以被预知吗?如果可以的话,那么是否是预先计划的呢?”与预见性相反的是意外性,“该事件是完全出乎意料,而且是无法提前做出计划的吗?”预见性和意外性看似矛盾,却共同构成了新闻价值;连续性,“这是已确立某种顺序的一系列事件新的、进一步的发展吗?”契合性,“ 它特别适合某个媒体或新闻渠道的受众需求吗?”之外还有新闻对象的精英和“精英国家”以及影响力;最后则是消极性,“对于新闻界而言,坏消息通常意味着好消息吗?”
相关性、及时性、简要性、预见性、意外性、连续性、契合性、精英、精英国家、消极性,这便是加尔通和鲁格确立新闻价值的十个标准,另外他们还提出了另一套影响他们核心价值体系的修饰语,它们是频繁性,事件完整地展现自身和获得意义所需要的时间跨度;幅度性,超出了正常范围的界限,意外事件成为新闻;清晰性,信号的含糊性越小,事件就越会引起人们的关注;意义性,事件的文化关联性以及社会一致性或不一致性;预见性,期望某个事件发生,而且该事件成了新闻条目;持久性,一旦事件成了新闻,那么它就聚集了自己的动力;成分性,在某个节目或出版物的范围内,新闻条目的内在相关性被当作一个决定先后顺序的体系。十个标准和七个修饰语,构成了加尔通和鲁格“构建和选择”新闻的条件,也成为新闻价值体系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成果,总结为一点,当事件从日常生活中显露出来,超过或无法达到常规的基线,也就意味着事件成为了新闻。
但是,加尔通和鲁格的论文发表在1965年,如何选择和构建新闻只是上世纪60年代的标准,而且保罗·布赖顿和丹尼斯·福伊认为,他们的对新闻价值进行研究并使之系统化的种种努力,都是为了体现三大新闻价值:一个是新闻职业的/专业的/正式的新闻价值,第二则是意识形态/文化主义者的新闻价值,第三则是审美的媒体导向的新闻价值,也就是说,新闻价值是在和意识形态、文化作用、技术决定论等结合起来中体现的,这和加尔通和鲁格研究的出发点有关,他们的目的是要消除这样的误解:“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把他们在报纸上阅读的内容与新闻混为一谈”——还新闻以事件性本质,纳入意识形态、文化和技术的宏观体系,区别与报纸上的诸多信息和内容,“构建和选择新闻”无疑适用于那个时代。
40多年过去了,“构建和选择新闻”无疑发生了改变,在“导言”中,保罗·布赖顿和丹尼斯·福伊一开始就列举了“英国小报最极端的标题”:“仁慈的同性恋牧师闯入王宫”,这个将性变态、慈善和王室结合的标题,真的具有新闻价值?甚至它就是新闻吗?保罗·布赖顿和丹尼斯·福一方面称之为“一个城市的神话”,另一方面却认为“标题深处隐藏的却是某种真实性”,而这种真实性就是若干当代新闻价值的交汇点。之所以称其为“当代新闻价值的交汇点”,保罗·布赖顿和丹尼斯·福伊也许在其中发现了这个标题背后的“禁令”,而禁令构成了新闻报道中的变量。变量当然是在正常视野之外的存在,“这些领域绝对是对新闻价值进行任何最新评价所不可遗漏的”,这些变量包括新闻会议、新闻报道时间选择和节奏、权力平衡、新闻与评论,除此之外,则是互动性、今天的明日新闻和新闻禁令——后三条似乎是真正具有时代特色的变量,而这些变量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不再以单向的方式选择和构建新闻:互动性的崛起,新闻不再是新闻机构的选择和创造,互动也是新闻;今天的明日新闻,是一种“预播”,它体现的是预见性,也可能是意外性的一种表达,而不管是预见还是意外,都在计划之外,都在明日发生,谁是“今天的明日新闻”的决定力量?新闻禁令,禁止的是谁?是新闻的传播者还是受众?当新闻被禁止,必然是从受终端传递到编发端的一种信号。
互动性突出的是新闻创作和构建的双向过程,“今天的明日新闻”考虑的是受众的期望,新闻禁令则是切断了受众的目光,所以,新闻变量体现的正是另一个时代的到来,按照保罗·布赖顿和丹尼斯·福伊的理解,新闻价值的理论和实践都需要做出调整,“新闻价值不只是被应用于它们的受众,也由它们的受众做出判断。”受众成为新闻价值判断的主体之一,也决定了“选择和和构建新闻”的体系:人们的选择是受到滚动新闻频道在国际上日益强势的影响的结果吗?人们的选择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由上述各种事件所引发的报道强度为前提条件的吗?或者,更确切地讲,新闻报道的强度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新闻机构对它们各自受众的预期或兴趣所做的判断决定的吗?“仁慈的同性恋牧师闯入王宫”,新闻价值当然也闯入了另一个领地。
| 编号:W51·2140507·1073 |
受众做出判断,成为了新闻价值新的标准,保罗·布赖顿和丹尼斯·福伊分析了全国性日报、全国性电视节目、星期日报刊、滚动新闻、数字时代广播新闻以及其他新闻的特殊领域的新闻生产,受众的需求成为新闻选择的一个关键标准。全国性日报就是一面社会的镜子,它反映民众的不同政治观点,所以一个真正技能娴熟的主编应该首先了解受众的预期,由此提供一套统一的价值,虽然新闻价值依然遵循着加尔通和鲁格的“旧的”体系,但是对受众的预期的关注成为新的变量;全国性电视节目以1980年6月1日有线新闻电视网的开播为标志,电视新闻开始了转变,之后还出现了“双向思考性节目”,演播室和现场新闻工作者之间进行交流,以表明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这无疑是直播的雏形,另外最重要的现象则是电视墙的广泛使用和“公民新闻”数量的增加;只在星期日出版的星期日报,内容多为“软软的”报道,侧重于思想性,制作精美,适合星期日休闲的人们阅读,受众的选择成为星期日报内容转变的方向;滚动新闻是24小时新闻遭遇大量突发报道后的产物,它遭受了批评,人们认为它的内容有太多的重复、过度猜测、过多依赖主持人和记者的双向交流,注重时效而不是准确性,但是在另一个意义上,直播节目、短信服务,都是在受众和播出机构中搭建了互动的桥梁;还有地方性报纸、杂志和在线新闻的出现,则体现了更多融合的特点,这些融合既有技术上的融合,也有内容上的融合,更多则是和受众的融合,比如地方性新闻,它的主要价值体现就是要与当地受众具有相关性。
保罗·布赖顿和丹尼斯·福伊在分析了全国性日报、全国性电视节目、星期日报刊、滚动新闻、数字时代广播新闻以及其他新闻的特殊领域的新闻选择和构建,受众、互动、滚动和融合成为新闻价值新的体现,在这里他们重点关注了“公民新闻”。公民新闻出现于何时?保罗·布赖顿和丹尼斯·福伊认为,历史转折点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当那一架被劫持的飞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的时候,最初的画面并非是由专业新闻团队提供的,而是普通民众使用数码相机和普通家用摄像机拍摄的。这是公民拍摄的画面成为“新闻”的历史性时刻,同时产生的是“公民新闻记者”。另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则是“公民新闻网”的开设,2002年2月韩国吴延浩创建了这个网站,其中有50多名记者和主编,有3.6万公民记者,网站提出的口号是:“每一个公民都是一名记者。”按照吴延浩的说法,“我们已经创建了一种新型的新闻业务,我们称之为21世纪的新闻业务、双向的新闻业务。因此,读者不再是被动的。他们非常积极,并参与进来,讲述他们想要讲述的内容。”
公民新闻不仅仅是互动,不仅仅突出受众的选择,受众成为了新闻的制造者、生产者,这当然是对新闻价值体系的一次革命,甚至是对传统新闻终结的一个信号,在这个最大变量出现之后,加尔通和鲁格在1965年提出的新闻价值理论是不是会最终走向灭亡?保罗·布赖顿和丹尼斯·福伊否认了这个观点,并且以“它本来就是”的态度重申了新闻价值的同一性,“旧秩序由于理解和遵守某个价值体系,因此,完全有可能取得胜利,而这个价值体系却很少为视自己为新闻记者和新闻编年史编撰者的个人所遵循。”在他们看来,公民新闻记者站在新闻的一线,以多元化的视角构建了更多的新闻价值,他们在新闻传播中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公民新闻记者受到太多的限制,他们凭借个人无法获得关于事件全面的资源,“这些资源需要一个主要的新闻机构与各方面进行联系才能得到,而个人很少有这样的能力。”他们能得到的只是片段的、有限的、碎片的资源,当然他们的新闻也是片段的、有限的和碎片的;另外,公民新闻记者都是热情的业余爱好者,他们很少因为报道而获得报酬,所以个人也没有长期进行新闻报道的时间和金钱;公民新闻记者发布的渠道,比如当时的博客,在本质上也是转瞬即逝的。
这是公民新闻的限制性因素,它无法像新闻机构一样构建起强大而立体的新闻价值体系,但是公民新闻和公民新闻记者的出现,却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新闻传播体系,凸显了新的新闻价值。一方面,新闻机构的新闻传输模式是一种“推送”,而公民新闻记者则是“吸引”模式,拥有丰富经验的编辑团队挑选的新闻就是那些与读者的预期相符的新闻,从推送到吸引,就是新秩序对旧秩序的取代,这种取代构建的是新的新闻价值体系,“换言之,他们以能否在自己的价值体系内与自己实现共鸣,来判断哪些新闻最符合自己的需求。”同时,公民新闻记者的出现“有助于我们学会倾听”,按照丹·吉尔默《我们即媒体》的观点,“他们将有助于促进一个真正的信息通畅的公民社会的形成。”更为重要的一点,公民新闻出现之后,当传统新闻机构将博客的信息转为主流新闻,必然要对传播渠道媒介化,在这个意义上讲,媒介化的新闻更符合受众的需求,也更容易体现丰富、多元的新闻价值。
1965年加尔通和鲁格提出“选择和构建新闻”的标准多少有些不合时宜了,因为当时没有互联网,没有舆论引导专家,没有滚动新闻,更没有公民新闻记者,当社会发生了改变,当变量不断增多,旧的体系需要更新,这种改变最主要的便是凸显受众的地位,重建新闻提供者和新闻接受者的关系,这不单单是新闻机构与受众建立关系,更在于新闻记者从受众的需求中发现新闻价值,这不是单向的吸取,而是双向的构建:公民新闻记者既是提供者也是接受者,新闻机构是传播者同是也是受众,“大多数当代新闻研究工作旨在重新解释与受众本身的关系,这也正是我们的信念。”受众接受新闻,判断新闻,制造新闻,而这些都是对新闻价值本质的多元化和丰富化,所以新闻依旧是新闻,新闻价值依旧是新闻价值,“它本来就是!”它也永远都是。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8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