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9-12《奥雷莉亚·史坦尼(温哥华)》:大海在沉默

一样是奥雷莉亚·史坦尼,一样的父母是老师,一样的十八岁,一样的写作,也一样通过信件写给没有名字的“你”,只不过从墨尔本来到了温哥华,只不过从28分钟变成了47分钟,只不过从彩色的影像变成了黑白的影像,玛格丽特·杜拉斯在进行异构?还是完成另一种同构?
《奥雷莉亚·史坦尼》的两个系列,当然表达着一样的主体:关于灾难,关于死亡,关于寻找,关于连接,关于我和你,以及关于历史和现在。但无疑,在“温哥华”中,玛格丽特·杜拉斯对于历史的叙述更多了笔墨,也更多了悲剧感:在那片异域的土地被关押,在那个恐怖的集中营被囚禁,在那种非人的伤害中被折磨,“我的母亲,她死了。”直接指出了“母亲”和“死亡”,也指出了“孩子”和“活着”;在一种死亡和活着之外,还有另一种死亡,那是一个他,一个爱她的他,一个更爱孩子的他,但不是因为给年幼的孩子偷汤,他被执行了绞刑。死亡之后是另一种死亡,死亡连接着死亡,死亡重叠着死亡,在复数的死亡中,他和她成了他们,“他和她在一起”,但是是以死亡的方式在一起。
| 导演: 玛格丽特·杜拉斯 |
他们死了,她活着,带着痛苦活着,带着被见证的罪恶活着,而这个活着的她又变成了“我”,走出历史的我,却走不出灾难的我:我在房间里,黑暗的房间,我照着镜子,镜子里是陌生的自己,我走出去,找不到方向,“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对永恒无能为力。”因为横亘在面前的是永恒的死亡,它让一切的生存都变成了转瞬即逝的幻觉,它延伸到了必须面对而且跨越过去的现实。但是在玛格丽特所书写的信件中,在我和你无限走近的对话中,“你”永远是缺席的,而在“你”的缺席中“我”也成为了缺席者,“我爱你,但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我不认识你。”
和墨尔本的部分相比 ,温哥华部分形成了在声音叙事上的不同,它以更细节化和更绝望的笔触表达着历史制造的灾难和历史对现实的侵袭。而在影像上,杜拉斯采用的黑白色调更是增添了沧桑感,更具有视觉的冲击力。黑白取消了多层次的颜色,它在黑与白之间形成叙事,就像生与死,而玛格丽·杜拉斯特却提到了占据海洋的绿色,天空和眼睛的蓝色,头发的黑色,甚至是余晖撒下的金色,但是这一切都变成了空洞的词语,颜色被抽空了,只剩下黑与白,也只剩下生与死。除此之外,墨尔本的画面是巴黎的塞纳河,沿着塞纳河拍摄连接起历史和现实,而在温哥华部分里,她的镜头面对的是大海,大海是宽阔的,目光可以无限延伸,但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大海却是沉默的,它制造了浪涛声,也变成了沉默的存在,因为它是对声音的覆盖,对声响的取消;大海也充满了迷雾,那里没有金色泛光的美丽,只有被窒息的压抑,就像我对你一样,“你长什么样?”当然,大海更是被那些突兀的岩石所阻拦,它们高大、坚实、甚至占据了整个屏幕,目光永远无法穿透岩石望见大海。
大海形成的海浪,海浪冲击着海滩,它是破坏的存在,它也带走了很多东西,或者历史也将被带走,留下的是残缺,并最终被人遗忘,而在他和她死亡之后,“他的船要走了”,那是真正的死亡之船,无法返回,没有靠岸,在大海的颠簸中,在海浪的吞噬中,连遗迹也可能不再存在。而以大海为主体的镜头里,玛格丽特·杜拉斯还插入了被标着“200095”数字的纸片,这或者就是集中营里囚犯的编号,它被呈现出来是对屠戮和非人性的控诉;还有关于奥雷莉亚·史坦尼名字的纸片,它不断被念及,从历史到现实,从集中营到温哥华,“他说了名字,又说了一边,再重复了一遍……”一遍一遍被说起,名字背后是生命,是个体,是活着,也许正是因为这个被铭记的名字,“我”才会写信,才会说话,才会寻找你,才会是那时死亡的18岁变成正在活着的18岁,“我叫奥雷莉亚·史坦尼,我住在温哥华,我的父母是老师,我十八岁,我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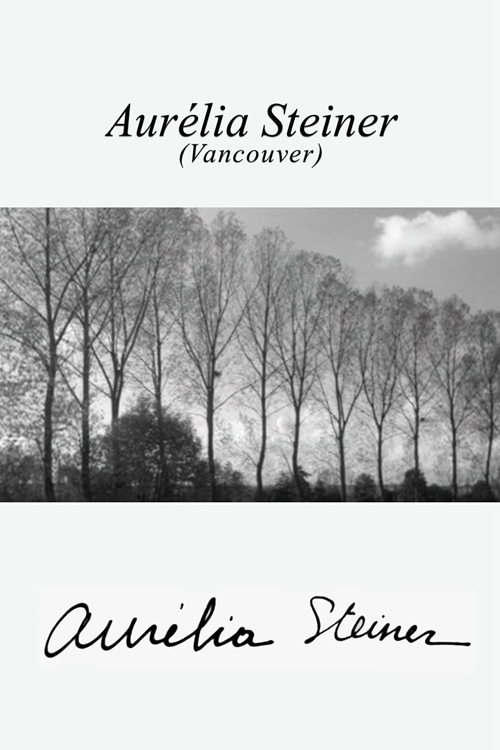
《奥雷莉亚·史坦尼(温哥华)》电影海报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1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