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0-26《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作品选3》:让我考虑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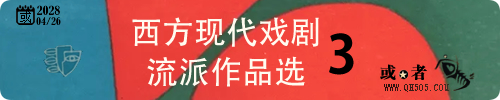
不管怎么说,我昨天碰到了您,我就有了这么一个想法:您这么半道上闯入我的生活道路,要么就是上苍派来拯救我的,要么就是恶魔派来毁掉我的。
——斯特林堡《通往大马士革之路》
《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作品选》的第2卷为“象征主义”戏剧,第3卷则是“表现主义”戏剧,黄色和蓝色的封面,2和3的标识,都是关于流派的区分,但是不管是象征主义还是表现主义,似乎都在趋同中远离了现实主义,而这种非现实的演绎就像斯特林堡在《通往大马士革之路》中“无名氏”面临的人生难题:那闯入进来的是上帝派来的拯救者?还是恶魔派来的毁灭者?拯救和毁灭的两难选择折射的也如象征主义的主题一样,是世纪之交中“人”的出路问题。
斯特林堡将戏剧中的主人公命名为“无名氏”,正是人的一种无名状态:他在家族中被称为“妖孩”,是因为自己是个私生子,更是因为给正常的家族生活带来了灾难:出生时家里破产,受调查时叔叔自杀;和哥哥争吵,被哥哥拿着斧子砍杀,自己则抓起石头砸掉了哥哥的门牙;在妹妹的婚礼上被赶了出来;没有参加父亲的葬礼;被监禁苦役达14年,险些送掉了性命……“无名氏”已经被书写的一生总是充满了困苦,甚至于不是一个生活在正常世界里的人,所以在遇见“阔太太”的时候,当回答她提出的“你信什么宗教时”,“无名氏”的回答是:“我信奉的是:这人生倘若实在叫人忍受不了,我就一走了之。”这种逃离的方式让他感觉自己面对的是死神,甚至将死神玩弄于股掌之间,“走向死亡”成为他最后的追求。
一方面是自己被生活除名,是经历了一切的困苦,“我是从仇恨里长大起来的。仇恨!以硬对硬!以牙还牙!”而另一方面,自己的过去也让别人变成了受害者:原来“阔太太”的丈夫“医生”就是因“无名氏”的过错而受到不公正惩罚的人,“医生”也因此对社会失去了信心;在路上遇到了“疯子”,疯子被叫做“凯撒”其实就是“无名氏”童年的绰号,这个绰号背后是暴力式的恶——所以对于“无名氏”来说,这个恶魔般的世界让自己感受不到生活中的爱,也因为自己是恶的制造者而成为了他人的恶魔,所以当认为人生有两种选择——要么是拯救者要么是毁灭者——的时候,选择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既没有上帝,也没有恶魔,或者:上帝就是恶魔。
二元论变成了一元论,这便是爱和信仰的“无名”写照。他在去邮局的路上听到了哀乐,看到“阔太太”胸前的花是象征邪恶和造谣中伤的曼德拉花,似乎一切都变成了死亡的征兆,当“阔太太”提出去教堂的时候,他更是拒绝,“那会使我难受不堪,而且使我觉得同那个环境格格不入,觉得我已经无药可救,再也不可能迷途知返,就象不能够重新变成个儿童一样。”但是,从奇遇开始,从揭露自己的经历开始,从和“阔太太”的对话开始,实际上斯特林堡却给了他“迷途知返”的机会——把“阔太太”英格堡叫做“夏娃”,就是一种命名的开始,从对他人的命名到对自己的命名,挣脱束缚自身的“无名氏”命运,似乎才是真正迷途知返的开始,“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重头再来一遍……尸骨残骸、乞丐、疯子、人的命运、童年时代的回忆……走出家门,跳出这个牢笼,让我成为把你从这个地狱里搭救出来的救星。”
从大街拐角到医生家里,从旅馆客房到海边,从公路到深谷幽径,从厨房到客厅,这是斯特林堡戏剧中第一幕至第三幕的场景,而以“在疯人院”为中心,“无名氏”又从客厅到厨房,从深谷幽径到公路,从海边到旅馆客栈,从医生家里到大街拐角,第四幕至第五幕,几乎是前面场景的逆行,五幕的17个场景构成了整齐有序的对位结构,而这种对位便是让灵魂“迷途知返”:在赎罪之后,在死亡之后,在毁灭之后,开始重新回到人生的起点,就像见到母亲时母亲对他说的那样:“你已经离了耶路撒冷,你正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走在大马士革之路上,每一处耶稣受难的地方竖起十字架,然后在第七处停留歇脚,便是和耶稣一样,在受难之后完成复活——“去大马士革之路”便具有了自我返身的象征意义,而疯人院在其中扮演的重要意义,便是经历了人生的“精神死亡”:最后回到大街拐角,回到邮局,终于收到了那笔稿费,“我真该死!原来那笔钱已经寄到啦!”一切不是重复,在“无名氏”看来,正是对人生新的命名,那些经历并不都是邪恶,上帝也并非以恶魔的方式来引诱,最后和阔太太走进教堂,听到新的歌声,便是完成了“通往大马士革之路”的自我救赎。
但是斯特林堡的某种乐观主义在表现主义戏剧中,却并不常见,或者说“无名氏”所说的两种选择、两种命运,更多的时候出现的不是上帝的拯救,而是恶魔的毁灭。德国弗兰克·韦德金德出版的第一部剧本是《青春的觉醒》,在剧中被夭折的是两个年轻的生命,他们是虚伪道德的牺牲品,而韦德金德用“青春的觉醒”为题并未让人看到真正的觉醒,反而这一出“儿童悲剧”中,儿童被反自然的迂腐社会所扼杀,他们无法通往大马士革之路,他们的归宿只有一个地方:坟墓。在剧作中,韦德金德的表现主义在于对人名的讽刺,校长痧丁、舍达古恩的名字表示的是生理或精神上的缺陷,亨伯和康邦1科克则是残暴的象征,波波芬是无能,在这个名字体现社会现实的剧作中,孩子们原本是自然、纯真的象征,但是在道德戒律中他们逐渐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爱的能力,甚至最后失去了生命。
孩子们对于社会有着太多的疑问:我们究竟为了什么而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为什么要上学?大人们考我们的意义在那里?疑问或者还有一些觉醒的味道,但是在现实中,觉醒变成了惩罚变成了绝望,莫里茨问梅肖尔的是“一个人的羞耻感只不过是教育的产物”?文德拉要带一把剪刀上宗教课,甚至告诉玛尔塔在她朗诵“不从恶人的计谋”时,就把她的鞭子见到,而玛尔塔害怕地说:“看在上帝的分上,文德拉要是这样,爸爸会把我揍扁的!妈妈也会把我锁在煤窑里关上三夜。”对此莫里茨有相同的感受:“我要是考坏了,我父亲就要打,妈妈会进疯人院。”他们不能看《浮士德》,他们接吻,最终社会的道德秩序将他们埋葬——文德拉的墓碑上写着:“一八七八年五月五日诞生 一八九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卒于贫血症”;梅肖儿爬上教堂公墓的围墙,“一罪接着一罪。我被送进了泥坑。我已没有足够的勇气以结束自己的一生……”一边却是不断地重复:“我并不坏!——我并不坏!——我并不坏……”而莫里茨在那里独语:“我就这样返回我的处所,把我那被这莽汉冒冒失失踩倒的十字架竖起,等一切都安顿就绪,我将重新躺下,暖和我的尸身,再露出笑容……”
| 编号:X92·1970719·0397 |
对孩子的毁灭早就了弗兰克·韦德金德的“儿童悲剧”,青春没有觉醒,青春只有被扼杀的命运,而被扼杀的何止青春?德国凯泽的表现主义戏剧《从清晨到午夜》,塑造了一个“出纳员”,他每天就坐在银行的柜台前,和支票、银币打交道,和“无名氏”一样,他的生活也是被“出纳”所注解,也是一种无名的状态,也和“无名氏”一样,遇见了“阔太太”,于是他抢劫了银行,带着钱去找阔太太,这一行为对他来说,像是一次冲动犯下的罪,他失去了工作成为了罪犯,但这只是一种法律建立的规则,出纳员之所以这样做,也并非是为了阔太太,而是改变自己一成不变的命运,“今天早上我还是一个非常可靠的雇员——成千上万的钱财都经过我的手。一家营造公司存了一大笔款。到中午,我已经是个彻头彻尾的坏蛋了。”在他看来,抢劫银行具有的勇气是对自我的肯定,潜逃的计划又是一个精心的杰作,“真了不起”是他对自己的评价。但是作为自我的英雄,出纳员并没有成为神,金钱有了,勇气有了,杰作有了,但是当拿着这些钱想要主宰比赛的时候,他才知道更大的英雄在后面,“皇上”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统治者,才是控制一切的神,“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用金钱都是无法买到的,就是用全世界所有银行里的金钱也买不到。弄到手的东西同花掉的金钱相比,总是不值。”金钱腐蚀了商品,金钱蒙蔽了真理,金钱也阻断了通往大马士革之路,他留下的悲剧式疑问是:“为什么我要急急忙忙地上路?我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
美国作家埃尔默·赖斯的作品《加算机》和《从清晨到午夜》有着相同的主题,主人公是有着一个高度抽象化名字的人:零,作为会计师,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一天到晚坐在椅子上加数”,二十五年如一日,没有缺过一天勤,单调乏味。但是有一天老板告诉他的是:“现在的情况是,我的效率专家建议安装加算机。”加算机是一架能够自动加数的机器,也就是说,零的工作将被机器无情取代,二十五年之后则是一个失业的人生新起点。于是在老板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零杀死了解雇他的老板——埃尔默·赖斯完全用表现主义的技法“表现”了杀人的瞬间:老板在絮絮叨叨向零解释,声音变成了一种强大的覆盖物:音乐声响起之后,一切戏剧手段被调动起来,风的呼啸声、拔浪的咆哮声,马的奔驰声、火车的鸣笛声、雪橇的铃声、汽车的喇叭声和打碎玻璃的声音混杂在一起,在震耳欲聋的声音之后,是雷声大作,然后一道红光闪过,最后是一片漆黑。舞台成为表现主义的舞台,声音、闪电、红光和黑暗,构成了零内心世界。
老板死了,零因犯了杀人罪而被处以死刑,在死亡世界,他遇到了杀死母亲而被处死的施尔德卢,而暗恋他的黛茜也以自杀的方式追他而来,三个死人在坟墓中相遇,对于他们来说,无论是报复也好还是无奈也罢,总之是解脱了,甚至零可以大胆吻向黛茜了。但是这何尝是一个属于他们的死亡之地?查尔斯进来让零去重新做人,零害怕重新回到人世间,而实际上查尔斯之所以让他回去并不是给他机会自我救赎,而是因为坟墓要给其他的人留出位置:“去,快去到外边找工具来,把这个烂摊子打扫一下。有另外一个人要搬进来。快点。”坟墓里人满为患,是因为死亡的增殖,更因为死亡也变成了机械般的存在,和加算机一样,不管活着还是死去,都是机器的世界,而人也异化成了一部机器。出纳员打破了二十五年不变的生活成了罪犯,零拿出了勇气结束了老板的生命而被判死刑,“出纳员”和“零”都成为了死亡的符号,德国佐尔格的《乞丐》中的那个“剧作家”当然也是被符号化、被异化的象征。
“家里整天都是阴阴沉沉,穷极潦倒,憎恨半点阳光,家父身患重病,令我们胆战心惊。”这便是“剧作家”的生活,而他的创作呢?因为过于奇特,过于陌生,剧本竟然被剧院拒绝了,“在他们看来,我的剧本中有许多标新立异的东西,所以人们有所顾忌,不敢尝试上演。”面对这样的打击,剧作家的想法是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剧院,但是遭到了出资人的否定,遭到了朋友的反对,理想破灭,对于剧作家来说是一种死亡,但是正是因为要经历死亡,才能以死亡的方式创作新的戏剧:剧作家直立在坟墓后面,把种子播在新鲜的土地上,“播下种子吧!播下种子吧!用双手播种!”一切的死亡是为了复生,苦难成为了新的剧本,那里有从未被人踏过的海岸,有从未被人爱过的爱情,有从未被啜泣过的歌,“我的成就促使我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我考虑很久,因为这条道路对于我也是非常痛苦,痛苦万分。”从死亡复生,对于剧作家来说,就是抛弃教士的身份,就是放弃成为半个圣徒的艺术家符号,而是——“我必须成为象征的雕塑家”,“让我考虑……考虑……象征……”成为剧作家新的使命。
《青春的觉醒》中的孩子死于道德的审判,《从清晨运到午夜》的出纳员死于金钱的统治,《加算机》中的零杀死了老板却被法律宣判了死刑,《乞丐》中的剧作家也在死亡中成为了象征的雕塑家——死亡无处不在,死亡是表现主义的常见主题:死是恶魔引导的死,死是没有上帝的死,死是生命鄙弃的死,死又会以何种方式成为复活的前奏?德国作家恩斯特·巴拉赫的《死亡之日》表现的也是人类死亡,但是他通过晦涩的意象将死亡阐述为一种中断。母亲在等待“他”回来,儿子却没有给母亲带来希望, 因为在母亲看来,“儿子就是过去的我”,只有当儿子将那部分生命还给母亲时,母亲才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生命,“别忘了,你拿走了我的生命,你要是走了,谁来给我生命?”这当然是一种对未来的抹杀,而儿子变成了婴孩,重新回到母亲的时间里,他看到的是梦魔,时间没有回来,过去没有回来,生命没有回来,儿子对母亲说的是:“一个死去的白天,一个幽灵,来惩罚一颗负罪的灵魂。”凶手是谁?凶手是命运,是不完整的生活,是父亲的缺失,“生我的不只是一个母亲。母亲无法再给我一次生命,这不是她一个人能够做到的。”当儿子高喊着“父亲”,在寂静中,“他”重新回来。这是对父亲的命名,这是时间的命名,它同样在死亡之后复活:母亲死了,儿子死了,“父亲”成为了一个象征,“所有人的血都是一个看不见的父亲所赐予的。奇怪的是,人们不愿知道他们的父亲就是上帝。”
死亡之日,是不见父亲之日,而美国作家欧文·肖的《埋葬死者》直接将矛头指向了战争的无情,这是最“写实”的一出戏剧:将军下令将尸体掩埋,但是士兵们发现那些尸体还“活着”,他们喊出了“别把我们埋掉”的喊声,不想被埋,是因为生命不想从此终结,尸体说:“我们没有向谁请求获准离开这个世界。也没有人问过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离开。”而那个名叫迪恩的尸体对着母亲说:“我才只有二十岁,妈。我还什么都没干,我还什么都没见识,我甚至连女朋友都没有。我花了二十年的时间,不过是为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作准备,接着他们就把我杀了。做孩子是没有意思的,妈。”死者没有死,是不是也意味着生者不生?掩埋队的四个士兵最后走出了舞台,他们似乎也走向了自己的死亡之路,而舞台上最后只剩下将军一人,“缩成一团地趴在机枪上,枪口对准着已空无一物的坟地。灯光渐暗。”就像尸体一样,在“静场”中走向了死亡。
死亡的世界里依然是恶魔,而对于死亡的“表现主义”题材,奥尼尔的《毛猿》讲述了一个现代寓言。行驶在大海上的大西洋邮船是现代社会的缩影,奥尼尔颇有深意地将邮船的大炉间表现为“一种压缩的空间”,一排排的铺位和一根根的立柱,形成了笼子结构,那些船员就像是笼子里的怪兽,无法从这里逃离。这是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但真正可悲的异化表现在那个叫杨克的船员身上,他拥有健壮的体魄,他向他人发号司令,充满优越感的他认为自己就是世界的原动力,“我是结尾!我是开头!我开动了什么东西,世界就转动了!”从船上到街上,杨克一直保持着这种优越感,甚至蔑视其他人,而实际上,其他人把他看成是关在笼子里的毛猿,空有一身健壮的身体却无法获得自由,而实际上现代社会就是一个牢笼,杨克的悲剧在于至死他都不知道自己就是一头畜生,“他象一堆肉,瘫在地扳上,死去。猴子们发出一片吱吱哇哇的哀鸣。也许,最顶事的,毕竟还是毛猿吧。”
“毛猿”之死,其实是杨克自己制造的死亡,在这种死亡里当然没有救赎者的上帝,只有恶魔般的毁灭者,而实际上,真正救赎的也并非上帝,而是自己。德国作家恩斯特·托勒的《变形》,指向的也是战争,除了流露出对战争的厌恶之情之外,托勒更想表现的是和平——这里有战争死神,也有和平死神,战争和和平都是被死神主宰,其实就是把世界交给了自己。在《货运火车》《铁丝网之间》《残废人》《寄宿者》《死亡和再生》《流浪者》《登山人》等图景在虚幻的真实中展现之后,弗里德里希喊出的是“前进”的呼声:
前进!在明朗的白天前进!现在去统治者那里,用怒吼的管风琴声向他们宣告,他们的强权是一个偶像。去土兵那里,他们应把他们的刀剑锻造成犁锋。去官人们那里,向他们展现他们那是一堆垃圾的心。不过对他们宽容些,因为他们也是可怜人,误入歧途的人。不过拆毁城堡,大笑地毁去那用炉渣,用晒干的炉渣建成的假城堡。前进——在明朗的白天前进。
前进是看到自由,前进是打碎强权,前进是“一个人的奋斗”,在经历了生与死之后,看见了战争与和平的假象之后,所有人喊出的“我们还是人!”表达出的是人类最后的命名,我们是人,是死去而复活的人,是“别把我们埋掉”的人,是通往大马士革之路的人。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387]
思前:元戈达尔的75面体
顾后:《懒兵》:军营梦游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