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0-26《法罗文献》:冷寂与便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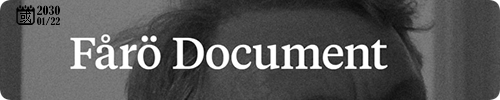
2022年看了《法罗档案》,一年之后补看了《法罗文献》,而属于英格玛·伯格曼的这两个文本,相隔了整整十年——当一年后看《法罗档案》十年前的“文献”,在片名相同的观影中,一种时光倒错的感觉并没有成为全新的体验,也许正如伯格曼在《法罗档案》时所说:“在1969年的《法罗文献》中,我给观众留下了一个黯淡的结尾……”十年后,黯淡还是黯淡,冷寂还是冷寂,孤立还是孤立,进与出依然是一对没有解决的矛盾,因为“噩梦还是继续”。
1960年伯格曼因为寻找电影《犹在镜中》的取景地,听取电影公司的建议来到了离北极只有几百英里的法罗岛,本来只是一次探访,但是伯格曼却意外地发现了这个“人间天堂”,他的电影《犹在镜中》《假面》《羞耻》《安娜的情欲》《婚姻生活》《豺狼时刻》都在这里完成了拍摄,法罗岛成为伯格曼电影世界的一个固定符号。不仅如此,伯格曼的人生也在这个小岛上发生了彻底改变,“我对摄影师斯文·尼夫基斯特说,我预备在这里度过下半辈子,我要在这里盖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这个愿望终于在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七年间实现。”伯格曼成为了新的法罗岛居民,直到2007年7月30日,伯格曼在法罗岛的最后睡梦中逝世。
从闯入者变成法罗岛居民,伯格曼的转变无疑是一种发现,而发现对于他来说则是精神的“回归”,在自传《摩灯》中他说出了自己被法罗岛吸引的原因,法罗岛“完全符合你内心最深处的理想——无论是它的景象、色泽、情调、静谧还是日光”。但是当他在踏上法罗岛9年后拍摄了这部纪录片,当他用镜头对准常住在这里的居民,他依然是一个旁观者和观察者,他的目光依然是以外向内的投射,那么这个“外来者”对法罗岛的解读,是不是真的能深入这个理想世界?观察法罗岛,首先是对法罗岛这个孤岛历史的一次回顾,诞生于3亿年前的法罗岛,位于瑞典哥特兰岛附近,现在还随处可见远古的珊瑚、贝壳和化石,漫长的历史演变对于法罗岛来说,依然是一种静静的存在,虽然在古代,法罗岛也是波罗的海地区发达商贸的连接点,它的另一个意义就是“旅程中的岛屿”,或者是“旅行者的岛屿”被大海包围的法罗岛给商贾船只提供了栖息点,但是这也无法改变法罗岛孤立的状态。
法罗岛的居民,似乎和这个岛一样,也生活在孤立的状态中,畜牧业、渔业和木材生产是居民的主要生活来源,“靠岛吃岛”是几代人维系的原始模式。女人的丈夫已经去世,她接手的农场有25英亩地,养殖了三头牛、五匹马和两只母猪,一家人的生活也很简单:早上六点钟起来挤牛奶,然后煮咖啡准备早餐,早餐后15岁的佩尔则去森林伐树,然后锯成木板,一天的活干完,一家人吃晚餐,然后便是上床休息。对于这样的生活状态,女人直言“很自由”,面对伯格曼的提问:“你担心未来吗?”女人犹豫了一下说:“担心被国有化。”接着她便说起在岛上生活,“一直被排除在外”,这种被排除的感觉并不是被法罗岛其他人排挤,而是法罗岛本身的归宿问题,有人认为他们是哥特兰人,而在语言、宗教和风俗上,他们和哥特兰岛存在很大不同,另一方面,法罗岛属于法罗松的自治市管辖,大海的隔阂让他们与自治市保持着距离,所以女人担心被国有化,就是害怕自己被纳入另一个政治体系中,眼前这“自由”的一切都可能不复存在。
| 导演: 英格玛·伯格曼 |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生活对于女人来说是一种“自由”,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是一种无聊——在1969年的纪录片里,女人15岁的儿子佩尔没有露面,但是在十年后的《法罗档案》中,已经长大成人并担负起家庭职责的佩尔则表露了对岛屿生活的某种不满。他的不满也代表着年轻一代的想法,在一辆疾驰的公共汽车上,伯格曼的镜头对准那些年轻人,强劲的音乐传递着他们的心声:他们不想被束缚在这个小岛上,理由是无聊,是没有工作,所以他们的目光开始投向外面,很多人去了法罗松德,开始了更广阔的天地。年轻人离开是因为法罗岛的闭塞,而实际上并不只是年轻人感受到了和外面的隔阂,长期住在这里的人,也慢慢有了一种向外的欲望,但是他们向外不是为了工作,而是和外界进一步的联系,而是为了改变法罗岛的现状。
法罗岛的现状是邮局马上要关闭了,通信将成为问题;现状是法罗松德的屠宰场垄断了屠宰业务,使得农户们的收入减少;现状是要看图书,必须要到法罗松德预定;现状是有人写报告要建桥,但是被认为是疯子;现状更是老一辈的传统手艺将没人继承……似乎在伯格曼的镜头下,那些被访谈的农民很少有像那个女人那样,认为现在的生活是一种“自由”,他们都有着对现状改变的渴求。而实际上伯格曼的叙事明显带着自己的观点,作为一个来到岛上的旁观者,尽管喜欢这里的景色、色泽和情调,喜欢静谧的自然,但是他那时候也只是以过客的身份居住于此,在伯格曼的世界里,法罗岛就是一个他者,所以他从自己的需求出发,希望法罗岛能有更便捷的交通,能提供更便利的出入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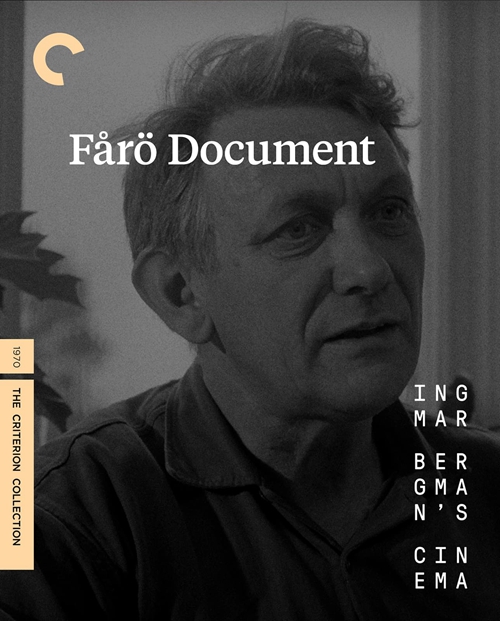
《法罗文献》电影海报
在他的镜头下,对于岛内自然风光的拍摄是彩色的,而对于居民原始生活的摹写是黑白的,而对于艰难生存的揭示则是通过冷酷而真实的全景描写:杀羊的场景中,从放血、剥皮到掏出内脏,伯格曼详细记录了“庖丁解羊”的全过程,带着血腥的镜头给人以残忍;而在拍摄母羊产羊羔的过程中,更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呈现,在寒风之中,母羊直接将羊羔生在了冰天雪地之中,母羊在挣扎,羊羔在呼唤,但是一切都处在自生自灭之中,有的羊羔掉在地上之后挣扎着站立起来,而有的则被冻死了,甚至还挂在母羊的身体上,这是自然的优胜略汰,却也是生命的适者生存。全景展示杀羊过程,自然主义角度再现母羊产仔,这两个场景中,伯格曼没有配以旁白,在无声之中,一切都是那么血腥,那么冷漠,而这或许也是法罗岛最真实的一种自然主义生存方式。
显然,这样的法罗岛是冷寂的,不是天气制造的冷寂,而是自生自灭的可怕,在交通、邮政、教育等公共资源严重短缺的小岛上,生存也是一个问题,而资料显示,1969年春天小岛居民数为754人,而40年前的数字是1100人,所以日渐减少的人口数反映的是人们对闭塞之地离开的选择:为什么那个提出修桥的老人会被认为是疯子?为什么那个从自行车上摔下来的妇人失去了救助的机会而截至?为什么社会民主党的奥维在孩子出生4个月的时候,抱着他开着拖拉机去地里干活?“幽灵农场”“死寂的森林”,这些小标题更是传递出伯格曼期望这里发生改变的渴望,而他在最后提出的问题是:“一个社会的政治民主对这里的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关于生存环境的改善,关于工作机会的增加,关于邮局的重建,关于桥梁的建造……这些都体现社会政治民主的作为,但是伯格曼遗憾地认为,“在高度工业化的福利中,法罗岛居民的生活经常被城里人低估了……”
伯格曼的想法已经很明确了,那就是法罗岛的新生,法罗岛的发展,法罗岛向外的目光,都必须有一个发达的民主政治体制,否则只能是法罗岛的噩梦。他以外来者的目光为法罗岛的未来提供了解决方案,无可否认,伯格曼的合理化建议正是基于他在法罗岛之外的生活经历,并将其和外界进行对比而做出的,在不是土生土长的法罗岛上,当伯格曼发现了它的迷人之处,也是选择性发现了它静谧的一面,它原始而自然的状态,它并不被人打扰的生活,符合伯格曼的期望,但是静谧同是意味着闭塞,原始和自然也代表着落后,在某种程度上他也希望这是一个更为便利的存在,而这两方面有时候却是矛盾的。当之后的伯格曼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并建造起了电影院,当然还有位电影拍摄的外景地,住在这里的居民对伯格曼的行为也颇有微词,他们认为伯格曼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这里的环境,包括之后法罗岛旅游业的开发,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有人出去,有人进来,有人坚守,有人离开,法罗岛并不固守一种状态,当然在伯格曼的世界里,它也永远不是单一的符号,或者真正属于法罗岛的自由,正是那个女人的生活状态,“你不应该恨任何人,也不能永远相信任何人。”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3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