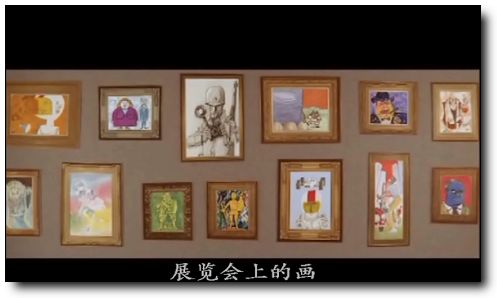2017-10-26 《展览会上的画》:并非虚拟的浮世绘

它们被挂在墙上,它们被展览,它们静止于一幅画中,这是不是一种以艺术的名义进行的“示众”?而示众的那些看客在哪里?穿过安静的城市,穿过寂静的街道,穿过展览会的大门,当那些绘画作品展现在眼前的时候,谁是观者?在一种镜头的深入中,在无人的场景里,看见的主体其实在画面之外,而所有的画面之存在都是为了看见,所以隐藏着的观者并不是消失,反而它以一种监视的方式把这些画纳入到日常生活中。
而画作上的那些主角,也并非只是挂在墙上的静止符号,在靠近、放大的过程里,他们从绘画的艺术世界走向了真实的现实,艺术形象从来不是虚拟的,他们就是现实的一部分,并且制造了现实的荒诞、无聊和权力,阐释了生活中的贪婪,欺骗和虚荣,就是在创造和真实之间上演了一幕幕的寓言。
新闻记者和士兵,似乎是最接近现实的人物,但是当他们走向画作进入到现实的时候,他们却以变形的方式演绎了关于谎言,关于贪婪的主题。白头发,紫色的脸和黑色的衣服,当新闻记者以这样一种形象出现的时候,他更像是一个骄横的大猩猩,腿脚变得细小,身体变得粗大,大与小比例的失调就像新闻和事实之间的关系,那些发生过的政治事件、游行、冲突,变成了一张张的照片,这是形成文本的过程,似乎在这过程中远离了发生过的时间,以孤立的方式被放进了历史中。当事件成为新闻作品的时候,还有什么客观的真实?
|
| 导演: 手塚治虫 |
 |
战火纷飞,爆炸不绝,这是冲突的世界,这是死亡的前线,但是当一名士兵打开小屋的门,看见里面病倒的女子,他却有了某种拯救的欲望,经历了战争,这或许是人道主义的体现,那水壶里的最后一滴水送到了女子嘴里。但是当他走出屋子,却看见另一个士兵也走进了屋子,面对女子,他似乎也展现了他的人道主义精神。两个士兵,面对女孩的时候,不如说是两个男人,而且在战争之外,他们之间又上演了新的战争:他们拿出枪,拿出匕首,打斗的目的只有一个,如何让女人更喜欢自己。战争被延伸了,两个男人何尝不是变成了敌人,而在争斗中,大火燃烧,就像门外不绝的爆炸一样,最中将他们推向了死亡而无人性的战争世界里。
|
|
| 《展览会上的画》剧照 |
一滴水的拯救,变成了两个男人的战争。同样是一滴水,对于那只在城市里迷路的蟋蟀来说,却像是对于自然世界的回归。饥饿、寒冷、孤独,这是蟋蟀非进这个陌生城市的感受,他需要的是食物,是一个家,当他看见那些鲜花的时候,似乎有了某种欲望的释放,但是,当他猛扑上去的时候,才发现所有的花都是假的,或者说都是人工制品,连同停在画上的蝴蝶。鲜艳的花朵,美丽的蝴蝶,多彩的城市,这仅仅是视觉上的逾越,它们无法提供一种真实的生存环境,所以在这个水泥城市里,蟋蟀依然找不到食物,找不到家的感觉,依然在饥饿、寒冷和孤独中。
而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个园艺工的“成果”,他是人工景致的园艺工人,他装点着这个城市,他维护着它们的美丽,视觉上的满足从来都是牺牲真实的现实,甚至扼杀了它,所以当他看见那一只垂死的蟋蟀时,抓起来将他扔到了角落里,蟋蟀不属于这个城市,他是一个过客,更是一个多余人。但是在他被扔向角落的时候,却突然发现了那株小草上有一颗露珠,如此透明,如此水灵,如此自然,当露珠终于汇成一滴水掉落下来的时候,对于还活着的蟋蟀来说,就是最大的福音,也是最后的自然。
迷失在城市森林里,这不是蟋蟀的生活,这是人类进入现代生活的困境,蟋蟀只是一个隐喻,而在这个逐渐发达的时代,蟋蟀的悲剧却在不断深化,也把人带向了荒谬的世界。工厂主拥有生产工厂,在这里他是主宰者,当生产车间逐渐自动化的时候,那些工人仿佛变成了机器,他们穿着同样的制服,他们做着同样的动作,在流水线上他们操作着机器,而实际上他们本身也变成了机器,也变成了流水线上的产品,而这不是异化的最后结果,当升级换代之后,那些工人失去了工作,他们连坐在流水线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机器取代了工人。在机械化的时代,人从变成机器到最后人的消失,都是对于人的异化,而人的异化并不只是在生产线上的人,他是全体的人——工厂主操纵着机器,最后却反过来被机器操纵,他反而变成了机器世界里的一个零件,甚至被完全分解,最后在机器的切割中走向悲剧。
工厂主的命运和蟋蟀有什么区别?异化的荒谬带来的存在的巨大悖论,而美容外科医生,也像工厂主一样,操纵着机器,控制着病人,只不过他是以美的名义。那些老人在他那里变得年轻,那些肥胖的人在他那里变得苗条,药物、器械、阵痛,改变着人的形体、年龄,它带来的是一种满足欲望的美,但是这种美却是虚假的,是虚荣的,甚至是病态的,年轻的老人离开之后还是变成了老人,苗条的女人离开之后也变成了肥胖的女人,而美容医生在给别人制造虚假的美的同时,也难以逃脱自我的异化,一个喷嚏之后,世界仿佛发出了巨响,医生猛回头,看见的不再真实的自己,而是一个完全变形的身体。
荒谬已经无处可逃,它完全控制了那些操纵者,那些实施者,让他们在更加荒谬的世界里被推向异化的世界。电视明星开着豪车,受着膜拜,完全在一种被虚构的生活里;拳击手是大象,当他击败了对手而站在最高荣誉殿堂的时候,他变成了英雄,于是在享受中失去了自我,最后被另一头大象击败,他的世界里只剩下那断裂的鼻子;那些自我命名为“垮掉的一代”的只不过是争权夺势的小鸡,他们看上去特立独行,反叛勇敢,却以一种狭隘的派对思想来扩张自己的领地,最后在内部的斗争中失去了原本属于自己的世界,回归到蛋壳里,是一种保护,也是一种倒退。
似乎在这些虚幻的荣誉、名利的欲望、人的异化世界里,只有禅宗宗师岿然不动,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山岳震动,无论是春夏秋冬,还是阴晴月缺,他都保持着同一个姿势,在打坐中保持自我,但是这真的是一种淡定?真的是一种自我?在长久的静态世界之后,他突然暴跳起来,咧着嘴大声叫喊,是终于无法忍受这样的打坐生活?还是在喜怒哀乐的表达中回归到正常人生?禅师之存在,却也是那个“寓言的结论”的开始,那些支撑着凯旋门的雕塑门,用自己的力量守卫着它,但是当那些画中的主角依次穿过大门,热闹的场景反而制造了喧嚣,雕塑似乎无法再承受同一种动作的生活,他们开始离开,像那些经过的主角一样改变了存在的状态,但是当他们离开变成行走的人,那凯旋门便开始断裂,甚至慢慢接近倒塌,而上面没有离开的妇女孩子开始害怕恐惧。
失去自我会导致正常秩序的解体,会制造更多的危险,这是生活中的寓言,那个记者、园艺工人、美容外科医生、大工厂主是不是制造了虚假?那个电视明星、拳击手、士兵是不是失去了自我?那两个士兵是不是导致了战争?甚至那个禅宗宗师是不是也背叛了自己的信仰?所以在寓言的世界里,世界需要的是一种和责任、义务、美、和善有关的秩序,他们是力量,他们是爱,他们是艺术,在重新支撑起来的凯旋门里,他们支撑起来的其实是最后的信仰,一种不被异化的信仰。
他们构成了浮世绘,而从墙上走下,又回归到墙上,这是画作上人物的命运,但是这不仅仅是艺术的展现,所有的画作都变成了现实的一部分,变成了我们存在这个世界的隐喻——片头的街道是真实的,落叶是真实的,光影是真实的,而片尾那些演奏着音乐的乐团也是真实的,在从真实开始到真实结束的世界里,艺术无法逃离真实,于是也以讽刺的方式在回应着真实。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634]
思前: 《宝贝》:被删减的欲望手枪
顾后: 《丹麦交响曲》:镜头在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