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5-16 谋杀幻影,万火归一

和当当的送货不一样,亚马逊的快递员直接把装有图书的箱子送到了我的办公室,签名,然后交接,直接面对的消费仪式将一切的程序摊开在我面前。8本图书、总额为127.30元优惠后为107.30元的价格,将五月的购书计划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高潮,也向“九品书库”千本存目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
乔治·佩雷克的“六十年代”是一个消费时代,而出版于1965年的这本小说或者也可以称为一种消费产物,当年的雷诺文学奖在小说文本的赞誉上试图摆脱物质主义的压力,所以这只是一场早期消费社会中对于“小资”生活品味的展示。而在“物的时代”,如何寻找幸福?佩雷克说:“今天要想做一个有福的人,就绝对得做一个现代人。”在这个消费社会里,现代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巨大的物质诱惑?逐渐失重的精神?在沉重中寻找幸福,在现代世界里这或许是一个悖论,“允诺并不等于现实”,佩雷克说出了一种幸福的可能,在无限满足欲望的过程中,物是一个巨大的旋涡。而在细致而又繁琐的社会学的描述中,佩雷克也用优雅、细腻、含蓄的小说语言,接纳和开拓了现代的叙事方式。小说第一句:“起初,目光将沿着一条又长、又高、又狭窄的走廊,在灰色的化纤地毡上向前滑动。”
 |
“它也是一部侦探小说吗?没错,只要你别忘记它所侦探的是藏于一切万有之中的那个秘密。”《时代》周刊这样问,而在越来越多的“反侦探”或者“伪侦探”小说中,精神上的那个迷宫才是我们失踪的地方。奥迪帕·马斯在《拍卖第四十九批》也是如此,在调查皮尔斯遗产过程中,偶然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暗示有一个历经几个世纪秘密地与美国官方邮政部门竞争的通讯系统——特里斯特罗的线索,迷宫出现了,那里有托马斯·品钦故意设置的熵、多义性和不确定性,大量邮票里暗含着一个现实之外的世界?神秘人物的到来,似乎并不是寻找出口,反而在迷宫里越陷越深,所谓迷失,也只是在无序、空虚、没有确定性的现代社会中,人类的尴尬处境,但是对于托马斯·品钦来说,消失也是一种真正的现实,他早年的照片和档案以及私生活早就消失在公众面前。据说这是品钦已有的长篇小说中,最易读的一部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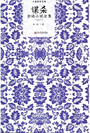 |
侦探?案情?死亡?我越来越觉得小说文本正在切入现实的身体,甚至生命。《余地小说全集》的标题注解就已经宣告文本后面的作者生命的一次终结,《谋杀》所以也是余地遗留档案中的先锋试验小说的整理。我不知道所谓谋杀,是不是指向死亡这个终极意义,作为“小说前沿文库”之一种,在小说中余地的探索一直在延伸,“他让小说中的主人公获得完全的独立意识而手刃作者的这种写作意识是‘作者之死’的灵活运用。”在书的介绍中说,“余地小说对密度的要求带来的直接效果是使阅读保持了‘间歇’和“滞涩’,天然的休止符,阅读余地小说有篇幅无形中被拉长的感觉,最终使作品饱满起来。”而当作者的书写和生命消逝,那么留给文本的是不是被拉长的谋杀过程,在《2001:十四行》的诗中,他写道:“从哪里开始,最后在什么地方结束?我不知道/上一步和下一步之间,所有的十字路口如此相似/这是肯定的:从我的脸庞中间穿过的,永远是同一面镜子”。
 |
再次引用才发现,《南方高速公路》变成了《南方高速》,作为一部小说的翻译标题,里面有着变化着的文本需求,但是堵车还在,流言还在,范晔在《八十世界环游一天》的译后记里说:“《南方高速》通过堵车这一现代社会司空见惯的现象呈现出另一种“非常态”的现实,——或许比“正常”秩序中的现实更值得留恋和向往;”“非常态”的现实是一个隐喻,而“正常”的秩序则是阅读中的经验主义。八个短篇所构成的“非常态”现实也是科塔萨尔在营造的充满爵士乐、先锋派绘画、拳击和黑色电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感觉与意识的质地被不断复制,深入其中你只能感受到时空交错,如梦似幻的不真实感觉,但这种不真实却让你不想回到“秩序”的现实,此大概就是科塔萨尔真正的魅力。《西语美洲文学史》的作者奥维耶多说:“每当想起科塔萨尔的名字,人们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词是:‘fascinante(迷人的)’”。
 |
“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这是第一章第一段的第一句话,在第一页里。一开始就说到死,说到那种偏离我们正常秩序的死,一定是保罗·奥斯特要带我们进入另一个世界,或者说,死亡即为幻影中,我们还如何辨别生者,辨别方向?一场空难让戴维·齐默教授失去了深爱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子,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他不知所措,他迷失了自我,他觉得自己也成了一个死人。他足不出户,沉溺于悲伤的酗酒泥潭中不可自拔,直到六个月后的某个夜晚,他偶然在电视里看到了默片谐星海克特·曼的电影片断,才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还有笑的能力——于是,为了看完所有海克特的老电影,他开始周游世界,那成了使他继续活下去的惟一动力。而海克特早已经离家出走,所有人都认为他已经不在人世。然而,新墨西哥荒漠中的来信,却使教授走上了一段不可思议的幻影之旅……幻影重重,其实并无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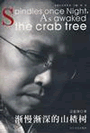 |
书的封面上,宗霆锋戴着眼镜,目光里是智性的闪烁,在贾勤“信仰的遗迹”中,我发现了宗霆锋,对于他,以及他的诗歌、绘画,我之前一无所知,正如他的“渐慢渐深的山楂树”,不知道是不是一样具有开花、结果、砍伐的植物命运?在诗中,宗霆锋说:“它已知道砍伐的秘密/它已被砍伐/它已被点燃——/成为火焰并成为/光明、光明它已知道/这正是它/无可避免的/命运、命运、命运它已知道!”在贾勤的《现代派文学辞典》中,“宗霆锋”已成为一个永恒意义的词条:“梦中,宗霆锋摆脱了对人世的赞美,他如今乐于观察植物的破土与存亡,乐于给自己振作的决心。”植物的存亡,在诗性中也具有那种不可言传的幸福感:“是不是有着如今我相信我的一生会在写作中度过。肯定这一点让我内心平静。我知道,只要写下去,写作必定会使我在很多时候遭遇困局;而在极少的时候,它会带给你肯定的幸福。”
 |
亚里士多德说:“当若干事物虽然有一个共通的名称,但与这个名称相应的定义却各不相同时,则这些事物乃是同名而异义的东西。”作为逻辑学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把它叫分析学,他谈到概念的划分,一般性和普遍性,本质属性和偶然属性,他以为属比种更加真实地是实体,也就是说种概念具有较高的普遍性,相对而言,属概念较为狭义而具体。在《范畴篇》里,亚里士多德首先使用了范畴这个术语的,他规定出十个范畴,作为基本概念,它们是:实体、数量、关系、性质、活动、遭受、姿态、时间、地点、状态。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前面四个范畴,特别是性质,尤为重要。规定明确而清晰的范畴是为了判断,判断是为了在最后得出结论,这个过程就是推论,亚里士多德首创了三段论法,即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在《解释篇》里他分析和明确阐述名词、动词和句子的性质。我们可以在这里获得一定的启发,那就是注意到了事物的常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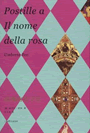 |
在我阅读《玫瑰的名字》之后,是不是必须要深入一部阐释的著作?“自从我写了《玫瑰的名字》 以后,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大部分都问我结尾的拉丁语六音步诗是什么意思,它是怎样孕育出书名的。”这是埃科给《玫瑰的名字》找的一个阐释的借口,借此找出隐藏在文本之后的“模范读者”:“因为我认为一个叙述者不应该为他的作品提供阐释,否则就没必要写小说,更何况小说正是生产阐释的绝妙机器。”所以恶鸟才会在《马口铁注》中说到要去“发现文本如何创造我所感受到的那种迷狂的运作机制,并且最想体验的是——自己如何利用这种文本机制去创造一个新的文本也让我的读者狂热一把”,所以《玫瑰的名字注》作为翁贝托·埃科的阐释著作,完全被隐藏在了“知识”的外衣下:为什么叫“玫瑰”的名字?为何选择在中世纪展开故事?迷宫是否有其原型?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328]
文以类聚
随机而读
暂无留言,快抢沙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