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4-14《小活佛》:死者的眼睑在眨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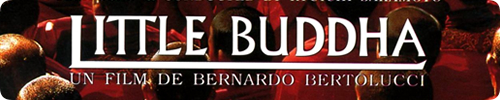
48分26秒,一场死亡的仪式正在举行,死去的人躺在水边,当举行仪式的人用双手掬了水,然后洒在死者脸上的时候,一个细节闪现:当水滴落在他眼睛的时候,眼睑却跳动了一下,甚至是眨了一下,仿佛是感受到了水的清冽。这是一闪而过的画面,也是容易被忽视的场景。一个死去的人如何会感受水的温度和刺激?在某种意义上这可能是贝托鲁奇拍摄时的一次大意,或者是演员不到位的表现,但是这一细节却在导演和“演员的休养”之外,成为了对电影主体的巧合性阐释:因为躺着的人只有在电影里是死者,作为演员,在电影之外他是一个生者,生与死,构建了电影的非现实特性,但是却在死者尚生的语境中,消融了生与死的界限,生死无界,灵魂不灭,而这正是这部贝托鲁奇“东方三部曲”之二的电影的一个主题。
观影中的发现,带着某种偶然发现的快感,而观影之外的另一个发现是:这部名为《小活佛》的电影在豆瓣上有相应的条目,但是只是静态的介绍,不能评分,不能标记,也无法发表评论——无论是短评还是长评论。难道这也是一部敏感的电影:或者和“小活佛”的宗教意义有关,或者和西藏的政治意义有关?一边疑惑着,一边便把这种无交互的现象称之为“死亡”——点击“看过”而没有任何痕迹,观者永远处在不在场的位置,这种留下空白的状态不正是一种缺省?暂且不评论导致这种结局的原因,在空白和缺省中,在“死亡”的意义上,似乎和48分26秒的那个细节,一起构成对这部电影的奇特体验。
而奇特性如果回到电影本身,回到宗教信仰本身,贝托鲁奇用西方视野来表现东方文化,似乎就是为了消除这种不在场,似乎就是为了在生死同一性中找到意义。来自不丹的诺布喇嘛千里迢迢去往美国西雅图寻找转世灵通,就是信仰一种轮回思想,这是东方宗教走进西方世界的一次跨界寻找,很明显的是:不仅在轮回的实践意义上,而且在不同文化的对话中,建立了一种在场性。从一开始,电影讲述的是一个佛教轮回的故事,在印度的村庄里,一名祭司要把一头山羊献给天神,当祭司举起刀子准备划破山羊的喉咙时,山羊突然大笑起来,祭司问山羊为什么笑,山羊说,我是在经过499次轮回之后而成为山羊的,现在我找到了转世成为人的机会。但是山羊又哭了起来,山羊说:“我是为你这个愚蠢的祭司而哭泣,因为500世以前我也是一位祭司,也曾献祭山羊给天神。”这个时候,祭司才开悟,于是他哀求山羊:“请您宽恕我吧,从现在起,我愿当这片净土上羊群的守护者。”
这个佛教轮回的故事并不是诺布喇嘛来到西雅图说起的,而是讲给那些小喇嘛说的,“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什么启示?”一只山羊曾经是拿着刀面向山羊的祭司,当他在轮回中变成了山羊,也就预示着眼前这个要将它献祭给天神的祭司会走和他一样的道路,所以他需要被宽恕,从而让自己成为守护者。不该献祭牺牲,不仅仅是对生命的尊重,不仅仅是在仁慈中逃避惩罚,它的更大意义在于轮回的本质,那就是一种众生平等的信念,无论你是山羊还是人,都是平等的,而这也赋予了生命以意义。所以诺布喇嘛在接到那封信时,说在西雅图找到了多杰喇嘛的转世者,便来到了现代的美国,来到了陌生的西雅图,来到了完全是基督教文明的杰西家中。
一直在美国传道的丹津堪布在见到诺布喇嘛时说起多杰喇嘛在圆寂之前做过一个梦,而他所描绘的梦中场景和杰西家的位置一模一样,这种神秘性当然是贝托鲁奇的一种虚构,但是却将现实和梦境、东方和西方连接起来。在杰西家的时候,杰西的出场似乎冥冥之中有了某种佛缘,当诺布喇嘛和杰西的母亲康瑞聊天的时候,杰西光着脚从后来出现,他没有示以自己的面目,而是戴着一个自制的面具,如佛教对于这个西方家庭来说,是一种神秘的存在一样,这个出生在这个多杰喇嘛梦中的孩子也成为神秘的一部分,当他揭开面具,看到穿着僧袍的喇嘛,没有丝毫的惊奇,反而向熟人朋友一样接受了诺布喇嘛送给他的那本讲述悉达多创办佛教的书。
| 导演: 贝纳尔多·贝托鲁奇 |
喇嘛、佛教进入美国家庭,这是一个起点,从此杰西开始在诺布喇嘛的讲述中,在这本佛教起源的文本中认识佛教,从此这个和佛教没有任何关系的家庭开始慢慢接受佛教,从此悉达多修行的故事也在这种接触中慢慢展开。贝托鲁奇用两条叙事线讲述这个故事,一方面是在文本里演绎的佛教起源故事,另一方面则是在现实中上演的佛教轮回故事,而两个故事最后又交叠在一起,尤其是在加德满都找到另一个转世者歌陀的时候,关于佛陀的故事已经到了最重要的阶段,那就是如何战胜自我,战胜自我的执着时,悉达多在菩提树下修行,天地开始变化,狂风暴雨、电闪雷鸣齐齐袭来,这时魔鬼开始干扰他,在他面前的池水里,魔鬼甚至化身为悉达多的样子引诱他,而悉达多不为所动,“你根本不存在。”魔鬼被击败,悉达多也在最后战胜自我中成佛,这种消除了分别心的结果完成了自我最终极的定义。
在这个过程中,来自美国的杰西和来自不丹的拉尤、歌陀一起站在菩提树下,在贝托鲁奇的镜头下,他们仿佛看见了几千年前悉达多成道的过程,一切如在眼前,现实和历史传说交错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仿佛是轮回在电影叙事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但是让这三个转世者认识佛教的起源、轮回的意义,似乎并不是难事,难的却是让杰西的父母接受这一古老的东方信仰,而这种接受的过程更像是消除分别心,更像是达到众生平等。而“接受”在贝托鲁奇的电影中,又运用了从最开始的两条叙事线讲述到最后合二为一的方式。悉达多曾经是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太子,这是衣食无忧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他不会选择创立佛教这条人生之路的。正是因为他偶然发现了王宫之外的世界,才感觉到了世界的缺省,才感觉到了自己的不在场,才感觉到了一种众生的不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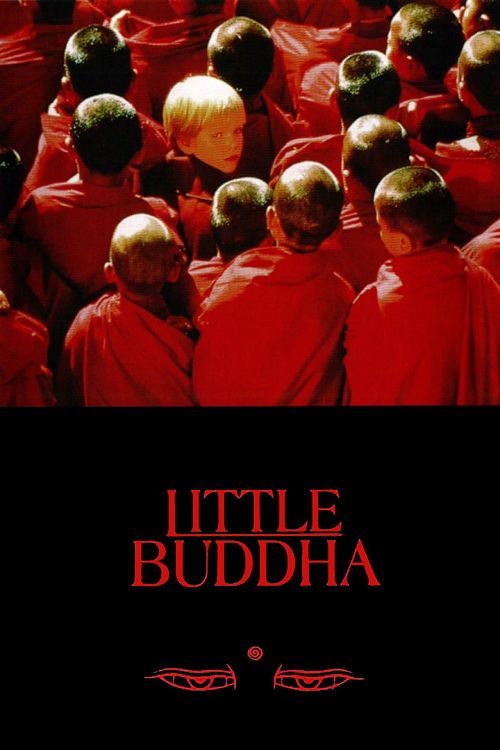
《小活佛》电影海报
在举行盛大仪式的时候,他看到了人群中一个瘦弱的老人,这个他从未见过的老人让他感觉到世界的一部分被隐藏了,所以他冲破了被预设好的线路,走进了穷人生活的地方,他看到了老人,看到了病人,看到了死人,这个王宫之外的地方打开了悉达多的眼界,让他认识到了“苦难”,也从此他在车匿的帮助下,他告别了锦衣玉食的生活,他走出了繁华的世界,开始走向更广阔的地方寻找人生解脱之门。这是悉达多为消除自我和他者之差别的努力,也是消除分别心第一阶段的努力:他和乞丐交换了衣服,他和森林里的大蛇共处,后来他又和合理的水牛对视和对话,都是在实践众生平等的理念,而最后在菩提树下击败了化身为另一个悉达多的魔鬼,是消除分别心的第二阶段,那就是战胜自我的我执。
在悉达多的文本之外,美国家庭的现实,也在感受着苦难,也在追寻着平等。杰西的父亲迪恩起初不相信佛家,更不相信轮回,当诺布喇嘛说自己的儿子是转世小活佛,他甚至把带走杰西的行为称作是“绑架”,但是在现实中,他却遇到了困难,这个工程师为朋友伊凡设计了漂亮的建筑,但是伊凡后来陷入公司的危机里,甚至最后走投无路而自杀了。这对迪恩的打击很大,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同意带着杰西跟随着诺布喇嘛他们一起去不丹现实遭遇的困境便是一种人生的苦难,每个人都感受着,也寻找着解脱之门,所以在内心挣扎之后,迪恩接受佛教也表明西方文明和东方信仰之间的对话。
当三个孩子来到寺院,当仪式举行,其实对于转世的意义,更多是一种灵魂的不灭观,就像诺布喇嘛曾经在迪恩面前摔碎了那只茶杯,他说茶杯尽管岁了,但是茶还在,不管外面的器具有什么变化,它都是这样存在着,就像灵魂——人会死去,会失去肉体,但是灵魂恒在,便能超越肉体,便能消除生死:48分26秒的死者眨动了眼睑,是不是具有了生的意义?而最后完成了任务的诺布喇嘛也在入定的状态中圆寂,“死亡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死是生的延续,生是死的轮回,当三个孩子回到各自的家乡,便把诺布喇嘛三分之一的骨灰撒入自然,或者融入大海,或者飘向天空,或者在菩提树下成为泥土的一部分,都变成了对于生命的一种延续,轮回而永在。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3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