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14 重现“书声e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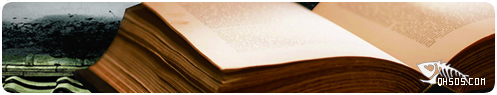
昨天搞卫生,竟然从书橱里发现几本值得保存的书,注意,我说的是保存,而不是收藏,他们有着天壤之别,对于我的心里慰藉也是天上和人间一般。这些书包括曾加盟微软和谷歌的IT风云人物李开复的《做最好的自己》,迪拜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副总统兼总理、迪拜酋长谢赫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的《我的构想》,新华出版社的《轰炸东京》和中央文献出版社的《天目抗日》(上下),后两本书的作者是本地一个大学的教师,长期从事田野调查和报告文学的写作,引起过很大争议。把这些书整理出来,是想发掘其中一些有意义的东西,他们湮没在许多消费型图书中,日久生尘,拂之不去,甚至有些发黄了。想来也是有点可惜的,虽然说不上是值得收藏的好书,但是想起来还是有一点可以去阅读的价值,可以收入我的九品书库。突然又是一些触动,关于图书,这段时日在用心地读着从网上购来的图书,今年这样的阅读热情尤甚,粗粗数了一下,从1月到现在4月初,已经完完整整读完了11部作品,这些作品也不只是从情节上吸引人的小说,还有需要做些摘录的诗歌、历史,读起来并不轻松,而且也保持着阅读之后写博客点评的习惯,似乎又回到了一个疯狂渴望阅读的时代,曾经远去,如今又重新拾掇起来,犹如哲学所说螺旋式上升的感觉。昨晚就是这样,很用心地把贾平凹的《古炉》放在灯下,用地板的冷意刺激着,不至于在他过于琐碎的记述中沉入梦境。有时候觉得阅读真的很累,记忆力衰退是无论如何都会有事倍功半的感觉的,但是只要手里还留着书,我想还是要做一个文字的仆人。
早上起来,在整理书房的图书时,发现了两个事实。一个是刚看完的《万历十五年》早在2001年就购买了,只不过那个版本是三联的,一下子感觉有一点自我欺骗的味道,10年前就购买了图书,却一直未曾翻阅,以致出现了重复,这案例以前也有,鲁羊的《在北京奔跑》,而且是一模一样的两本,真当有点囧,或许这也是和“书非借不能读”一样的尴尬,只是购买未曾阅读,当然是不会记在心里的,过眼云烟而已,如此,也是阅读的死穴。另外一件事是,翻了以前的购书记录,才知道“九品书库”的第一本图书购买并非以前传说的1990年,而是1991年,去年就信誓旦旦说要在网上建一个全新的个人藏书阁,还取好了名字叫“书生e气”,准备去年刚好值图书购买20年的纪念日推出来。但后来终究没有实现夙愿,荒废在找不到岸的的互联网上。而现在,日期改变了,也就意味着这个计划又迎来了新的曙光,按照这个最初的日期,应该是今年6月。
于是,便又激发了兴趣,纪念日只是找个好听的借口,真正的意义是把那些零散的书目整理在一起,毕竟20年需要这样一种档案的管理,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很多东西已经不成系统了,检阅不方便,当然也有对过去岁月的遗忘感觉。叫了一年,想来这个计划应该在这个因为纪念日错乱而激发欲望的日子重新上路。便开始把以前下载的程序进行改良,PJblog,下载模板,然后便是设计格式,这些最原始的准备做好,才能一步步按照计划实施出来。
大概有1000部图书了,我想,在这20年的购书生涯中,这个数字的背后是生活中充满着的“书生e气”,在形式大于内容的“悦读”时代,我仿佛看到了那闪过我们面前的光,照亮我们内心,驱赶我们的寂寞。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1419]
思前: 《安阳婴儿》:为什么生存?
顾后: 神马的纪念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