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6-14《秦教授》:“在场”是个悲剧

“秦教授”其实是“钱教授”,是钱伟长,当伊文思的镜头对准在清华大学宿舍内的钱伟长,当钱教授在镜头前说起自己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摄影机和拍摄对象同处在“在场”的世界里,在场而说话,在场而被记录,它抵达的一定是真实,但是因为“在场”而真实,是不是反而变成了一种谎言?
伊文思在让钱教授和家人“说话”之前,用旁白先进行了“说话”:钱教授是当年在外国求学的精英之一,20世纪30年代先后留学加拿大和美国,1946年回国,是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这一旁白无疑确立了钱教授的身份:知识分子,当旁白结束,在钱教授书房里的摄影机让之后的“说话”变成了指向此时此地的“在场”。在伊文思拍摄钱教授谈文革的时候,它的在场其实分成两部分,一是摄影机制造的在场,摄影机将记录下钱教授说的话,这些话会成为历史,但是在说的时候一定是一种此时此刻;另一种在场则是时代的在场,当时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结束,在这个没有结束的时间区间里,不可能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功过是非进行评判,也就是说,时代的在场必须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一员,这也就意味着钱教授的态度和观点必须符合时代的在场性。
摄影机在拍摄,时代还在行进,在双重的在场中,看看钱教授说了什么话:首先钱教授认为以前的教育体制上教授掌握着很大的权力,教授强调的是理论,在他看来,实践的影响并不重要,他甚至对学生讲,“保证你们的论文能够过关”;正因为强调在理论上的建树和突破,看不起劳动者,也不重视实践问题,造成了和劳动人民的脱节,也加重了自己的功利观。钱教授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自己认为如果去农村劳动肯定“活不下去”,“我愁的是我自己”,这便是自私的表现;儿子没有像自己一样从事研究,而是去了工厂,这对自己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一时无法接受,父子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但是现在看来,他所走的路比自己好多了,因为他就在劳动一线;作为教授如果完成一本著作,一定会署上自己的名字,但是哪个劳动者会在劳动的产品上署自己的名字?这就是一种狭隘的名利观……
| 导演: 尤里斯·伊文思 / 玛索琳娜·罗尔丹·伊文思 |
钱教授在伊文思的摄影机前批判自己不注重实践只注重理论的错误观点,批判自己不肯去劳动一线的自私表现,批判自己在著作上署名的名利观……正因为自己存在种种错误思想,所以他认为文化大革命起到了教育自己、改造自己的目的:他们对钱教授进行了批判,在门口贴出了大字报,还来查书,看看里面有没有反动思想,“还好我的书都是关于自然科学的,没有反动内容,他们友好地希望我进行思想改造……”后来响应毛主席“知识分子和劳动人们在一起”的号召,去了工厂,发现了自己只注重理论的后果,工厂里没有助理,也没有专门检测的机器,那时的钱教授想去找一块高碳钢,但是自己认不出高碳钢,找了一大圈也没有找到,是一个工人出来帮助他,“他拿一根棍子敲了敲,听听声音就找出来了……”通过文化大革命中的几个例子,钱教授认为自己的思想得到了改造,在镜头前满脸笑容的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很有必要,尤其对像他那样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解放了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不会再被书本所束缚,我解放了,同时也摆脱了名利的狭隘追求和自私思想……”而在一旁的妻子妻子孔祥瑛、女儿钱开来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
这就是“在场”的钱教授,这就是在伊文思的摄影机里“在场”的钱教授,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的那个时代中“在场”的钱教授。但是如果用历史的目光来看待这样的“在场”,是不是会感到一种悲剧的存在?科学界的“三钱”,只有钱伟长被打成了右派,她在1957年发表的批评苏联教育模式和对科学体制建言献策的两篇文章,因言获罪,45岁便被剥夺了讲课和从事科学研究以及发表文章的权利,这位学识渊博的科学家只能与扫帚、抹布为伍,最后因毛泽东一句“钱伟长是好老师”而保留教授头衔,并免于发配,但妻子被隔离的同时,儿子考上大学竟然也“不予录取”。而到了文革,对于钱教授来说是比“反右”更长的噩梦,他头顶着“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帽子强迫去首都钢铁厂劳动改造,成为了一名炉前工……直到文革结束,已过六旬的钱伟长抱着“让祖国更强大”的信念,依然充满激情地工作:“我力图夺回已经失去的良好岁月,日以继夜地工作。”
钱伟长在“反右”和文革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劳动改造,成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无疑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但是身在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的那个时代,面对有着某种政治需求的纪录片拍摄,也许钱伟长在“在场”的状态下,的确发现了自己身上的某些缺点和不足,发现了学术研究中的偏见,但是上升到对自我的批判、对文革的肯定甚至赞誉,这里面到底有着怎样的言不由衷,甚至有着内心的怎样的折磨和痛苦?也许只有钱教授心里知道,只有在场之外、历史之外的钱教授心里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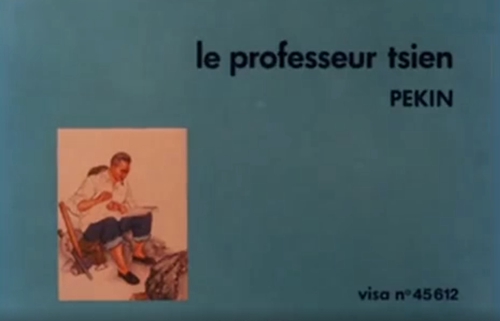
《秦教授》电影片头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2015]



